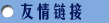我一定讓你走得風風光光
一個月裏,吳祥志又送走了6位老人。
秋天時,他去看望唐長根。那時,老唐戴著呼吸機,煩躁地躺在床上。老唐肺癌已到晚期,而醫保卡裏的3萬塊報銷額度早就用光了。那個下午,他抱怨起悲哀的人生,憤憤不平地講述四處求助均被拒絕的遭遇。但除了等待,他別無選擇。末了,他掏出一件襯衣。
吳祥志愣住了——襯衣被染過似的,滿是大片大片的血跡。“那是被我弟弟打的。”老唐説。從新疆退休回來後,他住在了母親家。不久,母親病逝,遺囑裏把房子留給了他。這是兄弟反目的開端。為房子今後的繼承問題,兄弟倆大打出手,直到遍體鱗傷的老唐被送進醫院。老唐盯著血衣,往事就像家中那些腐朽的空氣,充斥在回憶中。沉默了許久,他冷冷地説:“親兄弟。”
35天后,老唐死了。
開追悼會那天,天色驟變,上海下起了大雨。吳祥志帶著幾十位老人一同為老唐送行。他們並不認識老唐,但他們有著共同的標簽:上海知青。
他們都是1963—1966年,被送往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的十萬分之一。那時,國家剛剛經歷過大饑荒,邊疆依舊動蕩貧窮。而被視為道德墮落之所的城市,發展規模被嚴格限制,大量城市青年被剩餘出來,無法被計劃到就業和升學中去。在浪漫的鄉村理想和發展現實的雙重策動之下,知識青年遠赴窮鄉僻壤的藍圖被勾勒出來。10萬上海知青進疆的成功,拉開了此後“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運動的序幕。
1970年代末,隨著運動的破産,這10萬知青,有一萬多名順利回到了故鄉,剩下的人,或紮根新疆;或滯留上海,退休回城,為戶口為晚年保障,長年累月地奔波。
2011年上半年,老唐還是奔波群體中的一員。吳祥志眼前閃現他的身影,仿佛那才是昨天的事情。
吳祥志滿臉滄桑,表情倔強,像懸崖邊上彎曲的樹。2007年,他60歲,按照政策,終於可以正式退休回到上海。然而,2003年隨退休的妻子回城時,戶口問題就開始成為他的困擾。當時,上海中心城區的老家正在動遷,如果戶口順利遷入,他將可以得到一套新房子作為賠償。嫂子提出,必須交20萬元,才能入戶。隨著房價猛漲,要價又開到了50萬元。
親情在利益面前撕開了不堪的面目。他試圖向嫂子説情——三十多年前,兄弟倆必須有一個去新疆,是他代哥哥做出了犧牲。“那是你自願去的”,嫂子並不領情;他又去街道反映情況,“這是家庭矛盾”,街道不願管。就這樣,他只能在上海打工,租房子,四處討説法。
在上海,他“像個皮球被踢來踢去”。幾年後,他找到了知青群體,終於有了歸屬感。他還扮演起送葬人的角色。誰重病了,他代表大家送上100元的慰問金;誰死了,他組織追悼會、送花圈……
這些年裏,他似乎習慣了悲傷,“今天還一起參加追悼會,過幾天就成了被追悼的對象”。他看著當年前赴後繼踏上通往新疆火車的少年們,如今前赴後繼地死去,仿佛看著自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被悄然帶走。
為什麼要回上海?這成了他經常追問自己的問題。
而每當深夜來臨的時候,新疆總到夢裏造訪:熟悉的道路,地裏的勞作,和妻子縫製褲子的場景……
在上海的日子,新疆是老知青們共同的夢境。
在韋木英的夢裏,新疆化身為一朵朵棉花,她跪在地裏摘個不停。
在謝虎禮的夢裏,他總是手扶獨輪車,在荒地上推來推去。悵然四顧,發現到處是茫茫戈壁灘。心恍惚著沉下去:不是回上海了麼,怎麼又到了新疆?原來,回上海只是一場夢……
“我是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謝虎禮拍拍胸脯,一遍遍確認自己的身份,儘管過去十多年裏,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直呼為“新疆”。
1964年,他聽著“羊肉當飯吃,牛奶當水喝”的童話來到新疆,卻看到滿目的荒蕪。第一個除夕夜,他們啃饃饃,喝白菜湯。一位知青不禁唱起了《星星之火》,唱起了幾十年前被賣到日本紗廠當童工的小珍珠的命運:
“媽媽啊!我哪天不在想著你,我有多少苦楚要對你講。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親娘。到今朝盼著媽媽你到上海,媽媽啊!趕快救我出火坑!”隨即,整團的知青哭成一片。
“小林,你要聽我唱小珍珠麼?”這天,在老知青韋木英的小房子裏,微醺的謝虎禮閉著眼睛再次唱這首滬劇,韋木英輕輕附和著。陽光穿過石庫門老房子的天窗,照在他們臉上,韋木英哭了起來。相比起故鄉的親人,他們更喜歡呆在知青群裏。他們隨意串門,一塊吃飯喝酒,不需要客套,不需要言語,自在而親切,隨時可以哭泣,也不需要特別的安慰。
在上海,謝虎禮始終有一種不願承認的隔閡感。當他大口喝酒時,他會説,我們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憶起新疆,卻永遠逃不出這樣的詞語:忍饑挨凍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勞累,夏天開荒時成千上萬的大蚊子……
1980年一個禮拜天,謝虎禮得知了雲南知青“勝利大逃亡”的消息,整整一天,他心裏都激蕩著逃離的衝動。到了傍晚,他敲響大鐘,“上海知青託兒所集合了”,他大喊。他把返城的消息廣而告之,大家最終決定,選出5名代表到各團各連串聯。
當晚,謝虎禮幾人攔了拖拉機,一路顛簸七十多公里,從塔裏木河北岸一直開到了終點塔河南岸。黑夜裏,他偶遇了知青歐陽璉,兩人一拍即合。此前,歐陽璉和其他知青已經為回城陳情多次。第二天,他們決定,在塔河兩岸宣傳回城的決心。
1980年11月初,歐陽璉鼓動成千上萬知青集結到阿克蘇城區,但阿克蘇地委不願意對話。11月23日開始,他們絕食了近一百小時,直到歐陽璉收到電報,被告知中央工作組將會到來。12月11日,上海知青請願大篷車隊途中翻車,3名知青遇難,阿克蘇地委終於發出給知青簽發戶口的文件。
那幾天,拿到戶口的謝虎禮沉浸在回城的喜悅中,他變賣家産,收拾家當。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從廣播上傳來:阿克蘇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所發的戶口證全部作廢,火車站實行軍事戒嚴。謝虎禮一陣絕望,喝下一瓶60度的高粱酒,躺在地上抽搐。
“當時只想到了死。”醒來後,他暗下決心,一有機會便逃離新疆。
1981年秋,機會終於來了。謝虎禮帶著妻子張維敏、兩個孩子謝萍和謝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於1974年的龍鳳胎,名字寄託了父母樸素的希望——平均。他們希望孩子得到同樣的寵愛,享受公平的命運。
回城最初的日子裏,謝虎禮一家擠在張維敏哥哥的小房子裏,佔據著半個房間。謝虎禮從來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間。他成天泡在外面,做著各式小生意:擺康樂球、賣童裝。
不幸的是,這一年,國發91號文件的出臺幾乎阻斷了他所有的生路。文件稱要“堅決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數穩定在新疆”,列出10種規定,把知青們劃分為三六九等,除了1.5萬人符合規定可以調回上海市區或上海所屬的外地農場,其他的“一律動員返回新疆農場”。
謝虎禮夫婦正是屬於要被“穩定在新疆”的大多數。謝虎禮的小攤不斷被沒收,他在上海街頭四處流竄,連大舅子也被停職了。他被告知:謝家什麼時候回新疆,什麼時候恢復工作。但這些都不能動搖這對夫婦的決心,直到有一天,兩個孩子從學校被驅逐出來。
1984年,謝虎禮帶著一家子,再次踏上開往新疆的列車。車上,他和妻子張維敏聽到一聲慘叫,隨後得知,一個家庭的父親跳下了火車。3天3夜後,他們抵達新疆。謝虎禮望向窗外,一股絕望之感向他襲來。
“平均”的不平均
1985年,胡耀邦到新疆考察,他為知青題詞:“歷史貢獻與托木峰共存,新的業績同塔裏木河長流。”知青們奔相走告,重燃了希望。次年,上海副市長謝麗娟到新疆考察,得知消息的知青張寶璇向她遞交了聯名請願書,並要求召開座談會。知青們紛紛要求回城,至少讓子女回到上海。
幾十年後,張寶璇回憶起來唏噓不已,當年保證不被“秋後算賬”的帶頭人,最後都難逃懲罰。多年來,他總結、反思,最終走上法律的道路。他屢屢呈交行政訴訟狀,請求判當年的行政行為為違法的強迫勞動,並給予補償。如今,他相信法治的力量,再也不會像年輕時那樣去請願陳情了。
當時,他們的要求在1989年部分實現了:知青家庭的一個子女可回到城裏。但知青的命運似乎已經註定了。20世紀80年代年代以後,不符合回城規定的知青有了分化:有的永遠留在新疆,有的死亡,有的流散到第三地,最大的一撥有三萬多人,他們幹到退休,然後返城。有六千人左右自動和新疆脫離關係,選擇滯留在上海,成了黑戶。
1988年,謝虎禮帶著兩個孩子逃回上海,成了六千分之一。為存退路,張維敏選擇繼續留在新疆。
回到上海的謝虎禮和母親及兩個孩子擠在7平方米的老房子裏。謝君至今都記得,自己整整一週都躲在門後偷窺外面的一切,那種既嚮往又恐懼的情形。1980年初的記憶還困擾著當時的他——那時,他上小學二年級,和姐姐在開學的第一天,就被展示到眾多小朋友面前:這是新疆來的借讀生。姐弟倆一聽就把頭低了下去。
起初,少年謝君上課的時候總是走神,在本子上偷偷畫在新疆的房子、房子周圍的道路和建築,“怕自己忘了新疆”。可隨著生活的展開,他確實再也回憶不起新疆的模樣。
謝萍對於過去有著超強的記憶力。從房子的結構到老師的姓名到別人看她的眼神。在20世紀80年代那些年,她聽到最多的評價就是“野蠻人”。一天傍晚,她請新疆回來的同學到家裏吃飯,飯桌擺在門口,他們看到肉都特別興奮。她還記得,姑姑高聲對街坊説:他們新疆來的就是奇形怪狀。走在路上,她也總低著頭,感覺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她覺得,所有的癥結都在於,沒有上海戶口,而她本該是上海人。
轉眼間到了1990年,這對龍鳳胎16周歲了。按照政策,倆人中的一個可以入上海戶口。那時的謝萍想報考美術中專,而報考的前提條件是要有上海戶口。老師兩次到她家向謝虎禮誇獎她,希望戶口能給謝萍。但每次的答案都是:戶口要留給兒子。
那一陣子,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似乎人生也望到了盡頭。一個傍晚,回到亂糟糟的家裏,她再也不想去馬桶間做作業了。她拿起菜刀往手腕一割——幸好菜刀並不鋒利,家人立刻撲過來搶救。割腕事件終究是一場小風波,依舊改變不了戶口的走向。
舊矛盾未了,謝家又有了新矛盾。謝君報戶口,遭到了奶奶的阻攔。她把戶口本藏了起來。謝虎禮在家裏鬧得天翻地覆,把櫃子都踢爛了,最終才讓母親交出了戶口本。
許多年後,支離破碎的親情仍是謝虎禮難以言説的痛楚。他悲哀又自我安慰地想,這也許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宿命。1953年,父親作為資本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新疆勞改,留下母親帶著幾個孩子領救濟金生活。從童年開始,自卑感便如影隨形,他從未買得起書包和課本。當他站到臺上帶領少先隊員唱歌時,他發現“下面的紅領巾一片鮮紅鮮紅的,而自己卻是淡紅淡紅的”。都是父親害的,他想。去新疆後他從未給父親寫信,從未見他一面。少年謝虎禮以父親為恥,他認為是父親阻礙了他在新中國變成一個新人;中年謝虎禮不敢恨母親,卻不能原諒母親阻撓他在新時代進入新生活。
1992年,戶口總算對那些滯留在上海的黑戶知青開禁了,同時他們也被要求寫下保證書: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再過五六年,他們又得到了每月兩三百元的補助,有一年,他們拿到了369元。從此,“369”成了這撥知青的稱呼。
謝虎禮也是這一結果的受益人。可向母親討要戶口時,又是一番爭吵,最終謝虎禮以保證書來交換戶口本——不參與分房子。此後,這個7平方米的屋子充滿了緊張。同一屋檐下,母親和謝虎禮一家分開爐灶做飯。而直到老人去世,謝君未曾叫過她一聲奶奶。
這樣的故事在當時反覆上演。而隨著歲月的消逝,人們也慢慢淡忘了其中的情節。1993年,擁有了戶口的謝萍理直氣壯地在大街上昂首闊步,因為戶口問題而流産的初戀也已遠去。烙印在慢慢消退。她讀夜校,努力工作,結婚生子,融入了大都市的生活。
謝萍為自己感到幸運。她知道,在她身後,還有三萬多知青的子女們,註定要經歷更多的掙扎,43歲的陳莉就是其中的一個。
戶口人生
週末的傍晚,陳莉在廚房燒飯,看到記者,她勉強笑了一下。關於知青二代的生活,她不願回憶,不願看到他人同情的目光。
“講述過去能改變什麼嗎?不能。對我有好處嗎?沒有。除了揭開傷疤,讓我痛苦。”飯桌上,她眼皮下垂,把辣椒皮一點點地從豆腐上挑下來。可沉默良久,她還是回憶了,因為,“北方人會為人著想”。
陳莉傲氣、敏感,有一股把生活看明白不自欺的倔勁。如果可以重來,她不會選擇回到上海。可是1988年,如同其他知青二代,她和妹妹都只是被不甘心的父母送回上海的懵懂少年。她們四處打工,被欺負、被欠薪,飽一頓饑一頓,一斤麵條倆人搶著吃。妹妹哭著要回新疆,可她們根本買不起火車票,陳莉強裝狠心:要回,你自己回!
1989年報戶口時,陳家把戶口給了唯一的男孩。母親李鳳嬌想,女孩子畢竟可以嫁個上海人。於是,陳莉走上了通過嫁人改變戶口的道路。漂亮的陳莉對那些看得上她的上海男人從未動心過。她早就看透了待價而沽的交換本質:對方要結婚,她要戶口。
第一場婚姻以她遲遲沒生孩子而告終,而直到離婚,她還沒達到落戶的年限。2001年,母親從新疆退休回到上海,開始為解決女兒的戶口問題而陳情。陳情的結果給了她一些優惠:結婚滿兩年就可以入戶。
第二場婚姻的選擇餘地更小了,對像是五十來歲的上海男人。兩年總算過去了,陳莉在家四處找戶口本,丈夫卻站在一旁,冷冷地説: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吧,我是永遠都不會讓你入戶的。
陳莉果斷離了婚。慢慢地,她已經不再想戶口的事情,她甚至只想找到自己的家庭。後來,她又被介紹給一個帶著孩子的鰥夫。男人找各種藉口不和她結婚,但她還是和他同居了兩年。孩子和母親都慢慢喜歡上她,可他總對她挑三揀四,嫌她掙錢少,當他炒股失敗的時候,又把責任歸咎到她身上。
“如果有本事我還會找你這樣的人嗎?”陳莉反唇相譏。她總是忍氣吞聲,還嘴時,她已經下定了離開的決心。
如今,她似乎看開了,對於戶口也不再執著,她想擺脫戶口魔力——她的一些知青朋友,解決了戶口問題就像變成另外的人種似的。生活告訴她:安全感必須自我供給。所有以交換為目的的婚姻都是不會長久的,在矛盾和爭吵中,終究會暴露它不堪的面目。
過去,一種強大的自我保護本能讓她隱藏身份,她講一口流利地道的上海話,她察言觀色,她小心翼翼地打量自己,生怕露出外地人的馬腳——但她又看不起上海人,雖然她也遇過開明謙和的本地人,但在她的世界裏,那是少數。
許多時候,她感覺空蕩蕩的。她拼命掙錢,每天一早出門,深夜才回到家裏,必須為自己的晚年生活打下經濟基礎。上海許多角落都有她打工的身影,但是,“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她這麼形容過去的生活。她甚至羨慕起母親,他們有工齡、有歷史、有群體歸屬感,他們可以隨時放聲痛哭,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賠償青春,可以大聲説“我是上海人”。她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是。
母親李鳳嬌一邊打毛衣,一邊靜靜聽著,不住抹眼淚。許多事情她也是這一晚才聽女兒第一次説。多年來,她為愧疚感所壓抑,畢竟陳莉是大女兒,戶口本應歸她的。女兒有時問,我是你親生的麼?李鳳嬌説,我看不是。女兒回答,我也覺得不是。這樣的對話讓她難受到極點。
這位63歲的老太太,講述起往事,總帶著不自知的黑色幽默。
1964年,李鳳嬌還是一名初中生。5月28日——她還記得——下午,她去上學。校長笑瞇瞇把她招到辦公室,説,李鳳嬌同志,你被批准到新疆參加生産建設兵團了。
她困惑地説,我沒申請啊。但幾天后,她就到了新疆。然後被通知,分到農四師牧場。
“什麼是牧場?”她問。
然後,她就到了牧場。一晃35年。
回城10年裏,她四處打工,為女兒的戶口四處陳情,還去了北京,可是還沒下火車就被趕回來。
在一次陳情中,她認識了謝虎禮的妻子張維敏。此後,每次遇到什麼事,張總是“挺身而出”,她感覺自己找到了“主心骨”。
母親,快來救救我……
1993年,滿30年工齡的張維敏從新疆提前退休。幾年沒見,兒子對她已經有了陌生感。她看到家人上廁所都用草紙,心疼地説,多浪費啊,為什麼不用報紙呢?女兒感到不可以思議,好像她是另一個世界的人。
不過,張維敏很快重新適應了這座繁華的都市,她燙髮染發,衣服閃閃發亮,成天打麻將。隨著謝虎禮攢足了錢,她還住進了新房子。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10年,直到謝虎禮得知,“369”們將和上海退休工人待遇接軌。他對張維敏開玩笑説:我是上海人了,你還是新疆人。
儘管“369”們仍對自己被算少工齡而憤憤不平,但在張維敏看來,這卻是一種極大的不公平。她的退休工資是一百來塊錢,10年間緩慢地往上漲,醫療補助則是工資的3%。而當謝虎禮退休後,他們的門診報銷可以達到90%,住院報銷額度的上限是28萬。她問丈夫:“這是為什麼呢?你們是逃回來的,我們這一撥卻老老實實幹到了退休。”
那一年,張維敏去參加知青聚會,她在一張要求提高新疆退休知青社保待遇的“六千人聯名信”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此後,她去新疆生産建設兵團駐上海辦事處陳情。當一名官員要求推選代表時,她站了出來。李鳳嬌還記得張維敏的話:“我們這一代人為祖國建設貢獻一生,我們犧牲青春,毫無怨言。現在老了,落葉歸根,希望國家來解決我們的問題。”她覺得她説出自己的心聲,如同大多數人,她被推選為代表。
儘管張維敏身患多種疾病:高血壓、心臟病、嚴重風濕症……但她從來都是個精力充沛的爭先進的人。在青年時代,她屢屢在摘棉花勞動中奪得第一名。她總是天沒亮就打著燈往地裏出發,一直勞作到晚上才回家。謝虎禮總是教育她,幹多幹少每天都是一塊二,何必那麼積極,他甚至偷偷把鬧鐘調晚幾個小時。
從2003年開始,張維敏就在奔波中——爭取醫保,爭取和“369群體”享受同等待遇。每週三,他們就到政府門口表達訴求。張維敏總是站在人群中央,拿著擴音器喊……
吳祥志第一次見到張維敏時,她正在代表身後的老人們向政府表達訴求,他覺得她説出了他多年來的心聲和委屈。往後,為了他的戶口,張維敏奔相走告,五六十人站了出來,到街道討要説法。他終於獲得口頭承諾,問題將得到解決。
8年來,張維敏每天忙到深夜。在兒子的記憶中,家裏電話響個不停,一聽到需要幫助的,張維敏就一瘸一拐地跑出門去。“家裏的事她從來不這麼積極。”女兒説。一次次陳情,一次次談判,知青們的待遇終於有了改善,門診可以報銷了,從40%到75%再到85%。
世博會前夕,張維敏寫了公開信,讓知青們息訪。她寫道:“我們不能做破壞國家形象的罪人!我們應表現出高度的責任感,配合政府營造一種清平世界的和諧氣氛!任何時候我們個人天大的事都不如國家的事大!”
兩頭都是棄兒。
上海虹口公園。老遠就聽見歡快的音樂聲,老人踏著節奏翩翩起舞,他們身著新疆維吾爾族服裝,扭動脖子,輕擺手腕,忘情地轉圈,臉上綻放著燦爛的笑容。
“這是新疆剛運過來的!”張團長伸開手,給記者遞來葡萄幹。這位上海阿凡提歌舞團的創辦者鼻子下還夾著兩撮往上翹的假鬍鬚,笑起來一跳一跳的。每逢週六,張團長都要和其他的老知青群體在這裡跳新疆舞。
2000年,從新疆退休回來的張團長,感到滿大街都是異樣的眼光。他一個人跑到公園跳起了新疆舞。“我想證明,新疆回來的知青不是萎靡不振的。”張團長這麼認為。
郞先生站在一邊教授圍觀者舞步。他已經跳了將近十年,至今沒法習慣上海的精緻和優越。他跳新疆舞,上新疆館子。只有在這裡,他才能忘卻回到上海的失落感。
為什麼要回來呢?“落葉歸根。”他指指大樹,毫不懷疑自己樸素的情感。可他又總是懷念過去的時光,這時光自動剔除了痛楚,它是青春,是友誼,是豪邁的生活。
在這個公園的一角,另外的知青們松鬆散散地站著。他們拉家常,更多時候,他們彼此不説話,曬著太陽,靜靜圍觀跳舞的人群。
“都是苦中作樂。”另一位退休歸來的知青則説,自己有一肚子委屈,卻無處申訴。他想,只有等到見馬克思的時候,他再慢慢訴説了。
而這樣的訴説,送葬人吳祥志已經聽得太多,他把這些故事全裝在了心裏。這幾年,他回過兩次新疆,看到從前的地窩子變成了一排排新樓,走過的泥濘小路鋪成了柏油大道,當年他們住過的房子如今住進了年輕力壯的新工人。
在這個嶄新的世界,他想起自己聽過的經歷過的故事,想起他們這一代人的心血。但他又有一種陌生感,除了檔案,這裡似乎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跡了。
“新疆説歡迎我們回去,可是真要回去他們也不歡迎,我們已經老了。”他説,他開始理解這個世界的經濟學原理,也理解了為什麼自己“兩頭都是棄兒”——作為異鄉人,他對新疆失去了利用價值;作為本土人,他對上海未曾有利用價值。
“上海肯定想,我們從未對這裡有過貢獻,為什麼要負擔我們的養老。可是當時,是它把我們送去的。”歷史的債務,要由誰來承擔?為什麼要去新疆?為什麼又要回到上海?
他要養活自己。可對於未來,他已經沒有把握了,那套知青們集體為他爭取來的房子,也隨著張維敏的被捕變得虛無縹緲。
2011年的一個早晨,一群警察走進張維敏的房子,説要找她談談。前一晚,她忙到淩晨5點才睡下。丈夫謝虎禮叫醒了她。她迷迷糊糊睜開眼睛,邊穿衣服邊嘮叨著:都8年了,還有什麼好談的。
此後,家人再也沒見過她。2011年12月23日,法院二審宣判,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張維敏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林珊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莉、李鳳嬌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