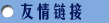朱家嶺的山腰上剩下78歲的李鳳鳴一個人。3個兒子相繼搬離,房子空了下來,她的心也空了下來。
時常來探望她的只有大兒子陽社成,他在一家建材工地做大理石拋光,自1999年下崗以來,臨時工是他的常年狀態。他57歲了,越來越苦惱:如何讓老母親安度晚年,也讓自己安度晚年。
上崗下崗
1975年,20歲的陽社成有了第一份工作,在湖南冷水江市玻璃廠當學徒工。在這家廠他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筆工資,20元。他花了5毛錢給弟弟妹妹買雪糕,剩下的悉數交給了父親。1976年,他被單位派往哈爾濱考察,那是他一生中去過的最遠的地方。
1979年玻璃廠虧損,陽社成調到了冷水江市第三水泥廠。水泥廠和玻璃廠一樣屬於集體企業,是冷水江街道辦事處的下屬單位。在水泥廠,陽社成進入煅燒車間,負責給立窯添煤加炭。
“那時工作實行三班制,早中晚三班,一個星期休息一天。”陽社成在上千度的高溫立窯前幹了19年,眼睛受不住炙烤,漸漸抬不起眼皮,最終變成了一條縫。眼皮常年耷拉,讓他形同盲人。
26歲那年,媒人給他介紹了一位鄰縣的農村姑娘。條件是,解決女方的城市戶口和工作。那個冬天,陽社成提著禮品,徒步一百多裏山路,來到了新華縣吉慶鄉梅花洞村,從山溝溝裏將那個從未謀面的姑娘帶回家。
20世紀80年代是國企職工最美好的時光,妻子鄢雲也順利地拿到了城市戶口。這段婚姻還給她帶來了一份國企工作——冷水江市耐火材料廠食堂炊事員。
1981年,陽社成與妻子鄢雲生下一子,取名陽希,寄意陽光與希望。每個月拿著固定的薪水,享受著國有企業的各種福利,生活頗感優越,“小的時候,我吃得最多的就是蜂皇漿,那時候獨生子女都可以去工廠裏領。”
但是這種優越很快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急轉直下。陽社成所在的水泥廠開始走下坡路。“廠裏的活越來越少了,假放得越來越多,開始延遲發工資,後來乾脆就不發了。”陽社成説。
初到水泥廠時,陽社成的工資是42元。1999年,水泥廠破産倒閉,他拿到的最後一個月的工資是208元。他工作勤奮,但也逃不過下崗的命運,和全廠207人一起,回家待業。
這一年,兒子考上大學。本是一件喜事,但是陽社成高興不起來,他要為兒子繳納近三千元學費,而當時家裏所有的積蓄只有5000元。
生活陷入停滯。陽希記得中學6年,家中不曾添置一件傢具,“好不容易才買了一台二手的熊貓牌彩色電視機”。這段婚姻也終因妻子不堪窮苦生活,于2003年畫上句號。
從1995年開始,工廠給他繳納的社保金,也在兩三年後停掉。和眾多集體企業一樣,由於效益問題,先是停繳了員工的社保,倒閉、破産、變賣隨後而來。
為供兒子上學,下崗後陽社成到工地打零工,“一天16元,一個月480元,每天工作最多10小時,沒有節假日”。陽社成掰著手指頭過日子,每個月要給正在上大學的兒子匯去400元,自己剩下80元生活費。
2003年陽希考上研究生。雖然生活清苦,陽社成鼓勵兒子繼續深造,自己則繼續幹苦力換取兒子的學費。
2004年,倒閉的水泥廠賣給當地最大的一家鋼鐵企業,改造成廢水處理廠。“有人説賣了300萬,也有人説賣了900萬,反正我拿到手的只有18000塊。”
陽社成從這筆錢中拿出8000塊,補繳了停交多年的社保金。“我的社保金從1995年開始算起,之前沒交的錢都得由自己補上,”他到當地社保局詢問了國企職工補繳社保的政策,“我一共要交納15年的社保金,60歲退休後,根據現在的政策,可以每個月領取1400元左右”。之後幾年,陽社成每年都去社保局繳費,從2000元到3000元。2008年到2010年這3年,一度還享受了個人交納40%、國家代繳60%的政策。
2011年本是陽社成交納社保金最後一年。“按15年算,這是最後一年”。2012年初,他又從社保局獲悉,如果再交5年社保,到了退休年齡可以每月領取1800元。
陽社成算了筆賬,“再交5年,得再交三萬多元。從60歲開始領取退休金,就算活到80歲,每個月可以多領400元,20年下來可以多領9萬多元。”他決定再交5年。3月,他續交了3750元。
此時,陽希已經工作6年了,每月給父親500元生活費。雖然每月有這筆匯款,陽社成還是在大理石廠打工,“給人修灶臺,做櫥櫃,還要給死人修墳臺。每個月能賺將近2000元”。
再過3年60歲,可以每月按時領養老金度晚年了,陽社成卻從電視新聞聽説退休年齡要延遲5年。“這樣的話,我要到65歲才能拿退休金,再幹5年,年紀大了,這樣的體力活我就幹不動了,負擔可能會落到兒子身上,如果國家不管我們養老送終,那還是得靠兒子啊。”陽社成對國家養老政策的變動表示擔憂,但更讓他擔憂的是母親的贍養問題。
四兒養母
母親李鳳鳴78歲了,獨居在冷水江朱家嶺半山腰上。
二十多年,這裡的房子拆了蓋蓋了拆,這裡的人走進走出。2008年老伴去世,李鳳鳴開始獨居。
李鳳鳴不識字,不識路,在娘家的時候,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直到出嫁,才邁出了家門,她知道沿著家門口那條長長的鐵軌一直走,就到陽家了。這是她此生唯一認識的一條路。
1955年,大兒子陽社成誕生。隨後又得一女兩子。在社會主義如火如荼的年代,丈夫陽家騰給3個兒子分別起名為:社成、定成、祝成。這3個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名字寓意是:社會主義成功,社會主義一定成功,以及祝賀社會主義取得成功。
5月,江南進入梅雨季節。連下了好幾天的雨,李鳳鳴睡到半夜,迷迷糊糊感覺到蚊帳上面在滴水。連日小雨,老房屋頂的石棉瓦被風吹落,床全部濕透了。
陽家的老房建於1982年。當時身為村支書的陽家騰,要了塊最狹小,最偏僻的宅基地,蓋起了一層紅磚屋。3個兒子分而居之,小兒子居東,老大居中,老二居西。後來小兒子陽祝成外出求學,他的房子由老兩口居住。
陽家騰還在世的時候,李鳳鳴從不上街,只在家裏做家務,或者上山種菜。所需的物品都由陽家騰操辦,財務也由他來管。
3個兒子當中,李鳳鳴對小兒子陽祝成最疼愛。
陽祝成是兄弟姐妹4人裏學習最好的一個。他天資聰穎,雖整日好玩,成績卻不差。1990年,初中畢業的陽祝成考入長沙冶金技校,3年後畢業分配到長沙一家冶金廠工作。他成了陽家出走得最早最遠的人,被認為是“最有出息的人”。
2008年9月底,陽家騰因病去世後,李鳳鳴開始學著認路,學著看懂數字,學習如何跟人討價還價。
人老多病。李鳳鳴身材略胖,2008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身體慢慢消瘦下去,每月服用藥物需要百元左右,沒有醫療保障,自掏腰包。2011年,由於身體器官衰退,李鳳鳴有時候會大小便失禁。
此時,兒女卻陸續離她遠去。
2005年3月,大兒子陽社成再婚,妻子在城裏開了一家小百貨店。婚後,陽社成搬離朱家嶺,住在百貨商店裏,工作之餘幫妻子照看店舖。
二兒子陽定成原是耐火材料廠職工,也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年代買斷工齡,隨即下崗。
陽定成是陽家唯一一個大酒量的人。其他的兄弟姐妹滴酒不沾,他能喝一斤白酒。後天“鍛鍊”出來的酒量,讓他在下崗後迅速融入市場。2000年後陽定成在弟弟陽祝成的介紹下到長沙做銷售,酒桌上的“本領”讓他在短時間裏積累了第一桶金。2010年6月,陽定成在縣城買了新居,三室兩廳,140平方米。
山腰上的陽家老宅終於只剩下李鳳鳴一個人,住在最東側3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裏。其他空房,偶爾會有商販租上一年半載。
小兒子陽祝成于2003年辭去了冶金廠的工作,在長沙遊蕩3年後,遠赴天津,在一家建築公司打工。一年到頭連妻兒也見不著幾次,更不用説寡居家中的母親。
女兒偶爾會接李鳳鳴去她那兒住,有時也勸她:“你一個人在老屋裏住著,也沒人説話,要不就在我這兒長住吧?”李鳳鳴沒有答應,也沒有否定。在女兒家住了幾日後,她便覺不自在。嶄新的被子蓋在身上,她怕弄臟;乾淨的地板,她踩在腳下怕滑倒;好吃的飯菜擺在眼前,她卻提不起胃口。
李鳳鳴還是回到了老宅。小兒子陽祝成提出要帶她去長沙,她也只是去待幾天,看看小孫子。10天不到,還是回到老宅。
“老人年紀那麼大,萬一哪天真走了,在屋子裏臭了,我們都不知道。”陽社成每次提起母親的事情都很生氣。雖然他住在店舖裏,離母親最近,也是照顧母親最多的人。2011年以前,他每星期回家看一眼李鳳鳴,2011年後,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去看看,給母親買點藥、買點菜,他能做的也只有這些。
2012年春節,家人相聚。弟妹3人提議每人每月給大哥200元,讓他全權負責照顧母親。陽社成覺得不妥,“我現在還要交社保,600元僅勉強夠吃”。陽社成還想趁自己有力氣,再幹幾年。思前想後,兄妹4人最後決定:“每人一個季度,大家輪著照顧母親。”
2012年2月,陽社成首先開始照顧母親,5月將照顧母親的“接力棒”交給老二陽定成。陽定成忙於銷售,照顧李鳳鳴的事情多由其妻代理。
為了照顧李鳳鳴,陽祝成辭去了天津的工作,回到長沙。但是他還沒想好,到時是接母親去長沙住呢,還是自己回冷水江,“不是折騰母親,就是折騰自己”。
(趙佳月魏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