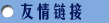沒想到淪落成這樣子
淩裕昌帶我們走進他的屋子時,有些窘迫,他坐在椅子上猛抽起煙來。碗裏的馬鈴薯已經發黑了,依然插著勺子和筷子,臉盆躺在房中間,一塊鞋墊漂在洗衣板邊上。日曆還停留在2006年8月19日,父親去世的那一天。一切都很固執的樣子。
他,一個57歲的男人,堅持著來自某個時代的尊嚴、價值傳統,力爭體面。在瀋陽這座冬天氣溫可低至零下20攝氏度的城市裏,這房子沒有暖氣。他説暖氣不暖,所以停了,還説,冰箱有魚兒呢。
從淩亂的雜物堆裏,他翻出一本瀋陽總工會給他頒發的“優秀積極分子”證書,上面寫著他取得了“顯著成績”。那時,他是單位的技術骨幹,中國職工技協會員證他還隨身攜帶著。
“看,我的專業是焊接,不是水電焊。”在他的解釋中,焊接是一項專業,而水電焊則是家常維修技術。他説,下崗後,自己從未上街掛牌從事廉價工作,而是被請去解決各種工程問題。
可如今,那些焊接工具,像是房子裏那些枯萎的塑膠花靜靜呆在角落。近年來,他的視力日益下降,身體被曾引以為傲的技術淘汰了,轉而當上“大齡保安”。
2011年9月,母親也去世了,給他留下了國企時代的福利房,那幾乎是他唯一的資産。錢,給母親治病養病時花了,在做生意時被卷走了。曾經的妻子,早就離他而去。他孤身一人,終於意識到——自己老了。
這年晚些時候,他得知,補繳養老保險的窗口將在年底關閉——正如千千萬萬下崗工人,2002年企業倒閉時,也停止為他繳納保險。他必須找到新的單位,否則就得負擔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的繳納部分——1992年,隨著國企改革,中國開始建立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從前由企業負責的職工從此逐漸被推向了社會。
失去單位的淩裕昌再沒有繳納過養老保險金。2011年年底,他到社保中心諮詢,對方給他算了一筆賬,單子上寫明,必須繳納欠款43311元。
然而,月薪僅1200元的他拿不出這筆款項。借錢,他開不了口,也沒有十足的把握。他拿著單子去追債,喊著我下半輩子全押在這了,仍收不回錢。後來,聽説補繳窗口又延遲3月關閉,他想到賣房子。可是,期限到了,房子還賣不出去。養老保險只能擱下了。
“我從未想到,我這一生,最後淪落成這樣子。”如今,他別無他法,唯有等待。再過3年他就退休了,儘管並不了解養老保險制度,但他以為這該也像其他許多政策一樣,總是變幻莫測的。也許,船到橋頭自然直吧,他想。
一疊福利彩票,散落在床邊。
繳納養老保險是件奢侈事
淩裕昌的房子坐落在瀋陽第三糧庫職工宿捨得院子裏。這座曾經擁有三千多員工的糧庫已經變成一座樓盤,據説房價已經漲到8000元每平方米。樓盤俯瞰著隔壁低矮的職工宿舍。院子裏,一群下崗工人呆坐著,蹙著眉頭沐浴下午的陽光。
52歲的王繼宏已經10天沒有工作了。每個晚上都在下雨,他不能到空地上製造人們需要的器具。而隨著新樓拔地而起,平房時代的煙囪被逐步拋棄,找他鑄造的人日漸稀少。現在,年紀越大其他工作越不好找。可他得在喪失勞動能力之前,給即將到來的老年做好儲備。有時,整個冬天,他都呆在家裏。閒下來的時候,失落感便裹挾著一股怨氣勾起他對往事的回憶。
“2000年,那天9點鐘,我換上工作服剛要工作,廠裏突然説召開大會。全場的人擠在一起,幹部也都到齊。突然,他們宣佈:‘你們快去辦理失業證,簽合同準備下崗了。’突然間我們就集體下崗了,大家都哭了起來。”王繼宏越説越激動,簡直要哭起來了。妻子拉住他,説:“別讓人聽見啦,整個院子都是你這樣的人。”在當時,國家提出“3年內搞活國有企業”,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企業裁員、破産及倒閉。數以千萬計的國企工人承受了這一切。根據政府統計,1998—2003年,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2818萬人。瀋陽鐵西區,曾經集中了80%以上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輝煌工業區,一夜間成了有名的“虧損一條街”。將近70萬下崗職工無所事事,群居在這個39平方公里的傳統重工業區。他們揣著買斷工齡的錢,有的幾千,有的幾萬,開始艱難生存。
一切都和承諾的太不一樣。關於下崗再就業保障,按政策規定的“三三制”經費籌措原則,企業是最薄弱環節,下崗職工集中的企業大多處於停産、半停産狀態,資金早就捉襟見肘。在政府安排的再就業中心,生活保障金難以分發。
一位民營老闆還記得,他當時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中央領導來檢查再就業情況時,就要到再就業中心扮演下崗工人,向領導彙報他所獲得的社會保障以及對未來的信心。
再就業顯得如此困難。當下崗工人被拋向社會,他們大多已邁入中年,難以找到穩定工作,只能零零散散、斷斷續續做點小工,或是在街邊擺小攤,還得應付城管的檢查——那些年裏,還流傳著下崗工人被逼刺死城管的故事。何況,都是失業工人,常常是“賣菜的比買菜的多”。
王秀增也是糧庫的下崗工人。當年他接受了下崗的命運,積極學習開車技術。然而,好不容易才托關係成了計程車司機,不久卻遭遇了搶劫,背部被戳了兩刀,錢也被搶光了。一家溫飽還得靠他來支撐,只能繼續開著,沒過幾天,又在計程車裏找到另一把尖刀。
如今,這把刀還收藏在抽屜裏,王秀增的妻子何文蓉拿起來向我展示,她至今還感到毛骨悚然。這個家庭,保持著卑微的溫暖。想起這些年見過的家庭悲劇,她唏噓不已。她説,在當時,女性就業如此艱難,一些女工只能陪人跳舞,10元3曲,“任人想做啥就做啥,丈夫不高興,大多數人就這麼離婚了”。她説,這些年來,自己就一心一意跟著丈夫吃苦。表揚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又補充道:咱姿色不好,也沒法去跳舞。
生活給了這個家庭小小的饋贈。隨著哥哥做起企業,王秀增也幫著打工,在哥哥的幫助下,還補上了養老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那是下崗後,心裏第一次有了踏實的感覺。
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説,生活只能永遠與當下週旋,繳納養老保險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他們懼怕老無所依但卻無力購買。
“在制度的安排中,他們一再被剝奪。由於結構性問題,他們難以再就業,而社會保障制度又寄希望於再就業,希望就業後就能有養老保障。社會保險安排和生命週期都發生了錯亂,困境就會很大。”清華大學的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説。2004年,她作為清華課題組的成員之一,來到長春和瀋陽對這一群體進行調研。
歷史的負擔
“兒子上大學就不能交保險,交了保險就上不了大學。”離退休年齡只有3年的何文蓉這麼概括她的矛盾,在兒子的前途和自我的保障之中,她選擇了前者。事實上,2006年,兒子上高中時,她就中斷了參保。那時,一家三口和老母親擠在35平方米的房子裏,全家都把希望寄託在這個未來的大學生身上。何文蓉心疼兒子,節衣縮食照顧他。
後來,兒子考上三本大學,每年須繳納1萬元的學費。老人家咬咬牙,把多年積蓄的養老金拿了出來,供孫子上大學。生活費則由孩子的姑姑阿姨和爺爺共同負擔。王秀增2000元的生活費是這樣分配的:老保和醫保費500~800元,400元給兒子作為生活費,剩下和妻子每月六七百元的收入一起負擔家庭的開支。
3年後,老人查出癌症。王秀增只得拿出下崗時近萬元的買斷工齡費,也給兒子交了學費——多年以來,那都是他們的不動款。缺乏保障和穩定的收入,他們得隨時準備著應付生活中的危機。
這家人的命運和他們的賬目一樣精打細算,總和危機擦肩而過。兒子畢業沒幾個月,老人去世了,為母親辦喪事,王秀增踢到了門。難以忍受的疼痛讓他上了醫院,這才發現,3年前一場忍著不看的病意外地讓腳骨頭壞死了。他再次失去了工作,住院看病,養起身子來。好在,兒子總算找到工作了,雖然只能拿上一千多元的工資。
陽光下,48歲的王秀增坐在院子裏養傷。他每天都幻想著退休。那時,他不必為工作、為明天憂愁,能有穩定的養老金收入。儘管沒有一個人知道,也沒有人為他們算過,自己將來能領到多少錢。只有到退休那一天,答案才能揭曉。可是60歲看起來是那麼遙遠,他沒法想像這12年裏,時代、生活或命運,將會發生什麼變化,會把他帶到哪兒去。
對於靈活從業人員,養老保險金是以在崗職工月均工資為基數來收費的,這些年,他應繳的保險金不斷上漲,因為月均工資不斷上漲——瀋陽市這一數據從2006年的1949.3元上升為2011年的4189.9元。而物價也在不斷飆升。
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所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率也隨著漲。2005年國務院的38號文件,把靈活就業人員的養老保險的費率從18%提升到了20%,把繳費基數從在崗職工工資的60%提升到了100%。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保障研究中心資深顧問研究員陳仰東看來,“這個調整對靈活就業人員的續保能力造成了很大影響。雖然制度上是多交多得,但是這麼高的費率和費基,同下崗人員的繳費能力是不相適應的”。不過他又補充,有些省市自作主張地規定可以選擇按社會平均工資的60%、80%來交,“雖違背中央,但有合理性”。
陳仰東認為,政府的負擔重,造成了現在費率高。“已經達到了警戒線,不能再升了,但是由於統籌的部分還是不夠,不升不行。這也是歷史的負擔造成的。”
1992年後,國家將國企職工的養老推向市場,給社會保險帶來巨大的養老成本。財經作家吳曉波曾寫道,在1998年前後,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賬的數目進行過估算,比較接近的數目是兩萬億元。
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包括吳敬璉、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過財政部長的劉仲藜等人便提出:“這筆養老保險欠賬問題不解決,新的養老保險體系就無法正常運作,建立社會安全網、保持社會穩定就會成為一句空話。”2000年初,國家體改委曾設計了一個計劃,擬劃撥近兩萬億元國有資産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賬戶,然而,幾經波折,這一計劃最終還是流産。反對的理由是,不能讓國有資産流失。
然而,吳敬璉早在1993年就説過:在國家承諾包攬國有企業職工的養老、醫療等保險,實行現收現付的情況下,職工的社會保障繳費在發放工資以前已經作了扣除。這筆錢積累在國家手裏,用來興建國有企業,職工不需要也沒有個人賬戶積累。因此,當老職工的養老保障由現收現付制轉向統賬結合製時,政府就必須履行原來的承諾,按照國家與職工之間的隱性契約,將原來上繳給國家已移作他用的這部分本屬於職工養老、醫療等的費用返還給他們,一部分用於增加社會統籌基金,一部分用於做實“老人”和“中人”的個人賬戶。只有這樣才能正式啟動和正常運作新的制度。到了2006年7月,吳敬璉仍在呼籲:“另外一件事,是歸還國家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這件事也是目前的國家財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他點評道,“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可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到了王秀增這裡,一切都只能現實地去承擔。他最清楚的一點是,自己的勞動力越來越貶值,近一年來,它幾乎回到了原點。所以,當不久前聽聞延遲退休的消息,他驚叫起來,那簡直是要我的命!他開始後悔自己重新續上保險,開始覺得那像是巨大的無底洞,不知何時把他吸幹。他還試圖算清楚,這是一筆怎樣的賬,但很快就放棄,因為,對這套體系,他知之甚少。
“過一天算一天吧,慢慢熬吧。”這是他給出的終極答案。生命有時如此脆弱,在他的同學中,去世的病重的,竟佔了一半。而每一個隨時來臨的意外,都能把眼前的平衡擊碎。
看到大家在訴説生活的煩惱,76歲的李奶奶湊上來展示她的傷痕。人們多半聽夠了“祥林嫂的故事”,紛紛興致黯然地散開。
她的故事很悲慘。兒子下崗後,打工遭遇瓦斯爆炸,渾身被燒傷,喪失了勞動能力。以後他常和妻子吵架,又懼怕離婚而被拋棄。貧賤悲哀的生活中,一家人吵架不休,甚至還動起手來。
她把退休金一點點積攢起來,靠撿垃圾維生。她説她一千多元的退休金得供養孫女上學,得隨時準備著給兒子交養老保險,以抵禦他被拋棄的風險。
老人邊説邊哭,如今,她擔心養老金和房子成為爭奪的對象,她甚至總想像自己被迫害。她一心等待兒子的退休,那一天到來,便是她的解脫。
沒底兒
等待退休,對於這一群體而言,意味著不同的內容。對於董阿姨來説,等待從一下崗就開始了。在她所描述的年輕時代,她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而驕傲。那時她簡直想著永遠幹下去。退休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因為那意味著衰老和自我價值的喪失。可是,下崗那些年裏,丈夫有一天沒一天地幹著搬運活,自己則做保姆、搞清潔,受過冷眼也遭遇失落。現在她甚至覺得只要有保障,衰老也是一件值得等待的事情。
當然,她也會保持著容顏的體面。她會化上淡粧,戴著黑絲手套走在馬路上。她以自己的理解試圖和這個時代顯得匹配,可她看著城市在發展,自己和它卻變得越發陌生。她忘了這座工業城市是什麼時候怎麼變成今天這樣子的,依稀記得2008年之後,感覺就不大一樣了。統計數據顯示,這一年,房地産開發投資額高達1010.91億,比上一年多了接近三百億。
媒體也在傳播關於這個城市的美好現狀,2011年《華商晨報》的文章稱瀋陽每人平均GDP近一萬美元,超過了世界平均水準。
可是對於董阿姨而言,城市越發達,自己越窘迫;越開發,自己越狹小。“過去吃爛蘋果,現在還是吃爛蘋果,過去擠在30平方米的房子,現在也還是。”她説風水輪流轉,甚至羨慕起農民來。如今她的世界幾乎只有女兒了,她會對女兒説:媽媽就是為你而活的。
2006年,遼寧省實行“4050”(女滿40歲,男滿50歲)社會保險補貼政策,財政按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60%給予補貼。她那時剛過四十歲不久,終於享受到這一政策,將養老保險補辦了。如無意外,再過兩年,她夢寐以求的退休生活就要到來。那時她領著退休金,女兒也將考入大學。命運安排得剛剛好。她只能祈求一切都平穩地抵達。
祈禱之餘,董阿姨也為好朋友李英俊惋惜。李英俊44歲,沒等到50歲,“4050”政策便關上了大門。1992年,李英俊並不知道辦養老保險的政策,等到1998年下崗,單位已經不願意幫他補交了。而他也就從未繳納過保險金。
在他看來,領到退休金,意味著“重新有了單位”。下崗這些年,他一直琢磨著為自己購買未來的保障,然而,排在那前面,還有許許多多的事。他努力掙錢,賣過雞蛋,賣過皮鞋,做過木匠……他供兒子上大學,甚至供完大學還為他買房結婚。當他開始為自己考慮的時候——妻子查出了白血病。很快,所有的積蓄花得一乾二淨。
妻子死去那年,他還沒從悲傷中恢復過來,就發現自己也患上了丙肝。這意味著,他再也不能工作了,醫生説他再不休息,就會有生命危險。
此後便是漫長治病。每個月治病就要花掉一千多元,兒子拿出1000元,母親拿500元,開始供應他。拿著母親的錢,他心裏不是滋味,畢竟,父母還要照顧他病退的弟弟。
治療持續了一年多,他就終止了。年後,他去復查,自己不敢面對結果,讓董阿姨幫他取結果。他站在醫院門口等待。取結果只需10分鐘,可是董阿姨去了半個小時也沒出來。
那30分鐘無比漫長,他抽了一支又一支的煙,他想,估計病白治了。他心裏快速算著幾筆賬,過去的投入,以及以後的投入。算到後來,他狠下心,決定不治了。一種絕望感涌了上來,立刻,牙齦腫了,眼睛也紅了。
後來證明,不過是命運開的一個小小的玩笑。結果顯示他康復了,只是那天,醫院恰巧人太多了。後來李英俊想起這一幕,覺得它集中體現了過去十餘年的生活——沒底兒。他開始想過上有底兒的生活。於是,在家休養的日子,他琢磨起養老保險制度來,他想算清楚,自己該借多少錢?何時能真正受益?自己還能活多少年?可似乎,他也弄不清楚具體的計算方法,而政策,似乎總在變化,數據也在不斷地飆升。比方説,他看著平均工資漲到三四千,他琢磨自己是零收入,別人怎麼能那麼高?他並不知道,月均工資是不將他這樣的人納入其中的。比方説,他看報紙,説老齡化給制度帶來的壓力,説空賬運轉,他又擔心,空賬了,錢都哪去了?現在的年輕人交保險嗎?以後能把錢拿回來嗎?系統會崩潰嗎?自己的老父母拿的也是社保發的退休金,但他們並沒有買保險,錢從哪來呢?一系列的問題,他沒能搞懂。
事實上,支付老職工的這筆養老費用,形成了對老職工的鉅額社保歷史欠賬。由於“老人”、“中人”的“視同繳費”賬戶是“空賬戶”,社會統籌基金中也沒有他們的份額,所以不得不使用轉制後為“中人”、“新人”繳納的社會統籌基金為退休職工發放養老金。統籌基金不足部分,被迫挪用“中人”和“新人”個人賬戶的資金,從而又造成了大量新的個人“空賬戶”。據稱,截至2008年底,個人賬戶空賬運作的規模已經達到了1.4萬億元。
陳仰東説,2000年以後提做實個人賬戶出來的,其實就是用國家財政去還歷史債。“已經試點10年了,還在試點。這就證明背後是有問題的,國家當年的承諾就很不清晰,沒有説補一個明確的數字,也遲遲看不到明確的效果。”
2000年在遼寧省、2005年在吉林省和黑龍江省先後實行了做實個人賬戶試點改革,以期實現部分積累制。但8年以後,遼寧省又允許借支賬戶基金,似乎做實個人賬戶難以實行,惡性迴圈難以打破。
於是,李英俊又糊塗了,一會報道説存在空賬,一會又説沒空賬,一會説延遲退休,一會説不延遲。在找“底兒”這事上,他又重新“沒了底兒”。
“你説,真的能延遲嗎?”他問。
兩眼一抹黑,完了。
“不會延遲。”朋友王紹剛回答他。
“你怎麼知道呢?”
“因為有很多人反對。”王紹剛似乎更願意相信電視上的民意力量。
這天,在王家,李英俊還得知了2012年3月後再也不能補繳養老金的資訊。李英俊一拍桌子,説:“我更不要交了!”可過了一會,他又懷疑,這興許只是吸引人們繳納保險金的策略呢?
王紹剛表示贊同。但他當時仍是害怕沒法補上。作為特殊工種的工人,那時他離55歲的退休年齡只有兩年,自己又得了糖尿病,視力模糊,勞動能力幾近喪失,便向母親借了5萬元拆遷得到的賠償費,將保險補齊了。
瞅著眼下養老保險金又漲到了700多元,連同醫療保險和看病,一個月要花1500元,所幸妻子還有1800多元的退休金和1000元的保姆收入。他想著,咬牙再撐上一年多就好了。
剛聽到延遲退休年齡的説法時,他兩眼一抹黑,只跟李英俊説了句:“完了,哥。”這意味著還得多熬5年。5年是一個不敢想像的概念,還不知保險金漲到哪是盡頭。
“延遲退休,説學國外的。什麼不學,就學這個?”王紹剛説,他想起下崗這些年所受的委屈,想起自己的身體,“不知還能活多久呢”,可過一會又寬慰起來,“反正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大家不都這樣?”
“延遲退休無疑將加劇下崗群體的困境,”郭于華想起2004年的那些調研結果,不僅沒有過時,所提出的問題,還一一應驗了。“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要通過制度的變革糾正過來。養老金有缺口,前期社保有問題,不能説去剝奪那些弱勢群體。目前國家實行養老雙軌制,延遲退休只會進一步讓下崗群體處於更不利的位置,而對政府部門更有利。養老保障不能雙軌制,不能讓強的越強,弱的越弱。”
可是,王紹剛似乎對雙軌制並不很憤怒,畢竟,自己的孩子去年考上公務員了。那個崗位只招了兩個人,王為這“全省第一名”而驕傲異常。
這些天,聽到反對聲後,他又覺得,推遲退休是遲早的事情,但也許他能僥倖躲過,“90%以上的人反對延遲,它敢公然實行麼?政府不也説了暫時不會延遲嗎?”暗示的聲音越來越響亮,離退休只有一年半,他想著一年半應該在“暫時”的範疇內。
還有一年半,就要熬到頭啦。甚至還竊喜,到那時,不僅不用繳納1000元,還能拿到2000元,等於是掙了3000元啊。一生中最幸福時刻就要來臨了,那將是送給自己55歲生日的禮物。
他還盤算著,也許搬離這破落潮濕的小平房的日子也不太遙遠了。整個城市在以空前的速度刷新面貌,高樓的步伐正在朝他逼近,等待他的,將是一筆拆遷補償,或是某個嶄新的房間。
那時,他將告別這一切,告別所有痛苦的過去。過去10年,他努力維持著外表的體面。“你到這條街看看,誰都體體面面,因為誰也不會訴説痛苦,説了也沒用,痛苦只有自己才知道。”他説。
新樓房,新面貌,當工廠拆遷,舊房拆遷、人群散去,他們就都消失在各自的世界裏,一代人的記憶似乎也便隨著消散。
在鐵西區,曾經密密麻麻的煙囪被密密麻麻的樓房所代替。從某些角度望過去,你會以為到了香港。只有廣場上兩個舉著鑰匙的工人塑像,只有冷清的博物館,提醒著曾經有過的輝煌。而那些只在10年前上演的悲歡離合、一望而盡的蕭條、被拋棄的生命、等待的煎熬,也被拆遷到不為人知的角落。
眼下,人們在這裡打麻將、跳舞、耍雜技。隨便的表演,都能吸引為數眾多的人群面無表情的圍觀和漫長的等待。
我想起淩裕昌,這個還沒從驕傲裏走出來的工人。這天,他帶我們來到過去的工廠,那裏只剩下一個銹跡斑駁的鐵門及一排小平房,還遇到從前的同事。兩人一下熱絡起來。而幾年前,他來到這裡的時候,因為這位前同事對他“不客氣”,他還把人家修理了一頓。
在過去,他遭遇身份的失落,如今,他要面對身體的失落。可他得接受這一切,想法安置無法避免的衰老。他還得工作。他小心翼翼走過一段泥濘的被掀開的地面,來到一棟空蕩蕩的舊樓。看不到一個人,甚至聽不到一點聲音。大多數時光,他在這裡度過,只有一台收音機和一隻電飯煲陪伴著他。他和另一個看守的人交了班,在門口走了下來。我們約定,第二天交完班後,和其他工人去拍照。
第二天,他沒出現,他仍得在那空樓獨自看守。他沒有等到來接班的人。
(林珊珊詹青雲)
(感謝杜強先生、馮翔先生、張啟亮先生提供的幫助。應受訪者要求,王繼宏、王紹剛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