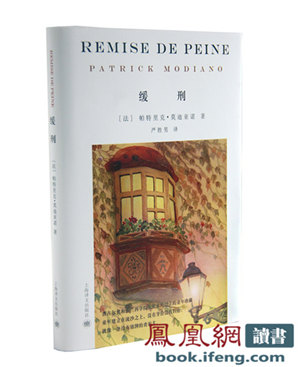
諾貝爾文學獎、龔古爾獎、法蘭西學院大獎得主的童年珍藏
童年建立在流沙之上,沒有身份沒有歸宿,就像一條沒有銘牌的喪家犬
書名:緩刑(REMISE DE PEINE)
作者:[法] 帕特裏克�莫迪亞諾 著(Patrick Modiano)
譯者:嚴勝男
這是一座二層樓的房子,正面的墻上爬滿了常春藤。英國人稱作“凸肚窗”的一扇凸起的窗戶延伸了客廳的長度。在花園的一座平臺的深處,吉約坦醫生的墳墓掩映在鐵線蓮之中。他曾經在這裡改進他的斷頭臺嗎?
年少的“我”和弟弟寄居在這棟屬於三個女人的別墅裏。週遭的成人世界充滿了謎題:房子為什麼沒有男主人?阿妮為什麼整夜哭泣?洛裏斯通街的那夥人在幹什麼買賣?科薩德侯爵是否會在半夜回到城堡?“我”在看,“我”在聽,“我”在想,到底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及至人去樓空,再無蹤影?
但“我”知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因為警察來了。
【作者簡介】

作者照片
帕特裏克�莫迪亞諾是當今仍活躍于法國文壇並深受讀者喜愛的著名作家。1968年,莫迪亞諾發表處女作《星形廣場》,離奇荒誕的內容和新穎獨特的文筆,使他一躍而成為法國文壇一顆熠熠閃光的新星。他的文學才華受到評論界的矚目,該小説獲得當年的羅歇�尼米埃獎。嗣後他接連發表了多部作品,幾乎部部獲獎。1975年的《淒涼的別墅》獲書商獎。1978年的《暗店街》獲龔古爾文學獎。2010年的《地平線》獲得了西蒙娜和奇諾�德爾杜卡基金會之世界獎,米蘭�昆德拉、略薩、博爾赫斯等人也曾獲此獎。
【附錄】
序言
作者:奧利維埃 亞當
第一次讀《緩刑》我還20不到。那次閱讀經歷恰巧——差不多吧——和我與莫迪亞諾的作品結緣的時間重合。我不知道先讀了哪本。可能是《蜜月》。《消失了的街區》。《廢墟中的鮮花》。抑或《環城大道》。我不知道。但記得是其中一本。我記得,某個早晨在於維西 火車站的華榭書店裏,我哥隨手買了一本口袋書,他當時在巴黎攻讀法律,他本想在去學校的路上讀的那本書落在了家裏。我記得,他闖入我的臥室,淡黃色的墻壁上貼了一張海報,此刻舊事重提,倒覺得這張海報“出人意料”地頗似莫迪亞諾的風格:神秘的外墻,樹莓縱橫,常春藤蔓延,這是一棟人們想像當中的巴黎別墅,亮著燈的窗戶、高高的柵欄門、影影綽綽的花園、模糊的剪影、痕跡、令人浮想聯翩的生活片段,這個畫面活脫脫就是《緩刑》裏面出來的,不過別墅的位置不太像是獨屬於作者的那個隱秘的巴黎,倒更像是遠郊,“那時候那裏還沒成為遠郊”,是一個個寧靜富庶的小鎮,消失在田野間,我看到過這樣的風景,在一次去埃松省參加鋼琴考試的路上。我記得,他把書給我,對我説:“喏,你應該讀一讀這個,你會喜歡的。”
我聽了他的話,就此沉溺其中,永永遠遠,那種奇妙和眩暈隨之而來。當然,一切已然在那裏:街名、電話簿、重疊的時空、模糊的倩影、銷聲匿跡、不可告人的過往、和納粹合作的污點、洛裏斯通街的暗影、四處遊蕩的調查、可疑的訪客、孤獨、遺棄、行跡存疑打零工的父親、在巡迴演出之間奔波的當演員的母親、沒有戶口簿、靦腆和優雅、壓抑的恐懼和痛苦、模糊地帶和黑洞,最後是這整個神話故事,珍貴獨特,用迷樣的句子寫就,用憂傷輕盈、無與倫比的嗓音念出,但這個故事極為簡單,沒有鮮明的個性、沒有驚世駭俗、沒有絢麗的外在印記。日子一天天過去,我跑去圖書館囫圇吞棗讀完了所有莫迪亞諾的作品。之後,我去聖米歇爾區的折扣書店淘書,連著幾個月省下飯錢,我漸漸補全了他的舊作,開始追他的新作:我翹首期盼著,幾乎每年一部,此後從未爽約,他的新書沒有讓我失望過,恰恰相反,每每讀完一本,等待下本出版的迫切之情就更甚一籌,我迫不及待想要揭開那層薄紗,我們總以為會在下本書中做到這點,最後卻發現還籠罩著另外的層層薄紗,人們急於親自揭開,卻無從知曉這最終是水落石出還是疑雲漸濃……閱讀莫迪亞諾的那段時日在我的記憶中是一段驚奇連連、歡欣雀躍的日子。
那時我初到巴黎,上課的地方離布洛涅森林不遠,我流連于拉丁區和聖日耳曼德佩區的書店、藝術實驗電影院,偶爾在別墅區的幽靜小道上會會朋友,這裡更有資産階級的味道,比起每個週末大區特快D線把我帶回去的那個家。我在他的小説中嬗變,在他的小説背景中漫步,我就是他筆下的一個人物,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個人物的兄弟、後代。我的生活和那些書互有關聯,互相滲透,書為我的生活抹上一層色彩,重新解構,使之變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虛與實的界限。兩者嚴絲密合:那些地方,過著雙重生活的印象,燈火通明的樓房底下長長的階梯,樓房大廳裏看見的人名,這一切都處在特殊的光亮中,這光亮屬於現在,一個滿載著過去並投向未來的現在,一個朦朧不定的現在。
我的私密地圖在演變,在更改,一層層疊加在我的出生地之上(當然在主城之外,在郊區),疊加在我此後不斷成長的土地之上,疊加在被莫迪亞諾的小説重新描繪、重新定義、重新創造的土地之上。我到處搜尋那個瘦高的身影,我總是關注作品而非作家本人,我有喜歡的書,但居於幕後或者融入其中的作者不是我的興趣點,但我總覺得會在不同的地方見到他,在盧森堡公園邊上、在維克多 雨果大道上、在布洛涅森林的池塘邊,可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直到幾天前,正當我準備提筆寫這篇序言時,我在樂蓬馬歇百貨公司的書店裏,在一堆書架中看見了他,既清晰又迷茫,穿著米色的長款雨衣,就像一個眼色、一個徵兆、一個奇怪——或者如他所説“古怪”——的巧合。我當然沒有上前和他攀談,我不敢。但我有了這樣的幻覺,我知道了他在我心裏的重要性,我對他的欽慕之情,我已經把他提升到神話的高度。再説了,退後一步來審視,我可以細細掂量在我巴黎頭幾年的真實記憶當中到底混雜了多少那段時間我如饑似渴吞下的莫迪亞諾作品中的內容,這兩種“敘述”——其一已經消逝但屬於我個人;另一個盤桓在字裏行間,我不是作者,這些文字也和我沒有任何關係——到底盤根錯節到何種程度。這就是莫迪亞諾作品的力量,它能直抵你的最深處。它融入你的生活,直到無法厘清。這段日子重讀《緩刑》,我才發覺這一切鑄就了我現在的精神格局,及至我作品的背景、內容以及遣詞造句,即使只有我能感覺到,即使這種影響的鮮明痕跡幾乎隱而不見,或者説這種痕跡太過隱蔽,無法為外人察覺。因此,莫迪亞諾的影響力是根深蒂固的,他的書佔據了專門一層書架,和其他對我意義非凡的書放在一起,其中有安妮 埃爾諾、雷蒙德 卡佛、亨利 卡萊的,收藏後幾位作家的書或者是出於其他動機或者是要表明另外的主張。這些在書架上緊緊挨在一起的作家從根本上動搖了我,改造了我,改變了我,包括作為個體的我和作為作家的我。
距離第一次讀《緩刑》已時隔20年,20年後重讀,我想要追回這無法追回的蹉跎(和誰有關?關於什麼?是要消減何種冒名頂替的感覺以及非法的印象?),我一直沒有時間重讀那些塑造我的書和作家,記性又不太好,我總是覺得在抹去以往的痕跡,我步步向前,卻困擾于遺失的東西,這個持續的黑洞不斷變大,我驚詫于這本書竟然留下了如此之多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印記,是應該重提莫迪亞諾了:莫迪亞諾和他弟弟居住的房子,這是父母留給他們的,儘管這對父母不太像父母;爬滿常春藤的外墻以及周圍的街道;進進出出的女人;學校裏的夥伴;科薩德侯爵的廢棄城堡;馬戲團和意外事故;美國産的轎車;牛仔外套;夜總會的名字;父親的露面;巴黎的修車行;成人團夥,只能依憑跡象、散落的碎片、通常無解的只言片語來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形跡。照此説來,這種稍稍令人不安的遺棄感、隱約的焦慮感,還有那份不真實感,于我而言就是童年的代名詞,童年建立在流沙之上,不斷從指間流走,充滿不確定,既無外廓也無中心,猶如疏鬆的泥土,我們在其中盲目前行,只能抓住殘言斷片,陷入“存在”與“缺席”這兩廂糾纏的麻團中,就這樣走過了少年時代,動蕩、模糊,沒有身份沒有歸宿,就像一條沒有銘牌的喪家犬。這種感覺,莫迪亞諾在另一本書中 也描寫過,似乎也非常契合《緩刑》,勾勒出小説的遠景和故事大綱:“我將要提到的我頭21年的那些事情,我是在混沌中經歷的——這種生活方式能讓一幕幕遠景迅速略過,而演員卻靜立在攝影棚的平臺上一動不動。我想詮釋出這種感受,在我之前已經有很多人感受到了:萬物流逝,模糊不清,我無法再過我的生活。”
參照莫迪亞諾之後的作品,特別是那部他盛情邀請我們解讀的《家譜》,《緩刑》在莫迪亞諾的所有作品中擁有別樣的色彩,獨具一格。首先,這是一部少見的開誠佈公的自傳性文本,甚至讓我們産生了錯覺,以為莫迪亞諾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上演自己的生活,並且趁此機會搖身一變為感人的“帕托施”——因為他難得地親密、親切,小男孩用精準和猶疑的口吻回顧起一段童年往事,我們後來知道這就是莫迪亞諾的童年,動蕩的生活,寄居在父母朋友家中,而這些朋友又行事神秘、過往成謎,一邊在等待當演員的母親還有從事可疑勾當的父親,同樣可疑的還有父親的過去和行蹤,這一切或多或少是因為深陷在淪陷期的泥沼中,父親會連續數日、數周、數月渺無音訊或者不來看他們,之後又把他們送往別的地方,交托給別的人照顧。説到底,故事的真與假並非問題所在,令人激動的是那一絲光亮,那卸下防禦的敘事,呈于你的肉眼之下,明明白白,扣動人心。自傳體的脈絡顯而易見,但同時又赫然存在一個巨洞,交錯著許多的猶疑和疑問。就好像在鑽研一個他假模假樣解開的謎團。就好像,在莫迪亞諾親力親為的調查的最深處,他用證據向我們表明,故事沒有重新編排,它的表像、它的真實性,真實或虛構,都無關緊要,無從確定真相,無從解開疑問,無從判定曖昧。
莫迪亞諾的作品是在邀請我們參與到一場盛大的多米諾遊戲或揭面紗的遊戲中,自《家譜》出版後,我就執著于對它的閱讀,我代替作者繼續調查,並且附上了我的個人調查。一個調查疊加在另一個之上,這是一廂情願的行為。我猜想,隨著歲月流逝,紙頁翻過,每個讀者都在悄悄地進行著自己的調查。《緩刑》提到的小説背景大概佔據了一頁的內容。“在茹伊昂若薩和巴黎之間,那還沒成為遠郊的地方的秘密。傾頹的城堡前是雜草叢生的草地,我們在草地上放風箏。梅茲村的森林。水磨的巨大轉輪發出轟鳴聲,送來河水的清涼。”“來來往往的奇怪女人【……】其中有齊娜 拉科夫斯基、蘇珊娜 寶萊、叫“弗萊德”的女人、卡羅爾馬戲團的經理、蓬蒂厄街上的夜總會,還有一個叫做羅斯—瑪麗 克拉維爾的女人,她擁有一家旅館,就開在老鴿棚街上,開美國車的女人。她們都穿著夾克衫和男鞋,而弗萊德,還戴了條領帶【……】一天晚上,【……】爸爸【……】問我以後想做什麼。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莫迪亞諾的書就像一個迷人的露天作業。每本都有雙層含義。你盡可以認為,在一部完結的作品的最大續航能力範圍中,它已經完結,同時又把它當成一塊全新的拼板,屬於一幅還沒完工的大拼圖,一些部分仍然“空著”,另一些部分已初具輪廓,愈發精確。精確的部分當然和莫迪亞諾的父親有關,他是這位作家作品中的大事件,我們在《緩刑》中又捕捉到了他稍縱即逝的存在,透過“洛裏斯通街”的往事,聽見了泄漏秘密的回音。魯迪,莫迪亞諾的弟弟,卻在整本書中是一個缺失的中心,一個振聾發聵的沉默。在《家譜》第44頁上,我們能夠讀到在他之後的書中再也不會提及的內容:“1957年2月,我沒了弟弟。[……]除了我的弟弟魯迪還有他的死,我想我在此處將要説出的一切和我沒有多深的關聯。”在《緩刑》中,讀來這一行行文字,讓人心痛、讓人揪心的正是這份回憶,轉瞬即逝又無處不在,靦腆、恰當的含糊其詞,不甚精確也無評論,小心翼翼,但這份回憶難能可貴,以至於帕托施的弟弟成了最突兀的存在。因此,《緩刑》才更加震撼人心,對比莫迪亞諾的其他作品,它並非是一部偏離主題的小品,有一個隱蔽的發動機在驅動它:鐫刻在紙頁上的,是兄弟間相處的朝朝暮暮,是一段回憶,在提起時還能説上一句:我和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