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藝女青年遇上臺灣農民
原標題:當文藝女青年遇上臺灣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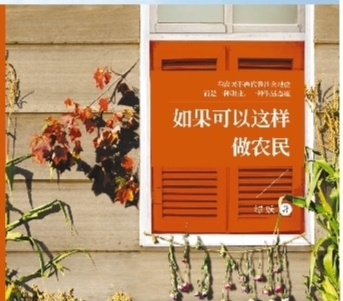
綠妖,著名的文藝女青年,當過編輯出過小説,其中《少女哪吒》還被拍成電影頗受好評。近日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了綠妖的新書——《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
這本書是綠妖的首部非虛構作品,她走訪了臺灣政府、10余個社會團體、60余位農民,記錄了臺灣農業發展的過去和現在進行時。
儘管創作《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時,綠妖把個人色彩降到很低,但她依然投入了大量的感情,寫書的過程中,綠妖感覺到自己在和這個世界建立了一種靈犀,她對記者説自己不再是個“死宅”的人了,“這個世界上沒有誰可以獨立存在,我會繼續非虛構寫作,因為人和人的交流,是任何的虛擬的技藝都無法替代的。”
綠妖寫農民,這樣的組合聽著有些“風馬牛不相及”,但綠妖卻樂在其中,甚至通過這次的寫作重新發現了自己在世間土地上的定位。
不管貧富,皆可怡然自傲
《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是綠妖的“命題作文”,是受《讀庫》的老六張立憲所托:“他給我打電話,問我想不想寫臺灣農業的書,我很吃驚,不知道是什麼觸動他做這個選題的。他説他有個臺灣朋友在北京,跟他聊起臺灣有一層基層機構叫農會,會做很多幫助農民的事。比如説水果熟了要賣枇杷的時候,農會就做個展銷會幫他們賣水果,場地費都是農會幫農民出。我和老六聽了怦然心動,覺得應該做這樣的訪問,但我不是出身農家,我自己五穀不分,所以我就和老六説:‘你找找有沒有更合適的人,如果沒有的話我可以去’。”綠妖笑稱她也不知道為什麼老六會想到讓她去完成這個選題,“可能他覺得我比較閒”。
接觸到這個題材後,綠妖先去北京的一個有機農貿市集,與那裏擺攤的農民交談,“先從了解本地的農民開始,有一個直觀感受,再去臺灣採訪,回來之後在圖書館也看了很多資料。我自我感覺,寫的時候更多是從記錄者的角度,不像梁鴻老師,她作為從事農業研究專業學者,是站在農村、鄉村內部角度去寫的。”
自傲,是臺灣農人給綠妖的深刻印象,不管貧窮富裕,他們都有一種怡然自傲之色。臺灣農民雖然也風吹日曬、面色黝黑,但是並無自卑羞怯之色,“我所見的大陸農民,尤其是出現在城市裏的農人,總有倉皇自卑的心理,沉默寡言。而在臺中鄉下,我列席産銷班會議,一個鄉村的微型社會結構呈現眼前,它內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來、技術學習,是血緣結構之外的另一種補充,我請教其中一人姓氏,該長者微微一欠身‘小姓姓黃’,舉止間的優雅矜持難以言喻,看似粗獷的書記,紀錄班級活動,竟是一手端麗雋拔的毛筆書法。”綠妖説臺灣農民不一定比大陸農民生活富有,可是他們有很高的自我認同,乍一看不算富裕,但內裏並不匱乏,他們的生活“樸素而殷實”。
對臺灣農民,梁鴻與綠妖感受一致:“我覺得在臺灣,説到農民的時候沒有那麼大的悲愴,沒有呼天搶地的感覺。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很平淡,農民就是農民,是一種職業,是一種生活方式,不是社會的病症,也不是感覺上的陳舊鄉村。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我們將來或者現在,哪怕是鄉村沒有了,當我們提到農民的時候,我們就僅僅把他還原到一個職業。”
綠妖同意梁鴻的説法,“臺灣農民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結合起來,農民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他們有反饋的渠道,也有發言的渠道,想要什麼他們也會去爭取。”綠妖説臺灣農村生態很豐富,以前有非常大的民間組織叫農會,在農會之外,這些年農民自己又建立很多,“比如説種地為主的就會有很多産銷班,交流技術,交流情感。經營範圍跨到了民宿,跨到了農家採摘,就會加入商圈,向政府爭取更多資源。還有的從城市向農村滲透的服務聯盟,會以購買、消費來實現他們想要的,就是我給你的價格好一點,但是你要給我沒有農藥,有機的産品,他們以消費者的力量實現他們想要的綠色食物,綠色土壤。還有像楊儒門那樣的監督者,像一個牛虻,時刻停在政府的脖子上,看見不對就上去咬一口。”
興致勃勃地種地,是一種生長的力量
綠妖的採訪者之一劉昌煬説:“臺灣有句話:吃水果拜樹頭。你吃這個樹的水果,有機會時給它上一根香。臺灣的土地,都有皇天后土,農民會給土地燒香,不管賺不賺錢,這個土地養育我有恩,我照顧它、它照顧我。”土地對一個農民來説,不只是他自己的一輩子,還意味著他父親、她丈夫、他們的祖父,世世代代的傳承,像一家百年老字號的傳人,努力工作未必是為了營利,更多倒是誠惶誠恐,希望老字號不要在自己手裏終止。
綠妖採訪時包的計程車司機劉福正也是個農民,家裏有兩分半地,言語不多的他,卻對綠妖説出了一串童話般的句子:“做農的話,你要了解農作物,你要跟果樹對話。它會生病,會肚子餓。它會説,它吃的東西不夠啦,肚子餓啊,有蟲在咬它啊,它微量元素不夠啊。做農一定要了解你的作物有什麼問題,才有辦法種得漂亮。跟小孩子一樣,他長得健康,依靠我們給他吃的什麼。”
綠妖在臺灣採訪了很多農民社團,有的以老年人為主,有的以中年人為主,還有的是以青年人為主,讓她感動的這些社團都有著濃濃的人情味,“你置身這樣的鄉村,你不是一盤散沙中的一粒,而是黏土當中的一部分,是有粘合的。可能年輕的時候産銷班是大家相互激勵,創業的土壤,到老年了就是一種長期的陪伴,大家結伴一起出去玩。臺灣農村有很深的多方面的人性因素來黏合農人,黏合在他的土地上。我們經常説葉落歸根,如果你沒有根,你的落葉應該落在哪呢?我覺得他們是有根的。城裏很多人恨不得三十歲就退休,不想上一天班了。在鄉下你看七十歲、八十歲還在種地,你會思考人和土地的關係,這些人很興致勃勃地去種地,這是為什麼?我覺得這裡面有一種永恒的東西。還有他們稍微大一點的姓都有祠堂,祠堂傳了好多代,到現在還有人去清掃、上香,是一種很綿延、恒定的東西在支撐著人,我覺得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是一種情感,一種生長的力量。”
綠妖書中提到一位80多歲老奶奶還種地,有兩個菜園子,讓梁鴻讀後十分感慨:“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感不僅來自於掙多少錢,也存在於和自然的和諧當中。今天我們把這種幸福感給遺忘掉了,在綠妖的這本書裏,我覺得這個幸福感是閃現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它是永恒的,有永恒的味道。它跟故鄉的永恒的失落是不一樣的,是相對照的。今天我們的文學,尤其是大陸文學裏面可能缺乏這種永恒的風貌,那樣一種繁榮,植物的繁榮、繁茂,確實是缺乏的,因為我們沒有感受到,連你的村莊都沒有了,樹也被砍了,河也沒有了。”
就像拳擊,一上來就被打得頭暈眼花
綠妖並非在《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中“美化”臺灣農民,描寫“世外桃源”:“臺灣農民也並不是那麼高大上,他們的內部意識形態也是千瘡百孔的,哪怕表面很完善,但細節上肯定也有不到位的情況。”綠妖坦承,自己剛開始聽老六的臺灣朋友講述時,確實預設了寫作立場,以為臺灣政府很好,很照顧農民,結果當她採訪到社會運動家楊儒門時,這樣的觀念便遭受“重創”,綠妖説:“我問他這些年的農業政策,有哪些方面他覺得比較不錯?他説‘沒有好的’。我問歷史上有沒有什麼時候是做的比較好的?他説‘沒有好過’。我説我來採訪這個選題是因為臺灣朋友説農會很好,楊儒門怎麼看農會?他説:‘農會就是地痞流氓’,這跟我的採訪印象有很大差別,我就説我採訪時看到農會和農民的關係還挺融洽的,他聽了立刻拉下臉説:‘你是不是收農會的錢了?’我説沒有。總之跟他的聊天有很大衝擊,中途都要崩潰了,就像是打拳擊,一上來我就被對手打得頭暈眼花。”
但是這“一拳”也讓綠妖多獲得了一個視角,“我覺得我不應該站在一個大陸參觀者、觀察者的角度,我應該拋棄大陸比較的參照體系,稍微進入他們的內部。臺灣農民也有自己的掙扎,全球農業進入現代化,小農經濟的臺灣一定會有自己的掙扎和失落。楊儒門的看法是一個極端,我最開始出發的時候,聽到的可能是另外一個極端,最終在寫作時取得了一個平衡中和的立場,把原來的立場打碎掉之後,其實長出了一些新的東西。比如説很多政策其實不是生出來就是完美的,是一個博弈的結果,都是農民爭取來的。”
綠妖説自己試圖寫出動態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止的美好農村,“臺灣不是我們的對比,它有自己的痛苦困惑需要面對。”對於大陸的農民政策是否應該借鑒臺灣的做法,綠妖表示不要簡單地説臺灣農業是大陸未來的方向,“不能一群坐在空調房裏的人一拍腦袋就決定了一大片土地的未來。可能還是要遵循民間真實的狀態是怎麼樣的,但是,我們決策者應該做的是傾聽民間的生態,讓它的生態自由萌發,讓民間有更多多元化的團體,當他們為自己發聲的時候也能聽到自己的聲音,幫助他們,陪伴他們。而説到溫飽的話,大陸現在很多農民並不是溫飽問題。我看梁鴻的書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同鄉人溫飽沒有問題,收入很高,但是很焦慮,找不到身份認同,沒有歸屬感。沒有自我認同感,這是最大的問題,所以並不是吃飽了就必然會得到問題的答案了。”
在梁鴻看來,現在的大陸農民像孤島一樣被孤立起來了,沒有人聊天,沒有人説話,“中國古代就有告老還鄉,很多官員退休之後都要告老還鄉,他是很開心的,賺到了錢,榮歸故里,回去蓋很多牌樓。他為什麼可以告老還鄉?因為大家都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文化氛圍。但是現在村莊裏人都走了,沒有回去的這種通道,這是需要建設的,需要大的制度建設和自我建設相結合。”
綠妖則認為,不要以為現代文明只存在在城市之中,在鄉下仍然有機會建設屬於自己的文明:“我覺得臺灣的美濃很文明啊,當地的民宿爭奇鬥艷的。我們住的地方就種著睡蓮,環境很好,房間裏還挂著藝術品,他們這一代五六十歲的農民,都是走南闖北,出過國的,眼界很廣。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審美是不俗的,民宿非常精緻,不是説很豪華,而是説有審美在裏面,住在裏面很賞心悅目,院子很寬敞,有湖,有青山,晚上散步覺得心曠神怡,我就覺得很文明。我們會有一種思想,覺得只有城裏才有現代文明,我覺得不是的,就是看你有沒有能力建立屬於鄉村的現代文明。”
終於不再“死宅”
完成《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後,綠妖暫時不會再寫這類題材:“因為我畢竟不是研究農業的專業人士。”但是她會繼續寫非虛構作品,《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治愈了她的“死宅”毛病,“我是有那種社交障礙症的,走出家門跟陌生人打交道,對我來説是很難克服的一件事情,我是一個特別怕依賴別人,畏懼跟人交流的人,很多寫作者都是這樣,內向。為了逃避這種東西,逃開我不勝任的交流,我連職場都不混了,從職場跑回了家,一個人在家裏宅著寫了好幾年。”
接下《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走出家門時,綠妖説自己的心情是“驚恐”的,慶倖的是她去的是臺灣,臺灣農民的熱情,臺灣的“禮樂風景”讓綠妖克制住了恐懼:“非虛構寫作必須依賴別人的幫助,不可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狀態,你必須依賴別人把你帶到這個地方,給你介紹人,有時候要給你做翻譯,你要接受別人的好意。這個過程中,它教會我一個很重要的道理,我以前一直覺得我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要求我自己寫好就可以了。其實不是的,這是一種虛幻想像的狀態,其實沒有人是可以獨立存在的,我們都是依賴著別人而存在,我們相互依賴存在,我覺得寫這本書,非虛構寫作對我來説是很大的啟發。”
綠妖説從這本書開始,她可以沒有心理陰影地走出家門了:“像我這樣的人整天坐在家裏,發現你變成了自給自足的世界,但是你要寫什麼呢?你無限地挖掘人性,無限地審視自己是會出問題的,所以走出家門對我來説是很好的開始。”
本版文/本報記者 張嘉 攝影/綠妖
[責任編輯:劉暢]
相關閱讀:
- 綠妖新作《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探訪台灣農村生態2016.07.05
- 浙江慈溪市取得臺灣鰻鰍苗種培育首次成功2016.07.05
- 臺灣青年創業考察團來梅交流2016.07.04
- 海南省長劉賜貴會見臺灣農業專家孫明賢2016.07.01
- 海峽兩岸現代農業合作助推粵臺農業發展2016.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