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新奇之作《獨藥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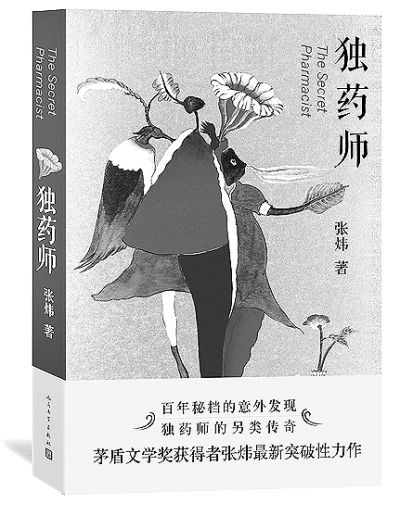
對於作家張煒來説,10卷本450萬字的大河小説《你在高原》的出版,是他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分水嶺。它耗費了作家太多的熱情和精力,似乎也耗盡了他最富情感與原動力的資源儲備。翻過這座“高原”之後,作家將會迎來怎樣的風景,當是文壇和讀者殷切期待的。此後一晃6年,這位為文壇所看重的多産作家,除了《半島哈裏哈氣》《少年與海》《尋找魚王》等寫給少年兒童的小説,新近又推出了長篇新作《獨藥師》(《人民文學》雜誌2016年5月號發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與張煒以往長篇不同的是,它除了仍然信賴和借助生命原動力之外,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豐富的知識儲備所進行的創作,是經驗之外的厚積薄發之作,因而具有特別的意義。
讀罷新書,掩卷之餘心想:這果然是資訊量極大又非常好看的一部奇書。然而,如何概括和把握這部新作呢?一部風雲激蕩的革命傳奇?一部深藏幽僻的養生秘史?還是一部纏綿悱惻的愛情悲喜劇?
作品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通過半島首富、第六代獨藥師傳人季昨非由反對革命到同情革命,再到援助革命和參與革命的漸變過程,側面記寫了清末民初膠東半島上的一段革命史,描述了辛亥革命時期歷史潮流的浩蕩大勢。同時還寫出了“五四”前夕這一劇變時期,各大宗教在中華大地上的衝突與交融。作家還以空前發達與敏銳的藝術觸覺,興味盎然地描述了半島地區具有神秘意味的養生文化,在思考革命與養生之間矛盾的同時,提出了關乎生命也關乎歷史的悖論,即人類與歷史需要怎樣的“獨藥師”的問題。僅就題材內容而言,作品也是重要的和特別的,其中的思想含量更是不可小覷。由此可見,長篇小説《獨藥師》是一部發力深遠的新奇之作,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均具有明顯而且重大的突破意義。
作品的結構是別致的。整部小説除了簡短導讀式的“楔子”,由兩個相對獨立而又相互滲透的文本組成:主體是主人公季昨非的回憶錄,包含了引人入勝的故事和豐富駁雜的心緒;其次是作為“附錄”的“管家手記”,以所謂史料記錄為主,從中可窺歷史背景的廣闊,感知革命的風雲之勢。作品中所寫的季氏家族,是中醫與養生世家,半島地區的首富。第五代獨藥師傳人季踐曾長期援助革命黨,其養子徐竟在留學東瀛之後成為革命黨的一員。季踐死後,季昨非繼承了龐大的家業,賡續著援助傳統,同時孜孜以求地探索養生奧義,並因此與季府的敵人、養生大師邱琪芝建立了恩怨莫辨的關係。對於養生與世道的關係,邱琪芝有言,“凡亂世必有長生術的長進,春秋魏晉莫不如此。我們如今又進入亂世,這樣的年頭除了養生,不值得做任何事情。只有生命危在旦夕,才更加明白生命的寶貴。”正是在與這位閱盡滄桑的百歲老人的切磋中,季昨非深刻地意識到作為第五代獨藥師的自己肩負的使命,決心將走向末路的養生術發揚光大。
然而,正因身處亂世,養生成了奢侈之事。革命黨人的突然而至和愛情的降臨,讓季昨非一再分神,竟至深陷囹圄,遭遇殺頭大禍。與中醫世家季府相對應的,是美國人在半島所建的有著“鑄了西洋圖案的生鐵大門”的麒麟醫院;在此,不僅有中西文化的碰撞,也有愛情火花的迸現。書中的女主人公陶文貝,在作品進行到近三分之一時登場了,其炫目的光彩令主人公為之傾倒膜拜。不難看出,這裡的人物與故事,在一定程度上隱喻了西方文化對東方人的征服與吸引,以及東方人對西方文化跟進式的激烈追求。作品在波瀾壯闊的背景下展開了多姿多彩的畫卷,塑造了一系列棱角分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繪了感人至深、柔腸寸斷的情愛故事。作品中,革命、養生、愛情三大元素的並置,不同角色極具個性的思考與表達,多元觀點的交鋒所形成的悖論,促進了生命哲思的昇華。究竟是“養生”的“獨藥師”還是“革命”的“獨藥師”更靠譜,或者説,哪一個“獨藥師”是真正護生的“獨藥師”,一直是書中不同角色所琢磨的。探索養生之道,對於邱琪芝和季昨非來説,固然是他們畢生的追求,然而一旦將自己置於革命的大背景之下,勢必産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邱琪芝最終在槍傷中死去,季昨非自己險些被殺,都説明瞭現實的殘酷無情。同樣,王保鶴他們提倡“不以暴力抗惡”,固然也屬於“好極了”的主張,但革命黨人認為,“除非是遇到了‘雅敵’才行!”而現實中的對手“是動輒淩遲的野獸”,如果不革命,不“在絕路中殺出一條血路”,最終只能是“拖著被淩遲後的一副骨架去乞求和平”。作品中,季昨非與哥哥徐竟之間那些激烈爭執,兄弟倆不同的人生經歷和結局,撼動人心又發人深省。
這部近30萬言的作品,有著豐富的資訊量和新穎的知識點,特別是對於方士文化和養生之道,有別開生面的記錄和描述。閱讀此書,收穫的不僅僅是好看的故事所帶來的快感,更多的應該是那些一時難以表述的哲學與文化層面的東西。對於寂寞的文壇和沉思中的作家,此書也許會帶來一些熱鬧:圍繞東西方文化的解讀,圍繞陌生化題材的認知,圍繞文化哲學與歷史哲學的質疑,以及圍繞這部書在作家創作史上的意義定位,都可能引發這樣或那樣的爭論和批評。但我願意相信,這部作品從語言到結構,從形象到思想,都抵達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它有極強的可讀性,又堅守了純文學的詩性品質,當屬作者最為強勁也最為傑出的一次文學虛構。
(張洪浩,作者單位:山東省煙臺市文聯創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