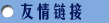第一章 恐懼的回歸
我們等他們上岸,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臉龐,他們就和平常人一樣。我們還以為他們長得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是美國人。
——柳波娃�科津岑(Liubova Kozinchenka)
紅軍第58近衛師
我想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想像俄國人,但是,當你看著他們,打量他們時,你沒法判斷你面前的人是否就是俄國人。如果你給他們穿上美國軍服,他們看上去就和美國兵一模一樣。
——艾爾�阿倫遜(Al Aronson)
美軍第69陸軍師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應該結束的方式:歡呼、握手、跳舞、喝酒,充滿了希望。時間是1945年4月25日,地點是位於易北河邊的德國東部小鎮托爾高(Torgau),事件是美蘇軍隊的首度會師,這兩支軍隊從地球的兩端進軍納粹德國,迎面相會。五天以後,希特勒在柏林的廢墟中畏罪自殺。希特勒斃命一週以後,德國人無條件地投降了。二戰中獲勝一方的大同盟領導人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溫斯頓�丘吉爾和約瑟夫�史達林,他們在戰時的兩次高峰會議——1943年11月的德黑蘭會議和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已經握過手,為一個更好的世界祝過酒。但是,如果他們的士兵沒有在戰爭前線為打敗敵人而舉行了慶祝的話,那麼他們的那些握手、祝酒的舉動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然而,為什麼在托爾高會師的士兵在迎接對方時會表現出惶惶不安,仿佛他們在期待會見外星來客?為什麼他們發現的彼此之間的相同點會顯得既令人意外,又令人心安?為什麼,即使有這種感覺,他們的上司還是決定分別舉行德國受降儀式:西線于5月7日在法國的蘭斯(Reims)舉行,東線于5月8日在柏林舉行?在德國投降的消息正式宣佈以後,為什麼蘇聯統治者要驅散莫斯科自發出現的對美國表示友好的人群?為什麼在蘇聯政府鎮壓親美人群的一週以後,美國領導人先是突然宣佈終止向蘇聯運送租借援助物資,然後又宣佈恢復提供該援助?為什麼羅斯福的重要顧問哈裏�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他曾在1941年為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而立下過汗馬功勞)要在羅斯福去世六周以後急忙趕往莫斯科,試圖挽救大同盟,不使它分裂?為什麼很多年以後,當丘吉爾在寫那個時候的回憶錄時,要將回憶錄的題目稱為《勝利和悲劇》(Triumph and Tragedy)?
對所有上述問題的回答都是一樣的:在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同盟中,其主要成員之間的關係已經破裂,它們儘管還沒有發生軍事衝突,但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方面,卻已經處於對抗狀態。不管二戰大同盟在1945年春取得了什麼樣的勝利,大同盟過去能夠成功合作完全取決於其成員國能夠超越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為了相同的目標而共同努力。悲劇在於:為了使二戰大同盟能夠成功運作,以贏得戰爭的勝利,成員國不得不暫時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追求。
一
如果1945年4月真有一個外星客來到易北河邊,那麼他,或她,或它可能真的會發現:在那裏會師的美蘇軍隊之間的相同點是那麼膚淺,他們所代表的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相同點也是那麼膚淺。美國和蘇聯都誕生於革命,兩個國家都信奉具有世界意義和目標的意識形態。他們的領導人都認為,在他們自己國家適用的一套制度,也同樣適用於世界的其他地方。作為領土廣大的陸地國家,美國和蘇聯都曾經在廣闊的邊疆中擴展;當時,從領土而言,蘇聯是世界第一大國家,美國是世界第三大國家。兩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也相同,他們都遭到突然襲擊: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四天以後,希特勒以珍珠港事件為藉口,向美國宣戰。美蘇之間的相同點僅此而已,任何外星來客都會很快發現,美蘇之間的不同點要大得多。
發生在一個世紀半以前的美國革命,代表了一種對高度集中的權威的極度不信任。美國的建國領袖們認為,只有約束權力,才能建立自由和公正。由於有一部聰明的憲法,由於他們的國家在領土上同潛在的對手隔絕,由於他們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美國人能夠建立起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強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以充分的體現。但是,美國人之所以能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因為他們嚴格地限制他們的政府管控他們日常生活的能力。不管是在政府對人們思想的灌輸方面,還是在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組織方面,還是在政府對國內政治的操作方面,美國人都大大地限制了政府的權力。儘管美國曾採用過奴隸制,曾發生過對土著美洲人的幾乎滅絕式的對待,還存在著種族、性別和社會等方面的歧視,但美國公民在1945年卻有理由聲稱:他們生活在地球上最自由的社會中。
相比之下,僅僅發生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卻信奉權力集中,並視此為打倒階級敵人,在全世界推廣無産階級革命的方法。卡爾�馬克思在1848年出版的《共産黨宣言》中指出,資本家所帶來的工業化,既擴大了工人階級的數量,也加大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使得工人階級最終要尋求自我解放。但是,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沒有耐心等待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發生,他在1917年試圖通過奪取俄羅斯並將馬克思主義強加給俄羅斯,來加快歷史發展的進程,儘管當時俄羅斯的情況並不符合馬克思的一個預言,即無産階級革命只可能發生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史達林接著通過改造俄羅斯,來使之適應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他強迫一個只有極少自由傳統的農業國家變成一個完全沒有自由的高度工業化國家。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蘇聯是地球上最專制的國家。
如果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之間有許多不同點的話,他們在1941-1945年中間打的許多仗也是不同的。美國同時和兩個敵人開戰:在太平洋和日本作戰,在歐洲和德國作戰,但是美國遭受的人員損失卻是相當小的,總共不到30萬美國人在戰爭中喪身,他們死在所有的戰區。從地理上看,美國離戰爭發生的地方距離遙遠,除了最初日本對珍珠港的襲擊以外,美國沒有受到別的什麼重大進攻。英國是美國的盟友,在戰爭中有357000人死亡。在英國的配合下,美國能夠選擇在什麼地點,在什麼時間,以何種方式,參加戰鬥,這就大大地減少了傷亡代價和降低了戰鬥的風險。但是和英國不一樣的是,美國在戰爭結束時,經濟仍然繁榮,在四年的戰爭中,美國的戰時支出使美國的國民生産總值翻了一番。如果軍事史上有所謂“好的”戰爭的話,那麼,對美國來説,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説是一個好的戰爭。
蘇聯卻沒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這樣的好處。在二戰中,它只和一個敵人作戰,但這場交鋒卻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交鋒。戰爭夷平了蘇聯的城市和鄉村,摧毀了它的工業,沒被毀滅的工業被迫遷移到烏拉爾山以東。除了投降以外,蘇聯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敵人選擇的地點和環境中作殊死抵抗。對戰爭中蘇聯軍民死傷的數字很難精確統計,但是很有可能多達2700萬的蘇聯公民是直接死於戰火的,這個數字是二戰中美國死亡人數的90倍。對蘇聯來説,取得二戰勝利的代價是無比巨大的,1945年的蘇聯是一個滿目瘡痍的國家,能生存下來就算是幸運的了。當時一個評論員説,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俄羅斯人民帶來最恐懼但又最自豪的記憶”。
儘管美國和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自的經歷和損失相差極大,但在討論戰後世界的安排時,他們卻勢均力敵。長期以來,美國外交中一直有一個不介入歐洲事務的傳統,在二戰結束時,美國也沒有決定要改變這一傳統做法。在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甚至曾向史達林保證:在二戰結束後的兩年中,美國要把所有軍隊撤回國。鋻於1930年代發生的經濟大蕭條,美國人不能確定戰時的經濟繁榮會不會在戰後持續下去。戰爭結束時,民主制度只在少數一些國家存在,但美國人不能確定,民主制度會不會向更多的國家傳播。在二戰中,沒有史達林的幫助,美國和英國就不能打敗希特勒,這一事實決定了二戰的性質,即它只是意味著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而不是意味著對專制主義或對其在未來世界中的地位的勝利。
與此同時,儘管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巨大,但它手中仍掌握著一些強有力的牌。因為它處於歐洲,它不會將軍隊從歐洲撤出。在二戰之前的年代裏,當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不能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時,蘇聯的意識形態卻在歐洲很受重視,因為在二戰中歐洲的共産黨組織領導了反對德國的抵抗運動。最後,蘇聯紅軍在打敗希特勒時所承受的巨大代價,使得蘇聯在參與籌劃戰後世界的安排時,在道義上擁有一個強有力的發言權。因此,1945年,共産主義和民主資本主義在決定未來世界走向的問題上影響力是同樣大的。
蘇聯還有一個優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所有的戰勝國中,它是唯一一個還保留著經過戰爭考驗的領導人的國家。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去世,缺乏經驗和孤陋寡聞的副總統哈裏�杜魯門入主白宮。三個月以後,丘吉爾在英國大選中遭到意外失敗,使名不見經傳的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成為首相。與英美的情況相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卻仍然大權在握,他從1929年開始就是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他改造了蘇聯,並帶領蘇聯取得二戰的勝利。他老奸巨滑,經驗豐富,外表不動聲色,內心對自己要達到的目的清清楚楚。作為克里姆林宮的獨裁者,史達林清楚地知道,在戰後他想謀求什麼,而杜魯門、艾德禮和他們領導的國家對他們在戰後想實現什麼目標卻不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