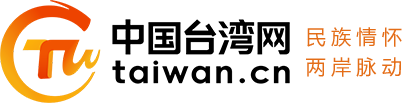當科學家遇上投資者 科技初創企業如何越過“死亡之谷”
當“看不上錢”的科學家遇上“看不上科學家”的投資者
科技初創企業如何越過“死亡之谷”?
採 寫:本報記者 崔 爽 策 劃:陳 磊
深瞳工作室出品
一身黑衣,並不引人注意。總是處在嚴肅的思考狀態。
吳樂斌突然意識到,坐到自己鄰座的是物理學家潘建偉院士。
作為時任中國科學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科控股)董事長,吳樂斌在很多會議上見過潘建偉。但個人交流還是第一次,還是在一趟從北京到合肥的飛機上。
那是2015年春天,離量子通信的大火還很遠。當時潘建偉等人聯合創辦的國盾量子剛成立五六年,幾乎是一個沒有銷售額、沒有利潤、沒有固定資産的“三無産品”。少有人相信,他們做的事可能帶來一個嶄新的通信時代。
飛機一路飛,潘建偉一路講,吳樂斌意猶未盡。
“當面講起來有邏輯、有趣味,講完都懂了,站起來轉個身就不懂了。”吳樂斌笑言量子通信高深莫測,“我説趕緊再來,咱們繼續談。”兩人很快約了第二次見面的時間,僅僅兩周後,潘建偉又來到北京。
一來一回,靴子落地,吳樂斌推動國科控股投資國盾量子。1.52億,第一筆國有資本注入量子通信。
“壓力很大。”吳樂斌坦言,把這樣一筆稱得上鉅額的天使輪投資拿出來,遭遇很大的阻力,世界上沒有先例可循,沒有人知道錢會不會打水漂,“還是國有資産”。
後來的故事廣為人知。
去年7月,國盾量子登陸科創板,上市首日漲幅超1000%,破科創板紀錄,收盤估值近300億。
近段時間,潘建偉領銜的科研團隊成功構建世界上首個天地一體化量子通信網路,標誌著我國構建出天地一體化廣域量子通信網雛形。
一邊是“臉難看、錢難拿、彎不下腰”的科學家
在吳樂斌看來,這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合作。
更多的時候,他要為科學家的“個色”捏把汗,“如果科學家不按常識做事、難以合作,就很難獲得支援。項目就會被扼殺在萌芽裏。”
“説這句話的時候,我腦海中出現了很多人。”吳樂斌笑説,板凳甘坐十年冷,科學家在長期苦心孤詣的研究歷程中,必須要對自己的研究非常篤定,否則很難堅持。但這也造就了科學家比較堅持己見的態度,以及放大成果意義的傾向。“成果本身很好,但科學家有鮮明的個性或者説很‘個色’,增加了合作的困難。”
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院士有句話流傳甚廣: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鼓勵科學家創業。在他看來,術業有專攻,鼓勵擅長科學研究的人辦公司、當總裁,是把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此話雖有爭議,但也得到很多人的共鳴。
“科研人員特別是一些年輕的科學家,做公司的短板很明顯。”一位學術成果豐碩、在晶片行業創業近10年的科學家坦陳,“我自己的短板就很明顯。比如我經常被老大數落,説我不願意拜訪客戶。可是拜訪的那個人,可能就是你的學生輩,還對你吆五喝六。他們和科研人員的氣質完全不一樣。身邊很多創業的老師説起來都頭疼這點,就是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臉面和身段。”
他話説得實在,有成果在手、有底氣創業的科研人員本來就在科研院所裏備受尊重,本身也多是國家級人才,一下到了市場上俯下身去,心理落差明顯,“一般受不了”。
在吳樂斌口中,這道坎兒更直接——“找錢”。
上個世紀80年代,有美國學者發現“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商業産品”是制約産業競爭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即科學研究與商業化産品開發之間嚴重脫節。1998年,時任美國眾議院科學委員會副委員長Ehlers將其命名為“死亡之谷”。
“越谷”不易。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開發服務中心開發服務處處長牛萍遇到過很多躊躇滿志的科學家,試水創業後回歸學界,原因不外乎——“臉難看、錢難拿”。
科研院所的院墻內外有著完全不同的氣候,科研人員往往要花很大力氣、栽很多跟頭才能適應。
一邊是追快錢,急回報,“耐不下心”的投資者
一邊是“看不上錢”的科學家,另一邊則是“看不上科學家”的投資者。
在吳樂斌看來,這種“看不上”並非看輕,更多是缺少判斷力和耐心,“科技成果的轉化,本身也是‘高科技’。”
“有一次參加成果發佈會,有人告訴我,採一滴血就能告訴我全部的身體狀況。”吳樂斌説,“我很好奇,問他一滴血看的是什麼,對方告訴我看的是血液形態、細胞形態,看顯微鏡下血液的有形物質。”
本來興趣盎然的吳樂斌開始起疑,“這不符合基本科學原理,目前沒有一個醫學原理説明細胞形態能夠囊括身體的健康資訊。”他強調,無論科研成果多麼酷炫,基本的原則是不能違背科學原理,既有創新性,又要有繼承性。
有趣的是,如果沒有把好這道科學關,故事的走向可能大相徑庭。有個現成的例子——“壞血”。
Theranos幾乎是本世紀最戲劇化的科技創業公司。2014年,年僅19歲的伊麗莎白�霍姆斯從斯坦福大學退學,創立Therano血液檢測公司,宣稱發明瞭新技術、新設備,只需刺破手指採幾滴血,就可以完成在專業醫療實驗室內進行的多達240項身體檢查。
這個革命性的驗血設備讓她“斬獲”“女版喬布斯”的大名,以及近百億美金的估值。
但伴隨著調查記者約翰�卡雷羅的不懈“扒皮”,這個創富神話被證實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局,從來沒有革命性設備,只有設備和數據的層層造假。一個持續十幾年的“壞血”騙局震動全球。
判斷成果的科學價值之外,更寶貴的是靜待種子發芽成長的耐心。
“科技投資需要長線。市場上理解和尊重科技、對成果有耐心的投資者少之又少,大部分追熱錢追快錢。”吳樂斌直言,他接觸的有些投資者明顯“把科研院所當成提款機”,“曾經有投資者簡單不過地説非常看好某項成果,要給錢,但恨不得當年就要回報,最多兩三年。”
面對早期成果,市場上投資者大多興趣不大。“科學家要和投資者走在一起,後者不能對前者太急功近利。”吳樂斌説,比如寒武紀,如今的“AI晶片第一股”開盤後市值很快突破千億元,無數人削尖腦袋想往裏擠,但在他的記憶裏,早些年幾千萬估值都鮮有人問津。
十幾年研究所副所長加十幾年投資者的經歷,吳樂斌經手的項目形形色色。曾經有科學家發現從動物器官中提取的成長因子成分,可以治愈不容易癒合的創口,主動找到他,吳樂斌跟他詳談,設計了成果如何實現轉化的路徑,結果第二天,科學家告訴他“昨天晚上,差一點就死了”。
吳樂斌嚇一跳。細問才知道,原來科學家聽完心情很激動,一晚上沒睡著,做醫生的太太直接説,“算了吧,這麼往前走我對你的健康很擔憂,會影響這條命”。
“他是很好的科學家,有很好的科學發現,他對創新非常敏銳,導致他性格中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對美好前景既欣喜又擔憂。”吳樂斌説,好的成果轉化,需要科研人員、企業經營人員、投資者三方的和諧步調,缺一不可。
怎樣才能讓人和錢走到一起
吳樂斌常被看作“離科學家最近的人”。作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轉化母基金的掌門人、中科院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他的工作就是把錢投向有轉化潛力的中國科學院成果。
在他看來,成果必須回應市場的真實需求,“起碼要有商業計劃書”。但能做到這一點的項目寥寥無幾。
商業計劃書可以回答成果轉化的基本問題——你的技術解決了什麼市場需求。
這能規避科學家的“自我欣賞”。他回憶,曾經有位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的同事,研發了一款致力於解決心臟衰竭問題的産品,“半衰期特別短,意味著針打進去還沒拔出來,半衰期就沒了。”
這不是個例。科學家“自以為是”的産品是成果轉化的常見問題。“一項成果最好做到新、精、特、廉。”吳樂斌説,“廉”是説産品比市場成品的價格至少低百分之二十。
另外,成果要有可量化的指標,結果可重復。“有位科學家發現用一個頻譜照射種子,種子發芽成長結果特別好,比如照了南瓜,南瓜就長得又快又大。我問他,能不能告訴我這個頻譜的光照射種子時,種子的濕度、光照的時長、環境的溫濕度。能不能告訴我這些指標和結果之間的線性關係,告訴我CV值(批間差)。沒有這些,成果是不可信的。”
一串問號給熱情高漲的科學家澆了冷水。吳樂斌説,從發現到發明再到樣品、到産品,過程漫長。半路“轉不動”的大有人在。
滿足了這些,成果還要遵循市場準入。藥品要有新藥證書,醫療器械也有器械證書,只有遵從行業的遊戲規則,才能進入市場。
牛萍坦言,技術越先進,和市場接受的時間差可能越大,“我們承載創新的豐厚土壤還不豐厚,技術需要主動找市場”。
從邁出成果轉化第一步起,做商業計劃書要錢,産品化要錢,這些需求沒有對應的科研經費支援,也很難得到資本支援。在這段“爹不疼娘不愛”的早期市場化階段,吳樂斌強調,正是科技資本發揮價值的時候。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表示,資本的逐利性與科研長期性存在矛盾。科技信用是一種特殊的信用,它源於人們對科學知識的信賴所産生的社會共識。基於科技信用,科技資本對科研進行投資並預期實現增值。
“科技資本要在看不到實物的時候相信他,在産品不完美甚至沒有産品的時候把錢給他。”吳樂斌説,要幫助科技初創企業走過“死亡之谷”,就要把三種人(科技人員、企業經營人員、投資者)以及四筆錢(政府科研經費、企業資本、保險、金融機構貸款)聚在一起。通過政府基金的引導作用,渡過市場“認錢不認人”的難關。
他尤其強調了科技保險的價值,“科研工作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投資本身充滿著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需要保險來對衝”。
據他介紹,科技保險覆蓋了科技創新全方位、全過程、全要素,使得科技投資不再是真正的風險投資。“今天的科技行業非常需要科技保險,目前很多科技保險並沒有真正發揮科技保險的作用。因此,科技行業亟須中國自己的真正科技保險。”吳樂斌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