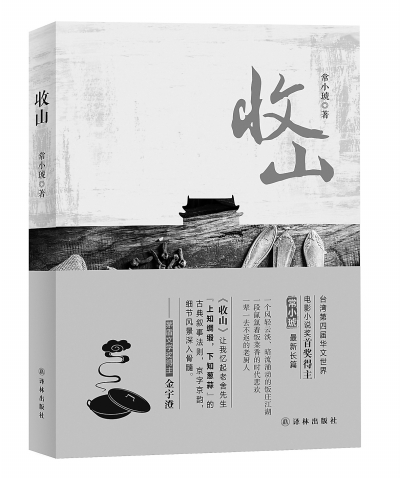
“我一直瞅你在那兒嘎嘎翻勺,跟按了電鈕似的。該翻的你翻,不該翻別瞎翻,沒用,懂嗎?”楊越鈞後面還有一些話,我聽了都下不來臺。
在楊越鈞面前,馮炳閣像一只被拴著嘴的駱駝。老人丟開他,聲嘶力竭地問大夥。“你們多的,跟著我幹過幾十年,少的也不下五六年。現在誰能告訴我,油溫最高是多少度?”
楊越鈞來回巡視,滿屋子人,沒一個答得上來。
“連油溫最高是多少都不知道,還有臉炒菜?”老人是真急了。“三兒,你給個數兒我聽聽。”他喊我三兒。
“三百。”我喊回過去。
“帶腦子的就記腦子里,沒帶的給我拿筆去。水的沸點是一百,油的燃點是三百,這是科學。油熱了,表面先開始冒煙,浮頭上呼呼一層火,這要是超過三百,等著消防隊逮你吧。”
老人隨便站到一個灶上,瞄了眼單子,馮炳閣看懂意思,立即遞來半斤瀝幹水的夾心肉,又打了三個雞蛋,拌進幹淀粉攪成糊。
肉是真好。精挑細揀的五花三層,瘦肉肥膘互夾,薄皮易爛,被提前用肉刀拍松,切成略厚的小核桃片,蘸進一碟古銅色的調料中腌漬。老人很快和進蛋糊里,柔中帶勁地反復抓捏。由指尖到掌根,肉片像一枚枚輕解羅裳的懶婦,順從地臥在他手心,軟媚牽纏。
“別光看我,瞧鍋里。”老人提醒我們。他專用的灰口大鍋,紅搪瓷底,一體澆鑄,不打鉚釘,黑沉沉架在火上。這時鍋底的花生油,從里朝外略微泛起粒狀的小鼓泡。
幾絲青煙,飄旋升起時,安緩的鍋面已能辨出螺紋。
肉片被他輕描淡寫地劃進鍋里,轉眼間,桂花開,像是揮抖水袖的奇女子,戲出白色綢絹。水袖變成鵝黃的照晚殘雲時,老人眼到手到,即刻撈出,讓油走幹。
一陣窸窸窣窣的脆響,油面的鼓泡越發壯大、躁動。肉再入鍋,要真見到桂花黃後才算數。這種肉片,分量足,質地細嫩,走油時必用武火。手潮的,極易過火脫漿,所以很多人和馮炳閣一樣,寧肯不到家,也不硬來。
“你們是想讓道林看笑話對不對,我再講一遍,滑炒菜是三到四成熱,你做滑熘里脊、滑熘雞片,有個90到120度就行。炸制菜,五到六成熱,往上推,就要150到180度。這道桂花肉,現在的油溫正合適。到了爆炸菜,比如香酥雞、樟茶鴨子,都是八到九成熱,不是炸所有東西都是一個油溫。”馮炳閣迅速再將肉入凈鍋,撒蔥花,淋麻油,松松脆地端出來,滿盤酥香,趁師父沒想起他,這位腳下抹油,趕緊溜了。 (完)
[責任編輯:楊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