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百年孤獨》是為中國人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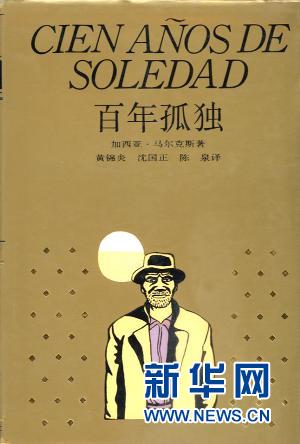
按:據説,馬爾克斯已經點頭了,允許《百年獨孤》出中文版,原來之前我們看的都是盜版,我們等得太久了。每一位中國作家心中,都有一個寫一部《百年孤獨》的夢想,李洱也有。
1985年的暑假,我帶著一本《百年孤獨》從上海返回中原老家。它奇異的敘述方式一方面引起我強烈的興趣,另一方面又使我昏昏欲睡。在返鄉的硬座車廂裏,我再一次將它打開,再一次從開頭讀起。馬孔多村邊的那條清澈的河流,河心的那些有如史前動物留下的巨蛋似的卵石,給人一種天地初開的清新之感。用埃利蒂斯的話來説,仿佛有一隻鳥,站在時間的零點,用它的紅喙散發著它的香甜。
但馬爾克斯敘述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有如颶風將塵土吹成天上的雲團:他很快就把吉卜賽人帶進了村子,各種現代化設施迅疾佈滿了大街小巷,民族國家的神話與後殖民理論轉眼間就展開了一場拉鋸戰。《裸者與死者》的作者梅勒曾經感嘆,他費了幾十頁的筆墨才讓尼羅河拐了一個彎,而馬爾克斯只用一段文字就可以寫出一個家族的興衰,並且讓它的子嗣長上了尾巴。這樣一種寫法,與《金瓶梅》、《紅樓夢》所構築的中國式的家族小説顯然迥然不同。在中國小説中,我們要經過多少回廊才能抵達潘金蓮的臥室,要有多少兒女情長的鋪墊才能看見林黛玉葬花的一幕。當時我並不知道,一場文學上的“尋根革命”因為這本書的啟發正在醞釀,並在當年稍晚一些時候蔚成大觀。
事實上,在漫長的假期裏,我真的雄心勃勃地以《百年孤獨》為摹本,寫下了幾萬字的小説。我虛構了一支船隊順河漂流,它穿越時空,從宋朝一直來到20世紀八十年代,有如我後來在卡爾維諾的一篇小説《恐龍》看到的,一隻恐龍穿越時空,穿越那麼多的平原和山谷,徑直來到二十世紀的一個小火車站。但這樣一篇小説,卻因為我祖父的話而有始無終了。
假期的一個午後,我的祖父來找我談心,他手中拿著一本書。他把那本書輕輕地放到床頭,然後問我這本書是從哪搞到的。就是那本《百年孤獨》。我説是從圖書館借來的。我還告訴他,我正要模倣它寫一部小説。我的祖父立即大驚失色。這位延安時期的馬列學員,到了老年仍然記得很多英文和俄文單詞的老人,此刻臉漲得通紅,在房間裏不停地踱著步子。他告訴我,他已經看完了這本書,而且看了兩遍。我問他寫得好不好,他説,寫得太好了,這個人好像來過中國,這本書簡直就是為中國人寫的。但是隨後他又告訴我,這個作家幸好是個外國人,他若是生為中國人,肯定是個大右派,因為他天生長有反骨,站在組織的對立面;如果他生活在延安,他就要比托派還要托派。“延安”、“托派”、“馬爾克斯”、“諾貝爾文學獎”、“反骨”、“組織”,當你把這些詞串到一起的時候,一種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就像芥末一樣直嗆鼻子了。祖父幾乎吼了起來,他對我父親説:“他竟然還要摹倣人家寫小説,太嚇人了。他要敢寫這樣一部小説,咱們全家都不得安寧,都要跟著他倒大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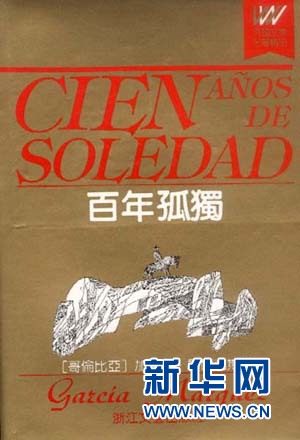
祖父將那本書沒收了,並順手帶走了我剛寫下的幾頁小説。第二天,祖父對我説:“你寫的小説我看了,跟人家沒法比。不過,這也好,它不會惹是生非。”祖父又説:“儘管這樣,你還是換個東西寫吧。比如,你可以寫寫發大水的時候,人們是怎樣頂著太陽維修河堤的。”我當然不可能寫那樣的小説,因為就我所知,在洪水漫過堤壩的那一刻,人們紛紛抱頭鼠竄。
兩年以後,我的祖父去世了。我記得合上棺蓋之前,我父親把一個黃河牌收音機放在了祖父的耳邊。從家裏到山間墓地,收音機裏一直在播放黨的十三大即將召開的消息,農民們揮汗如雨要用秋天的果實向十三大獻禮,工人們夜以繼日戰鬥在井架旁邊為祖國建設提供新鮮血液。廣播員激昂的聲音伴隨著樂曲穿過棺材在崎嶇的山路上播散,與林中烏鴉呱呱亂叫的聲音相起伏——這一切,多麼像是小説裏的情景,它甚至使我可恥地忘記了哭泣。但是二十年過去了,關於這些場景,我至今沒寫過一個字。當各種真實的變革在謊言的掩飾下悄悄進行的時候,我的注意力慢慢集中到另外的方面。但我想,或許有那麼一天,我會寫下這一切,將它獻給沉睡中的祖父。而墓穴中的祖父,會像馬爾克斯曾經描述過的那樣,頭髮和指甲還在生長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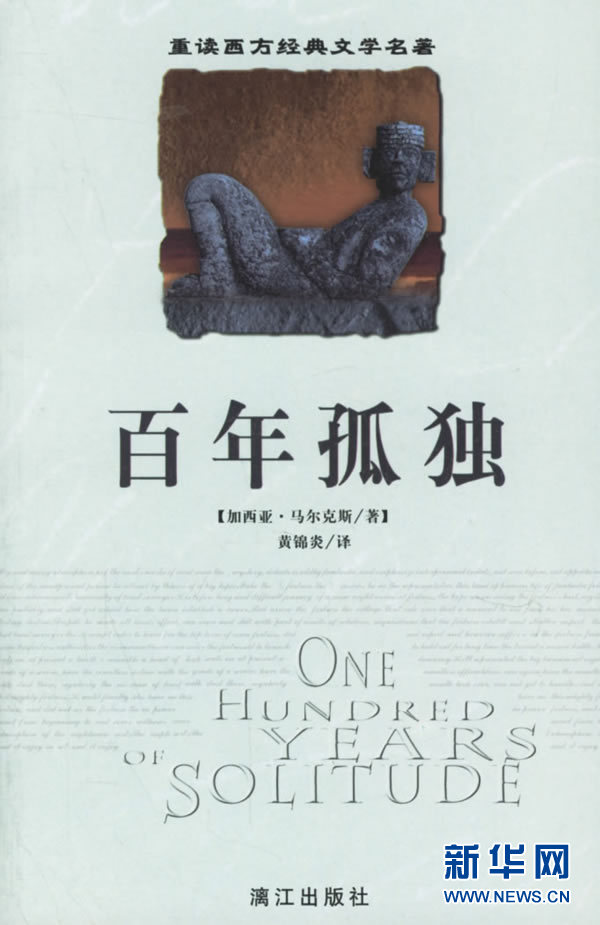
毫無疑問,《百年孤獨》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説,是小説中的皇冠。它雖然寫的是拉美,但每個中國人似乎都能從中看到自己的生活。雖然我後來的寫作與《百年孤獨》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我仍然要對它表示敬意。它最初帶給我的閱讀體驗,至今也仍然清晰如昨,比如現在,我就再一次想起了從祖父的棺材裏傳出來的聲音,聽到了山林中的鳥叫。我仿佛也再次站到了一條河流的源頭,那河流行將消失,但它的波濤卻已在另外的山谷迴響。它是一種講述,也是一種探究;是在時間的縫隙中回憶,也是在空間的一隅流連。
□李洱(北京 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