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估計需要多長時間?”
2011年夏天,上海徐虹中路20號,路金波先生問我,當時在座的還有他的同事瞿洪斌先生。
這是我和他們第二次見面。我們第一次見面達成了三點共識:首先,市面上流行的外國名著譯本絕大多數錯漏百齣,是不合格的劣質産品;其次,這些劣質産品不利於青少年養成閱讀習慣,進而妨礙了整個社會的進步;最後,我們有責任、有信心、有能力為讀者提供一套跟得上時代、對得起原著的經典譯本。第二次見面,我們商談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翻譯出版項目:我負責選定和翻譯二十種歐美文學名著,金波和瞿老師負責這套“李繼宏世界名著新譯”的出版和發行。
此前我已經在大陸和臺灣出版了十六種涵蓋文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哲學等領域的譯著,除了艱澀的《公共人的衰落》,其他作品——包括多達40萬字的《窮查理寶典》——都是在兩個月以內完稿的。
根據我當時的經驗,文學作品的翻譯難度不高,我曾經用十天假期譯完《追風箏的人》,至於《維納斯的誕生》、《倒轉地極》和《燦爛千陽》等,則是利用下班的時間和週末抽空做的,各自花了一個月左右。因此當金波問這個項目需要耗費多久時,我不假思索地説:“三年。”
起初十分順利,到2012年4月,《了不起的蓋茨比》、《老人與海》、《小王子》、《動物農場》以及《月亮和六便士》已經先後完稿。前面四種在2013年1月作為“李繼宏世界名著新譯”第一批産品上市,《月亮和六便士》由於版權原因,直到今年才和讀者見面。反正當我在2012年4月開始翻譯《瓦爾登湖》的時候,仍然很有信心用三年完成這個項目。
可是《瓦爾登湖》卻做了差不多一年,而且這一年,比大多數人的一年要長得多。我沒有社交活動,除了偶爾出去旅遊,每天有十幾個小時在工作。我自己粗略估算過,《瓦爾登湖》雖然用了340天,但花在查閱、翻譯和註釋上足足有4000個小時。但這主要是因為梭羅這部名作特別晦澀,他引用了大量東西方的經典,描繪了數百種新英格蘭地區特有的動植物,在我選定的二十種名著中,它的閱讀難度系數是最高的。因此我在2013年3月28日寫完《瓦爾登湖》導讀以後,感到無比輕鬆,滿心以為再過兩年就能把剩下的書做完。
休息幾天之後,2013年4月,我著手準備翻譯《傲慢與偏見》。簡 奧斯汀這部小説我以前看過幾遍,當時感覺它的情節簡單,文字淺顯,篇幅也不長,應該很快可以完成。但等到真正動筆的時候,我才發現《傲慢與偏見》其實比《瓦爾登湖》難理解得多。這主要是因為,以普通讀者的身份看書,和以譯者的身份譯書,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普通讀者看書往往不求甚解,只要了解故事梗概和大致寓意就可以了;但作為譯者,卻必須全面徹底地揣摩作者的寫作意圖和原文的準確含義,而這裡面的難易,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品的時代背景。
在《瓦爾登湖》之前,我譯過二十幾種書,但都是20世紀以後的作品,它們使用的語言和我們現在相差不是太遠。《瓦爾登湖》是19世紀中期的,所以耗費了更多時間。至於《傲慢與偏見》,是簡 奧斯汀在18世紀末創作的,那時候的衣食住行、道德觀念、法律制度、社會風氣等等和現在的英國大不相同,和現在的中國就更不用説了。如果對那段時期的英國歷史缺乏足夠的了解,在理解原文上會遇到極大的障礙,根本談不上準確翻譯。下面我會從衣食住行四個方面舉一些例子來説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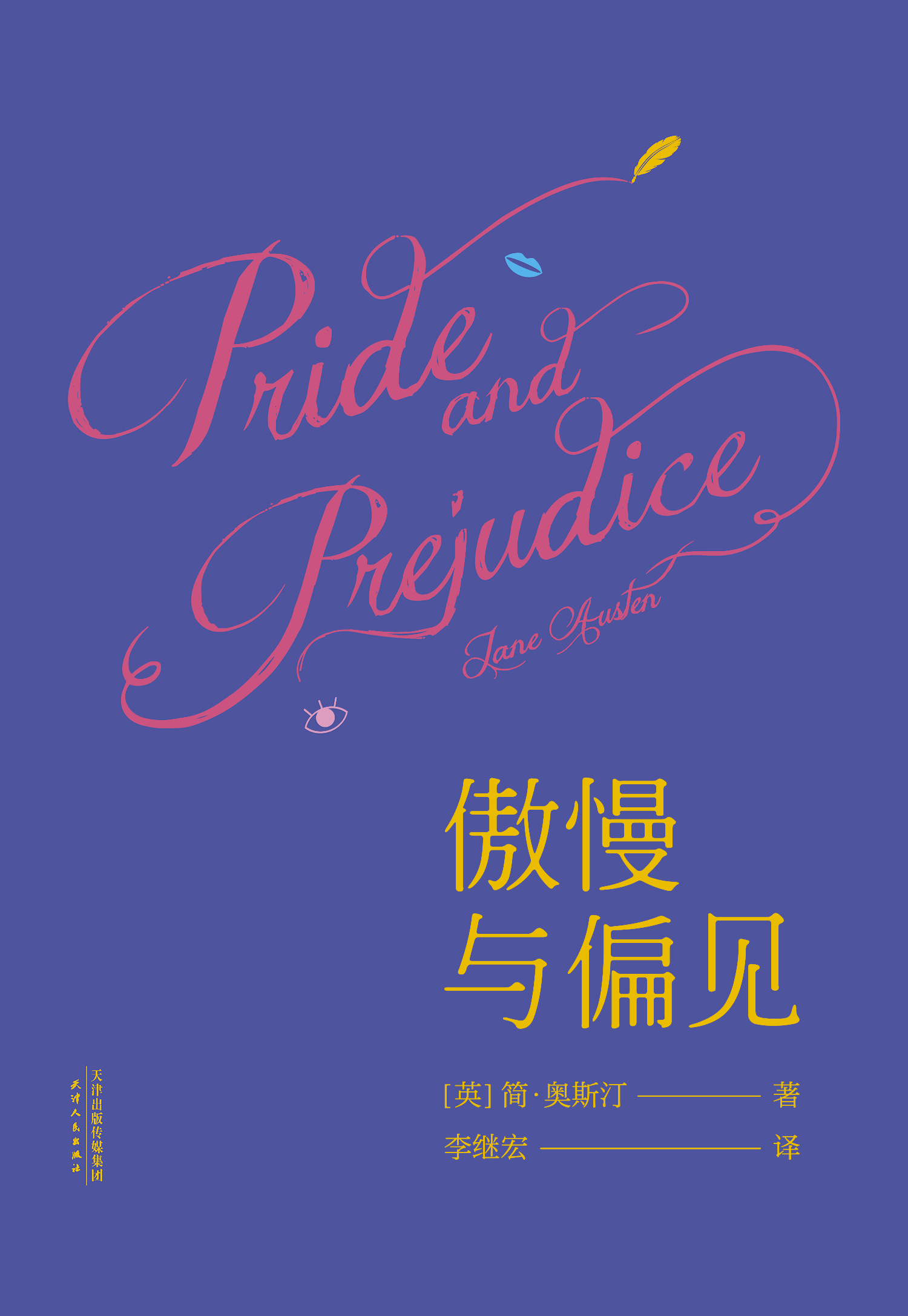
《傲慢與偏見》作者 (英) 簡�奧斯汀 譯者 李繼宏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6-6-1
當時我信心滿滿、幹勁十足開始翻譯《傲慢與偏見》,沒想到第一頁半個句子就把我難住了。這半個句子是這樣的:
he came down on Monday in a chaise and four to see the place.
這句話好像很簡單對不對?本來我們可以請到場的朋友試著翻譯一下這句話,再來分析難點在哪;但為了節省時間,我特意專門找了市面上三個比較流行的《傲慢與偏見》譯本,大家來看看它們分別是怎麼處理的。
1、他星期一那天,乘著一輛駟馬大轎車來看房子。
2、他星期一那天乘坐一輛駟馬馬車來看房子。
3、他星期一坐了一輛駟馬轎車來看了房子。
三個版本文字略有不同,但意思一樣的。請仔細再看原文,你們的理解是不是和它們差不多?如果是,那就有問題了。問題出在哪呢?出在兩個地方。
首先是came down。這個片語有點奇怪,對不對?因為如果簡 奧斯汀想表達的是“他”來看房子,那麼依照英語的語法,這裡用came就可以了,也只能用came。她為什麼要用came down呢?其實在簡 奧斯汀時代,英格蘭只有倫敦一個城市,其他都是鄉村地區,所以説去倫敦,一般説go to town,也就是“進城”。《傲慢與偏見》裏面出現了66次town,毫無例外都是指出現55次的London。至於從倫敦到其他地方,則用come down來表示,也就是“下鄉”。簡 奧斯汀在這句話裏面,明確地指出了“他”是從倫敦來的,但我們可以看到,上面三個版本都沒有再現這層意思。
第二個問題出在chaise and four的翻譯上。這個片語無論是美國的《韋氏英語詞典》還是英國的《牛津英語詞典》都沒有收錄,它們只收錄了chaise和其他幾個片語。那麼chaise是什麼呢?《牛津英語詞典》是這樣解釋的:
A light open carriage for one or two persons, often having a top or calash; those with four wheels resembling the phaeton, those with two the curricle; also loosely used for pleasure carts and light carriages generally.
所以我們知道chaise是一種馬車,至於chaise and four,國外有幾種Pride and Prejudice註釋版,它們都給出了定義。其中比較準確的是哈佛大學Belknap出版社的版本,它是這樣解釋的:
A carriage seating four people, drawn by four horses.
也就是説,chaise and four是一種使用四匹馬的四輪車。這樣看來,前面三個版本譯成“駟馬大轎車”、“駟馬馬車”和“駟馬轎車”好像是可以的。但為了弄清楚這個片語到底應該怎麼譯,我們需要先熟悉簡 奧斯汀時代的馬車製造業和《傲慢與偏見》中提及的各種馬車。
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馬車製造業和現在汽車製造業一樣特別繁榮,除了chaise and four之外,常見的還有gig、landeau、phaeton、whisky、curricle、wheelbarrow、barouche、chariot、hackney等上百種,在《傲慢與偏見》中出現的有chaise and four、chaise、phaeton、gig、barouche、curricle和hackney等七種。這些馬車和現在的轎車一樣,大小价錢各不相同,象徵著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簡 奧斯汀利用它們來展示小説角色的財富和階層。比如這部小説中只有兩個人擁有chaise and four,一個是賓格利,就是前面引文中的“他”,一個是達希的姨媽凱瑟琳夫人;curricle也只出現兩次,擁有者分別是達希和顧爾丁。凱瑟琳夫人家裏至少還有phaeton和barouche;女主角伊麗莎白的舅舅加德納先生和鄰居威廉爵士都有一輛chaise,她表哥科林斯先生開的是gig,至於hackney,則是倫敦的計程車,維克哈姆先生曾經租用過。
我們先來看看這些車的樣子。這是chaise and four,這是phaeton,這是barouche,這是gig。根據這些圖片,我們可以很直觀地發現它們明顯是分檔次的。但到底是不是這樣呢?這種直觀的印像是否反應在它們的售價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查了很多資料,後來終於在一本1795年出版的圖書裏找到了想要的答案。這本書叫做A Treatise on Carriages,很詳細地講解了當時各種馬車的價格,基本款多少錢,豪華款多少錢。比如説chaise and four和barouche的豪華版是200多英鎊,凱瑟琳夫人的女兒用的phaeton要賣100英鎊,至於gig,則不到32英鎊。用現在的轎車來打比方的話,chaise and four大概相當於賓士S600,phaeton相當於奧迪TT,chaise相當於雅閣、帕薩特或者凱美瑞,gig則相當於飛度、卡羅拉之類的。我最終採取的策略是,這些馬車的名字統統音譯,並加註釋詳細説明它們的售價是多少英鎊,大概相當於現在什麼車。所以上面那半句話我的翻譯是:
他禮拜一坐著一輛四驅翠軾從倫敦來看房子。
然後我給四驅翠軾添加了詳細的註釋,讀者看到我的譯文和註釋以後,就會明白賓格利乘坐四驅翠軾去伊麗莎白家鄉租房子,大概相當於現在某個富豪從上海開著賓士S600到江蘇太倉定居,當地居民十分轟動自然可以理解。為了翻譯這半句話,我用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去研究當時英國的馬車製造業和道路交通狀況。或許有讀者會覺得這是小題大做,因為《傲慢與偏見》有其他文字描寫了賓格利、達希、凱瑟琳夫人、科林斯先生等人的身份地位,所以沒有準確地把這些馬車解釋清楚也不影響理解。但實際上,簡 奧斯汀還巧妙地用這些馬車來體現小説中各個角色的性格,下面我來舉兩個例子。
在小説的第二卷第十四章,女主角伊麗莎白到朋友夏洛特家做客,準備要走了,達希的姨媽凱瑟琳夫人擅作主張請她留下,凱瑟琳夫人是這麼説的:
如果你留下來,再住一個月,我可以送你們一個人到倫敦,因為六月初我要去那裏住一個禮拜,道森不會反對坐巴羅赫的箱子,車裏再容納一個人綽綽有餘。
道森是凱瑟琳夫人家的跑腿,巴羅赫是一種豪華敞篷四輪馬車,後軸上有兩個座位,前軸上是一個收納行李的木箱,可以容納車夫和跑腿兩個人。巴羅赫車身高,又是敞篷的,所以當年的貴族喜歡在氣候宜人的時候乘坐它外出遊玩,既可以炫耀自己華麗的服飾,也可以享受旁觀者崇拜的眼神。這裡有一張巴羅赫的照片,大家可以來看看這種豪華馬車長什麼樣。
但巴羅赫本質上是一種適合在城區使用的馬車,並不適合長途旅行。我們知道凱瑟琳夫人家在肯特郡韋斯特勒姆附近,離倫敦大約25英里。這段距離現在看很短,開車不用半個小時能到,但在簡 奧斯汀時代,馬車的平均時速只有五英里,也就是説,從凱瑟琳夫人家到倫敦需要五個小時。並且當年的馬路可不是水泥路面或者柏油路面,而是非鋪裝路面,晴天塵土飛揚,坐在敞篷車上是很難受的。因此當時公共交通工具郵政馬車的座位是分車廂內車廂外兩種票價,比如説從倫敦去約克,坐在車廂裏面需要3英鎊3先令,坐在車廂外面需要1英鎊11先令6便士。凱瑟琳夫人家裏有許多馬車,我們知道她至少還有一輛適合長途旅行的四驅翠軾,但去倫敦偏偏要坐巴羅赫;這大概相當於現在有個富婆,家在南京,車庫裏明明有賓士S600,甚至很可能有勞斯萊斯幻影,但她寧可在滬寧高速上吸幾個小時的霧霾和汽車尾氣,也非要開敞篷版賓利歐陸GT去上海,可見其為人是多麼的淺薄和虛榮。
另外一個例子比較複雜,但它反映了簡 奧斯汀極為高明的寫作技巧,我想詳細和大家説説。在《傲慢與偏見》第三卷第九章,伊麗莎白的妹妹麗迪雅結婚回家,説起路上的情況:
喔唷!媽媽,周邊的鄰居知道我今天結婚嗎?我怕他們還不知道呢;剛才我們坐車趕上威廉 顧爾丁的卡裏克爾,我覺得他應該知道這件大喜事,所以把靠近他那邊的玻璃窗搖下來,脫掉手套,把手放在窗框上,讓他見識一下我的戒指,然後我朝他點了點頭,笑得特別開心。
表面上看,這段文字主要展現了麗迪雅的輕佻,但實際上也側面描繪了她母親本尼特太太的好高騖遠。威廉 顧爾丁是她們的鄰居,此前只在小説中出現過一次,就是在第三卷第八章,當時傳來麗迪雅即將成婚的喜訊,本尼特太太忙著給她的女兒女婿找一個住所,書上是這樣寫的:
“哈耶花園還可以,”她説,“可惜顧爾丁一家不肯搬走;斯托克府也不錯,就是休息室比較小;但阿什沃斯離得太遠啦!我不會讓她離我超過十英里的。至於珀維斯別墅,那裏幾個閣樓太糟糕了。”
如果不是特別細心,如果不是對當年的馬車有全面的了解,我們根本無法領略簡 奧斯汀巧妙安排的前後呼應之處。
卡裏克爾是一種高級兩輪馬車,用一匹馬或者兩匹馬拉均可,適合車主自己駕駛,車廂只有一個座位,我前面提到那本關於馬車的專著A Treatise on Carriages指出卡裏克爾的“使用者通常是傑出人士”,豪華版售價高達103英鎊5先令,大概相當於我們現在的保時捷911跑車。在整部小説裏面,除了達希先生,便只有顧爾丁駕駛卡裏克爾,可見顧爾丁也是超級大富豪。本尼特先生的家境很不錯,然而算不上特別富裕。小説沒有指明本尼特先生家的馬車是哪一種型號,但是根據相關描寫,我們可以推斷出大概也是翠軾。另外我們知道,本尼特先生的馬不是專門用來拉車的,有時候需要幹農活。結合這些背景,我們可以得出一道等式:本尼特太太想租顧爾丁先生的房子,相當於現在一個家裏只有一輛雅閣、有時候連油都加不起的中産人士,試圖叫一個開保時捷911的大富豪搬家把房子租給她。和簡 奧斯汀同時代的讀者,只要看到這裡就會發現本尼特太太實在是——呃,用上海話來説——實在是太過十三點。但現在你就算請英美名牌大學英文係的教授來看,也未必能看出來這些奧妙之處,反正我看過六個《傲慢與偏見》的英文註釋版,沒有一個指出這一點。
其實我在翻譯的時候,不怕像chaise and four這種雖然費解但比較罕見的表達,因為如今資訊發達,任何問題都有答案。我最怕的是一些常見的單詞,因為最常見的反而最容易犯錯。比如説第一卷第二章最後半句話是這樣寫的:
and determining when they should ask him to dinner.
好像很簡單,對不對?這時候本尼特先生已經去賓格利家做過客,本尼特太太母女幾人正在討論什麼時候請賓格利來家裏吃飯。問題出在dinner上面。這個單詞就連小學生也認識,就是宴席、晚餐的意思,現在一般是指晚餐。所以我開始把這半句話譯為“請他來吃晚餐的日子又應該選在哪天”。
這麼譯似乎沒有問題,讀起來很順,甚至到了第一卷第八章開頭,伊麗莎白到賓格利家探望生病的姐姐,留在那裏過夜,簡 奧斯汀提到傍晚六點半有人叫伊麗莎白去吃dinner。看來dinner確實是晚餐。然而,到了第二卷第十六章和第三卷第五章,作者又明確指出伊麗莎白家吃過dinner之後是下午。這到底怎麼回事呢?是不是作者弄錯了?換一個譯者,也許會把後面這兩處dinner翻譯成“午餐”,那麼就能自圓其説了。但我知道《傲慢與偏見》的初稿在1797年就完成了,直到1813年才出版,中間十幾年經歷過千錘百煉,這裡簡 奧斯汀弄錯的可能性很小。於是我只好去查資料,沒想到一查又是兩個月過去了。
原來在簡 奧斯汀時代,由於生活節奏遲緩,物質匱乏,英國人每天只吃兩頓飯,就是breakfast和dinner,午餐(lunch)極其罕見,夜宵(supper)相對較為頻繁,尤其是在上層階級家庭,但也只在夜間有親友聚會時才提供。因此dinner只能譯為“正餐”。像本尼特先生這種鄉紳家庭,早餐通常9點吃,正餐在下午3點——這主要是為了節省柴火,因為英國地處高緯度,冬天太陽很早下山,如果太晚吃飯,那麼準備飯菜時廚房需要點燈,這意味著額外的開支。至於更為有錢的貴族和商人,比如達希和賓格利,他們不在乎這些錢,日常活動也較為豐富,吃正餐的時間比本尼特家要晚三四個小時,而吃早餐的時間通常是11點。這也解釋了《傲慢與偏見》中另外兩個貌似矛盾的地方。
第一個是在第一卷第七章,伊麗莎白的姐姐簡去了賓格利家做客,因為淋雨生病了,寫信回家告訴伊麗莎白。收到信時,本尼特先生一家已經吃過早餐,伊麗莎白姐妹情深,所以迫不及待地去探望簡。她在雨後的泥濘中跋涉三英里,到內德菲爾莊園以後,發現賓格利家還沒有開始吃早餐。這個細節貌似矛盾,其實簡 奧斯汀的目的是用它來展現兩個家庭的社會地位高低有別。
第二個出現在第一卷第九章,伊麗莎白髮現姐姐病情惡化,一大早請賓格利派人給家裏送信,等她母親帶著兩個妹妹坐馬車過來的時候,賓格利家已經吃過早餐了。好像很奇怪,對不對?伊麗莎白走路過來,抵達時他們還沒吃早餐,她母親和妹妹坐車,怎麼來的時候他們反而吃完早餐了?實際上,簡 奧斯汀這麼寫,是為了展現本尼特太太對大女兒不是很關心,在家拖拖拉拉很久才出發。
和上面提到的馬車一樣,簡 奧斯汀也用飲食來刻畫人物形象。在《傲慢與偏見》第一卷第八章,伊麗莎白和賓格利家的人一起吃飯,有一句話是這樣寫的:
as for Mr. Hurst, by whom Elizabeth sat, he was an indolent man, who lived only to eat, drink, and play at cards; who, when he found her to prefer a plain dish to a ragout, had nothing to say to her.
這句話表面上也是不難理解,我是這樣譯的:
至於赫斯特先生,他就坐在伊麗莎白旁邊,這人好吃懶做,生來就是為了吃飯喝酒打牌,看到伊麗莎白專門挑口味清淡的菜肴吃、對拉古敬而遠之以後,更沒有話跟她説了。
現在的普通讀者看到這句話,恐怕是摸不著頭腦的。伊麗莎白專挑口味清淡的菜肴吃有什麼寓意嗎?赫斯特先生發現她不吃“拉古”,為什麼就“更沒有話跟她説了”?我查閱了一些相關的論文和專著,終於找到了答案。
拉古是重口味法國菜,具體做法是把胡蘿蔔之類的根菜和肉一起下鍋,倒入清水,添加佐料,再用小火慢燉。這道菜用料多、耗時久,被視為高檔菜,在當時英國貴族階層中特別流行,但普通人認為其掩蓋了食材自身味道,是一種虛假的菜肴,更為偏好本國清淡簡單的烹飪方式。伊麗莎白故意不吃拉古,就是表明瞭這種鄙夷的態度,所以赫斯特先生“沒有話跟她説”,下文賓格利姐妹將會指責她“舉止非常糟糕,既傲慢又無禮”。用現在的情況來打比方,相當於伊麗莎白到富豪朋友家吃飯,飯桌上有燕窩魚翅佛跳墻,但她偏偏只吃白灼芥藍和清炒空心菜。因此這個句子既説明伊麗莎白的清高,也説明赫斯特先生的庸俗。
在這部小説的第二卷第十六章,伊麗莎白和簡出遠門回家,兩個妹妹小琳和麗迪雅乘坐家裏的馬車去半路接她們。簡 奧斯汀是這麼寫的:
兩位姑娘已經在鎮上快活了個把鐘頭,她們光顧過街道對面的米蘭鋪,欣賞了站崗的哨兵,還享用了一份黃瓜色拉。
接上兩位姐姐以後,她們指著一桌子客棧常見的冷菜,自鳴得意地説:“不錯吧?有沒有很驚喜?”
米蘭鋪是一種特殊的商店,我們先不去管它。如果沒有註釋,現在的讀者看到這裡也許不會多想。但是在古代中國,黃瓜,尤其是反季的黃瓜,是一種特別貴重的蔬菜。下面是我找到的幾個文獻證據:
元旦進椿芽、黃瓜,所費一花幾半萬錢,一芽一瓜,幾半千錢。——《帝京景物略》,卷三
京師極重非時之物,如嚴冬之白扁豆、生黃瓜,一蒂至數镮,皆戚裏及中貴為之,倣禁中法膳用者。——《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
黃瓜初見比人參,小小如簪值數金。微物不能增壽命,萬錢一食亦何心。——得碩亭《草珠一串 飲食》,載《清代北京竹枝詞》
古代英國是不是也這樣呢?帶著這個疑問,我又搜尋了許多史料,最後在1794年出版的A Treatise on the Culture of the Cucumber和1809年出版的The Agricultural Magazine, Vol.III, from January to June中找到了答案。
根據這兩份文獻,黃瓜在英國正常的上市季節是每年7、8、9月,伊麗莎白和簡回家的時間是5月中旬,所以小琳和麗迪雅能吃到的只能是春茬黃瓜,這屬於反季蔬菜,在當時價格特別離譜,最高達到每根10先令6便士,而普通家庭老師的年薪只有25英鎊,也就是説,一個家庭老師要花七天的薪水才能夠買一根黃瓜,所以許多家庭每次只舍得吃半根,雜誌上甚至有文章專門教人怎樣把一根黃瓜分兩次吃,而第二天還能保持新鮮。另外正如前面説過的,當時英國人很少吃午餐,小琳和麗迪雅接上伊麗莎白和簡正好是中午,所以她們“指著一桌子客棧常見的冷菜”問兩個姐姐“有沒有很驚喜”。在這裡,簡 奧斯汀希望讀者留意的是,她們自己剛剛吃過昂貴的黃瓜色拉,卻用“客棧常見的冷菜”來招待遠道而來的兩位姐姐。如果我們把時代背景改到現在的中國,那就是小琳和麗迪雅自己先吃了燕窩魚翅,然後點了涼拌木耳、皮蛋豆腐來招待兩位姐姐。這樣一打比方,我們就能明白她們是多麼奢靡浪費和自私自利。
説完行和食,時間好像已經差不多了,下面我再簡單説説住和衣。簡 奧斯汀時代的居住條件和現在英國有挺大的差別,很多地方也是需要專門研究才能弄清楚。比如説小説裏出現了drawing-room、sitting-room和saloon,你要是去查英漢詞典呢,會發現它們的釋義都是“客廳”。但這當然是不對的。簡 奧斯汀去世以後第一家出版社John Murray曾在1865年出過一本建築專著,叫做The Gentleman’s House:How to Plan English Residences, From the Parsonage to the Palace,按照這本書的定義,drawing-room:
“本質上是女主人的房間……是女眷在白天接待客人的地方,正餐開始之前,賓主先在這裡集合。正餐結束以後,女士們先回到這裡,男士們隨後也來,一起度過黃昏的時段。它也是夜間舞會的接待處。”
至於sitting-room,則是家庭成員平時相聚聊天的地方;用古代中國建築來類比,通常設在一樓的drawing-room相當於外廳,一般設在二樓的sitting-room相當於內堂,我分別譯為休息室和起居室。當時英國普通人家不單獨設起居室,其功能通常由正餐廳或者休息室承擔。Saloon是17、18世紀英國大宅必備的標準房間,位於花園前側正中,兩邊是書房和會客室,是大富大貴之家才有的,這個我依照慣例音譯為沙龍。當然這些都加了註釋,以便讀者明白內中的區別。
在第二卷第六章,伊麗莎白在其表兄科林斯先生的帶領下,第一次到凱瑟琳夫人家——也就是洛辛斯莊園——做客,有一個句子是這樣的:
縱使他指出那座華廈正面有多少個窗戶,當初光是裝玻璃就耗費了劉易斯 德 伯爾爵士多少鉅資,伊麗莎白聽了也是無動於衷。
如果不加以解釋,現在的普通讀者是很難理解這句話的用意的。其實從1696年到1851年,英國政府向境內所有房屋的住戶徵收窗戶稅,免征額為9個,超出越多稅率越高,甚至連地窖的出入口也計為窗戶,所以在這段時期內,人們造房子時總是儘量少開幾個窗戶,哪怕室內通風不良造成了痢疾、壞疽和斑疹傷寒等傳染病的橫行。另外從17世紀末開始,英國貴族和富商流行給自己的住宅安裝玻璃窗。英國的玻璃製造業在18世紀發展很快,到18世紀末,玻璃已經不再是奢侈品,但有些仍然很貴,面積較大的售價可高達每片404英鎊12先令。而且安裝玻璃窗的工序十分複雜,需要耗費許多人力,通常只有教堂才用得起大量的玻璃。簡 奧斯汀安排科林斯先生指出洛辛斯莊園有很多窗戶,而且裝了大量玻璃,是想讓讀者知道凱瑟琳夫人特別有錢,同時烘托伊麗莎白不畏權貴的性格。
關於居住方面,書中的例子還有很多,但我們先講到這裡,下面來看一個有關衣著的例子。這個例子出現在第一卷第八章,賓格利的兩個姐妹在批判伊麗莎白,路易莎 賓格利鄙夷地説:
Yes, and her petticoat; I hope you saw her petticoat, six inches deep in mud, I am absolutely certain; and the gown which had been let down to hide it not doing its office.
要理解這個句子,我們需要先弄清楚petticoat和gown這兩個單詞。在18世紀大部分時間裏,典型英式女裝由bodice(胸衣)、petticoat(襯裙)和gown(長裙)組成。襯裙類似于如今的半身裙,顏色通常和套外面的長裙不同,繡有花朵或者其他圖案。長裙分敞開式和封閉式兩種,前者由腰部向下呈V型敞開,旁人可以看見襯裙的樣子。貴族婦女為了維持裙擺的形狀,還會在襯裙裏面加上鯨魚骨製作的裙架。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句子的譯文:
是啊,她還穿著襯裙呢,你們應該看看她的襯裙,上面濺滿了泥巴,我敢説足足有六英寸高;她拉低了外面的長裙,想要遮住,但哪遮得住啊。
但就算把句子翻譯出來,讀者也無法理解路易莎 賓格利為什麼要特意指出伊麗莎白穿著襯裙。其實襯裙在18世紀末已經式微,等到《傲慢與偏見》出版的時候,倫敦已經很少有女性穿襯裙,當時流行的是長袖紗裙,但在英格蘭鄉村地區,胸衣、襯裙和長裙仍然是中上層階級女性的正式服裝。路易莎 賓格利特地指明伊麗莎白的穿著,目的是嘲笑她的打扮土氣過時,大概相當於現在北京或者上海的時髦女性嘲笑三四線城市的少女打扮得很殺馬特一樣。
在《傲慢與偏見》中,除了剛才談到這些衣食住行的例子,還有其他許多地方需要深入的研究才能徹底理解。我用了整整三年,查閱了數以千計的文獻,完成了這個帶有詳細註釋的譯本,值得講的例子很多,但限於時間,這裡我們就不再討論了,各位如果感興趣,回頭可以看看我的譯本。總而言之,就像我在這部小説的“導讀”中提到的,簡 奧斯汀這部代表作就像《女史箴圖》或者敦煌那些精美的壁畫,可惜經過歲月長河的沖洗,它的精妙之處在後世普通讀者眼裏已經模糊虛化。我希望通過我的譯本,以及譯本中盡可能詳細的註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修復它的本來面貌。
啰哩啰嗦講了這麼多,其實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從業十二年以來最深的體會:文學翻譯,尤其是經典文學的翻譯,是特別專業的事情,需要契而不捨的求索、旁徵博引的考證和持之以恒的付出才能做好。可惜絕大多數讀者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對文學翻譯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傲慢與偏見。
所謂的傲慢與偏見,就是那種認為讀譯本不如讀原文的心態。有一些讀者學過幾年外語,也許還留過幾年學,便自以為能夠看懂原文。但實際上,像《傲慢與偏見》這樣的經典作品,就算英語國家名牌大學英文係的教授,如果不是專攻18世紀英國文學方向,也是看不出什麼門道來的。
講到這裡差不多該結束了,我想借這個機會感謝一下我的出版人路金波先生和瞿洪斌先生,還有我的編輯趙海萍小姐。我三年沒交稿,金波應該挺著急的,但他從來不催我。瞿老師為了緩解我的壓力,有合適的機會就安排一起旅行,這三年我們去過兩次美國和一次歐洲。海萍特別有耐心,説實在話,有時候我也嫌自己做得太慢,但她總是寬慰我,跟我説不急,可以慢慢來。能遇到這樣的合作夥伴,我是很感激的。
最後謝謝大家來到這裡,希望我説的這些,能夠引起你們對簡 奧斯汀和《傲慢與偏見》的興趣,不過如果你們想看,千萬要看我的譯本。再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