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對於作家殘雪來説,是收穫頗豐的一年,她同時獲得了兩個國際文學獎的提名:美國紐斯塔特文學獎和英國倫敦的獨立外國小説獎,另外還與她的翻譯安娜莉絲共同獲得了美國最佳翻譯圖書獎。
面對獲獎的喜訊,殘雪很高興她的努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在她看來,自己能夠得獎,是因為學會了西方的思維工具,又將中國文化的特質很好地融入進去,讓西方人覺得很新奇。
但在國內文壇,殘雪卻似乎沒有得到如此的理解和認同,而她自己也不願意和中國文壇的人有更多的交流,甚至不願意再作出評價。“我早就説了,不抱什麼希望了,也懶得評價了。因為我搞這一套,他們不欣賞我,我也不欣賞他們那一套。”
在殘雪看來,中國的大部分作家固步自封,只知道守住和回歸傳統。但她認為僅僅這樣做是不能夠恢復傳統的,因為過去的已經是過去的了。“相對於西方的文化,中國文化有自己的優勢,但需要比較、學習和融合,只有再創造才能守住傳統。”
但其實1980年代的西學熱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再次促進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殘雪也是那批受影響的作家之一。不過在她看來,其他人已經放棄謙虛地向西方文化學習的勁頭,還是覺得自己的傳統文化好。
殘雪最近五年在研讀西方哲學家的經典作品,並且她還在寫一部批判薩特《存在與虛無》的作品,叫做《物質的崛起》。“文學與哲學探討的是相同的問題。只不過最近幾十年,文學的發展已經超過了哲學。”
她看到了西方現代社會最終指向的虛無,“現代人已經解決了吃飯穿衣的這些問題了,但他們面臨的是相互之間的交流、人際關係和感情等問題。”
“不過中國現在還沒有解決吃飯穿衣這些問題,所以後面這些問題在中國暫時好像還不是那麼大的問題,但也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殘雪試圖在自己新出版的小説《黑暗地母的禮物》裏描述一個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案。她説,這是一本慾望之書,也是在寫愛情。“就像瑞典的評論家夏谷所講的,我的幾本寫慾望的書描寫的都是人類社會的烏托邦,在探討什麼樣的關係是最理想的關係,什麼樣的社會是最理想的社會。我的探討是超前一點,但也不是超前得那麼不得了,因為已經出現了這種問題。”在殘雪看來,《黑暗地母的禮物》的讀者是具有現代精神的中國人,“可惜目前這種人很少。”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殘雪的專訪內容。
澎湃新聞:您自己覺得您的作品在英語世界受歡迎的原因是什麼?
殘雪:主要因為我的作品和西方文化的融合。在這個方面,我應該是在中國作家裏面做得最好的。所以國外的讀者能夠把我的作品作為文學來接受,我覺得這是很少有的,這一點我感到很高興。因為我的方法和其他作家都不同,我很謙虛、很努力地想去理解、認識西方文化,並且將其很好地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老老實實做了幾十年的工作。然後把我作為中國人的優勢在西方發揮出來了,所以他們覺得我的作品很新奇。要不然那麼多外國人都沒有得獎,而為什麼我的作品能被選中呢?如果我的作品類似他們曾經誕生的那些文學風格,比如卡夫卡、但丁、塞萬提斯等,那他們就沒什麼新奇感了。
澎湃新聞:在之前的訪談裏面,您提到了一些西方哲學的術語,比如説“自我意識”,那您是不是除了對西方的文學比較感興趣之外,還對西方的哲學比較感興趣?
殘雪:是,我最近五年裏一直在攻讀西方哲學。我搞了30多年的文學創作,而我這麼多年一直看西方哲學那些前輩的作品,現在越來越感覺到了我們這種實驗文學和哲學探討的是同一個問題,就是探討的途徑完全不同。而且在思想界,文學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取得的成就比哲學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所以我就想把哲學最根本的問題重新探討一下,也是我的野心。因此我一直每天堅持用四個小時讀西方哲學,已經堅持了有四五年了,黑格爾、康得和尼采這些哲學家的作品我都讀過。
我最近在寫一本批判薩特《存在與虛無》的書,現在已經在掃尾了,主體部分和導言都寫好了,需要繼續再檢查幾遍,可能有60多萬字吧。但我不是“文革”那種大批判。薩特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是西方哲學處在一個轉折階段的大哲學家。對照他的觀點,我把我的不同觀點表達出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有我的這個體驗。因為搞了30多年的文學創作,我和薩特等人面對的都是同一個問題,但作為中國人,我有我不同的體驗和想法。薩特不是自己也寫過文學嘛,當然他寫得不是太好,也算不錯了。所以我和薩特在這個方面特別有共同點。
但是我作為中國人,同薩特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我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圖型。我的那套生命的圖型跟他的存在圖型是兩碼事。我這本書既是講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這本書,也涉及了西方的其他經典,主要是黑格爾、康得、馬克思早期手稿等。一方面我通過學習了解他們的這些觀點,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們民族以前並沒有這種系統的哲學,這些邏輯系統都是從他們那裏來的;另外一方面我掌握了這些東西之後,就覺得我有優勢,可以用我這本書和他們抗衡一下。所以我在大概四年以前就開始寫這本書,現在還沒有完成,最後還差一點,不過也快了。
我自己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也覺得激動人心。因為我的觀點都是從我的文學創作中來的。“文學在這個方面是走在哲學前面的探險隊。”我一直這樣説,我在國際上跟那些外國人也是這樣説的。也就是説文學比起西方的經典哲學,已經走到它們的前面去了,文學現在更厲害了。
我是怎樣做的呢?通過學習西方,然後進行反思,再回過頭來看我們自己的文化,就産生了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藝術,實際上就改造和再造了我們自己的文化。我覺得繼承傳統只能通過再造或者重新創造的方法。創造出來的才是傳統,因為那麼多年已經過去了,你説你是傳統,他説他是傳統,誰是傳統啊?怎麼能夠肯定呢?這很難説的,過去了的就是過去了的,現在已經不是當時的那種環境了,很多東西都已經變了,你還説就只能是那樣搞,不創造,就是被動地去繼承一下,那是不行的。要恢復傳統必須要創造,而文學在創造性方面是最好的途徑。因為我們搞文學就叫做創造,通過創造把我們古老的文化再重新化腐朽為神奇,重新把它發揚。這是我的思路,跟我們國內的這些作家一般講的那一套繼承的思路不同。
澎湃新聞:對西方文化的興趣是受父母的影響嗎?
殘雪:有吧。因為我父親以前攻讀馬克思主義,家裏都有《資本論》那些哲學書,所以小的時候就看過,就激起興趣了。我記得我十四歲還是十幾歲的時候,把《資本論》都通讀過一遍,那個時候也給了我好的影響,打下了基礎。所以我後來搞的那種文學就是跟誰都不一樣了,人家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還以為我是那種本色演員,搞幾下子就沒有了。所以還是從小有這種氛圍的,有積累,到一定時候它就以文學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澎湃新聞:您和您的兄長鄧曉芒為什麼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個人選擇做文學,而另一個人選擇哲學?
殘雪:我跟他還是不同,他是那種比較冷靜的氣質,我可能更加現代一些,就是那種容易衝動的氣質。因為家裏到處、包括朋友和鄰居有那些書,包括俄羅斯和西方的文學,所以很快我就融入了文學的氛圍裏面,就被文學吸引過去了。十幾歲的時候是有幾年看過哲學書,後來很快就被文學吸引過去了,覺得文學更能夠吸引我。因為我看過的這些文學就是哲學嘛,它只不過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我現在説的這種方式——以物質的方式來表達精神的東西,一種情感的精神,其實和哲學就是一回事。
只不過因為氣質的差別,我很快就被文學吸引過去了。搞了30多年以後,再回過頭來看,發現我搞的這個東西確實有點優勢,就是在這些大師的指引之下,從但丁、莎士比亞開始,還有《聖經》,一直到後來的這些現代派,都給了我非常大的影響。而且讓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建立了自己的優勢,因為中國人是物質的民族,有這個深厚的基礎的。
澎湃新聞:您所講的“中國人是物質的民族”是指什麼?
殘雪:我是一個二元論者,我所指的物質就是精神,精神和物質二者是分不開的。西方把精神的那一維已經搞到了頂點,但是物質這一維還沒有起步,所以我們處在這個歷史的關頭了,就是我們古老的文化在這個歷史關頭面臨了機遇。這是我自己認為的,可以把物質這一維開發出來,就是物質和精神的一種抗衡。
我認為世界最高的終極設定就是精神和物質的抗衡,就是“有”和“無”的抗衡。我是一個二元論者。西方是一元論,認為精神至上。它的唯物主義的那種物質至上也不是真正的物質至上,因為它的物質沒有精神化。而我所講的這種“物質”是有形的精神,有品質的精神,所以這和黑格爾、康得都不同了。我的“圖型”也是有品質的,不是那種空靈的圖型了,而且更有力量,是從大地那裏面生發出來的。
澎湃新聞:那您和您的兄長會討論哲學問題嗎?
殘雪:討論啊。之前還出了一本書,叫做《于天上看見深淵》,就是魯迅的那句話了。在網路上賣得還可以,我看到印了一萬多冊吧,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今年一定要推出第二本,叫做《旋轉與升騰》,可能有70萬字吧,之前拖得太久了,現在得到了資助,所以一定要推出。內容還是我跟他的談話,第一本也是談話錄,談的是哲學和文學的關係,既談哲學又談文學。第二本哲學談得更多,基本上就談哲學問題和抽象問題了。
好多人都在盼望這本書,尤其是那些學哲學的,想從這裡面找到一些新東西。我跟他也不完全一樣,但是有共通的地方,另外他的哲學根基非常深厚,在這個方面可以指導我往前奔了,像探險隊一樣。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興起的西學熱對於文學的創作有沒有産生積極的影響?
殘雪:當然有積極的影響了,我就是這一批裏面出來的。當時出過不少好東西,包括最突出的像余華早期的創作,還有一個叫張小波的,我給他寫過幾篇評論,他寫了三篇中篇小説。梁小斌是後來居上,這些都算是一流的作品吧,那個時候他們的小説散文,就是拿到世界上去,也是拿得出手的一流作品。但是可惜後來就不再學習了,説還是中國的好,還是我們自己的更有東西可學,“自己的東西都沒學完,還去學人家”,都是這樣一種腔調了。
澎湃新聞:您之前在採訪中也談到,中國人對日常生活的態度缺乏一種自我意識,您能具體談談嗎?
殘雪:就是不善於分析自己,只是大家這樣做我就跟著做了,一窩蜂。到世界各地的留學生都要成堆,“個性”這些東西對於中國人來説還是遙遠的事情,包括我的作品讀者量也還可以,但是比起他們那種主流的傳統文學,銷量就少得多了。可能還是少數不滿意現實的年輕人來買我的書。當然能夠賣一萬多冊也不錯了,跟別的國家比較起來也算很不錯的,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還是太少了。中國人最喜歡的就是一窩蜂,一窩蜂就是我們這個文化最大的特點,沒有自我意識。要看別人怎麼做的,買房買車和賺錢,不都是看別人嗎?就像那個學者説的一樣,“要看自己,就難於上青天。”
澎湃新聞:這也是造成中國文學缺乏內省和自我批判的原因嗎?
殘雪:對,缺乏精神性的東西。精神性的東西的確是西方搞到頂峰去了,但是現在我自己回過頭來看,我們要把物質的這一維搞到頂峰去。我們現在處在一個轉捩點,也面臨最大的機會和挑戰。
澎湃新聞:您曾經説過《紅樓夢》也有缺憾,比如缺少性心理的描寫。
殘雪:《紅樓夢》是一個奇葩,它獨獨作為文學,就已經超越了中國的文化,這也是文學的特點。因為曹雪芹其實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藝術就有這個功能,有的時候它就超出自己的文化了,走到自己的文化前面去了。雖然曹雪芹口口聲聲説,自己好像比較提倡佛教,實際上你看他的那些人物,那些描寫,一點都不佛教,都是非常入世的,都是非常認真地追求一種理想的生活,一直追求到死。一個個都是那樣的人,哪有佛教?
這就是純粹藝術家的特點。《紅樓夢》遠遠地走在其他那些所謂的經典的前面,而且高出一個很大的檔次,達到了精神描寫的層次。因為他是藝術家,藝術就有這個功能,所以我説藝術是探險隊。哪怕你的文化還沒有達到這個層次。沒有描寫精神的文學作品,除了《紅樓夢》以外就很少了,有的有一點點,像《金瓶梅》什麼的,哪像《紅樓夢》這麼全面。因為曹雪芹是純粹的藝術家,他窮困潦倒,專門去追求精神的發展,所以才産生了這樣偉大的作品。
澎湃新聞:如果中國文學再有偉大的作品的話,是不是也不能再重復曹雪芹的這種方式?
殘雪:那不可能了,現在已經是新世紀了,需要在曹雪芹的基礎上重新創造。不能創造的話就別搞文學,守成當然也可以搞點通俗的東西,但不創造的話就無法傳承傳統。文學就是一個硬東西,是試金石。別的東西還可以説不創造,比如手工業等等,但是文學如果不創造,就不能夠守成,就會把以前所有的好東西都丟失掉。
澎湃新聞:有評論説,曹雪芹最在乎的是《紅樓夢》裏的詩詞,希望能夠流傳下來。
殘雪:那肯定流傳了,現在不是很多人在看嗎?連我以前對《紅樓夢》都迷的不得了。
澎湃新聞:但我們現在已經完全丟掉了舊體詩。
殘雪:用新的形式把它復活嘛,我現在寫的小説別人就有説像詩歌的。那種東西在我們的血液裏面,怎麼會丟呢?不可能丟的,但要繼續創造它才能夠發揚。
澎湃新聞:那您如何評價現在中國文壇的現狀?
殘雪:我早就説了,不抱什麼希望了,也懶得評價了。
澎湃新聞:那您平時和其他的作家交流多嗎?
殘雪:沒有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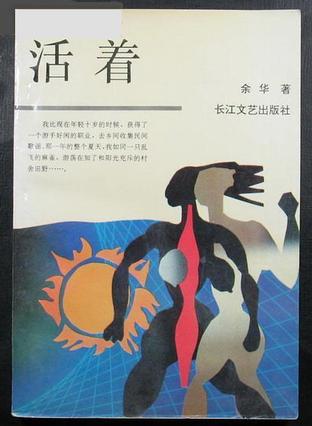
1993年余華的長篇小説《活著》首次出版,2004年余華因這部小説榮獲法蘭西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
澎湃新聞:為什麼會這樣?
殘雪:因為我搞的這一套,他們也不欣賞我,我也不欣賞他們那一套。我就寫過對幾個作家的評論:余華、張小波、梁小斌,就他們幾個是我欣賞的,當然他們有的也不再重視文學寫作,也出不來更好的作品了。
余華是早期的作家,但他後來轉向了。他們後來也寫不下去了,就沒寫。那他們自己也要負責任的,但是和大的氛圍也有關係嘛,對創新沒有任何支援,有時還要打壓。
而且那個梁小斌那麼苦,大家都為他募捐。你看這個社會都沒人管這些人了,所以他沒有條件進行創作,社會沒有保護他,他就感覺自己的境遇非常慘。連純文學都不要的民族是非常危險的。
澎湃新聞:您之前説過中國文壇的氛圍不好,講究“混圈子”,大家都在彼此唱讚歌,是這個原因造成中國沒有這種好的文學批評嗎?
殘雪:大家都要守舊,不和他們一起被動地回歸傳統,你就不是他們一夥的。異己就要受到排擠和冷落,然後就沒人管,像梁小斌這樣的情況就根本沒人管。
澎湃新聞:您為什麼説自己的作品是為二三十年後的未來寫作的?
殘雪:就是為現在的年輕人而寫的,過二三十年他們不就老成了嗎?就是為這些人寫的,還包括有現代精神的中國人,但因為有現代精神的這些人還不太多,我就沒有提。
澎湃新聞:為什麼寄希望於年輕人?
殘雪:現在具有現代精神的中國人數量比較少,所以我寄希望於年輕人,也就是現在20多歲的,再過20年可能就碰到精神上的問題了,物質不能夠再滿足他們了之後,就會有可能看我的書的,因為我的寫作是給人力量,使人獨立,塑造人的素質。我這本新書《黑暗地母的禮物》最重視的描寫就是人的素質。人要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在大地上站立起來,他應該具有一種什麼樣的素質?我做了一些預測,他們説我講的是烏托邦,但其實也是相當現實的。
澎湃新聞:您最近在讀什麼書?
殘雪:我現在還沒寫完手頭上的書,所以還在讀《存在與虛無》和法國的梅洛�龐蒂,一直在讀大哲學家的東西。文學方面在讀現在在歐洲比較走紅的那個奧地利大作家,叫做羅伯特�穆齊爾。現在我們剛剛翻譯了他的作品,在網上有賣。他們翻譯成《沒有個性的人》,當然我不太同意這個翻譯。這是一本很長很長的書,他一直寫到死還沒寫完的書,可能有一千萬字吧。我還比較欣賞這本書的上部,它跟我能夠合得上,他是西方人,所以我覺得還不夠滿足,對人性的描述還可以更進一步。

《沒有個性的人》登上了豆瓣“2015年度再版高分圖書”榜。
澎湃新聞:那能不能請您給年輕的讀者推薦一些西方文學的作品?
殘雪:就是剛才説的那本《沒有個性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我看的是英文的,年輕大學生最好是看英文原文,因為那個翻譯我看了幾章,我不喜歡,最好是看英文,因為他們都學了英文的嘛,為什麼不能看呢?
這本書裏面有一點烏托邦的性質,對未來也做了一些預測,他是1940年代才死的。不過還沒有像我搞的這樣的,就是完全跟現實結合起來。那個年代比我早嘛,現在現實的問題越來越緊迫了:怎麼處理你同家裏人的關係?你跟你老婆的問題怎麼處理?或者你跟女朋友的關係怎麼處理?這些東西以後都會是很緊迫的問題了。解決的方法就是交流。交流是一個核心詞,新時代的核心詞,交流其實就意味著愛,當然也意味著鬥爭。我這本小説就是專門寫這些問題的:什麼樣的關係能夠達到真正的交流。我一方面提出問題,另一方面我也嘗試做了一些預測,就是解決問題的預測,所以我這本是實驗小説,那裏面提出的東西都是實驗性的,而且很幽默,跟現實結合得很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