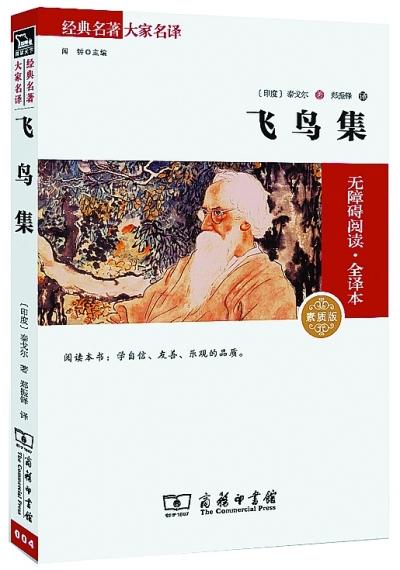
①由鄭振鐸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飛鳥集》封面。資料圖片

②由馮唐翻譯、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飛鳥集》封面。資料圖片

浙江文藝出版社社長鄭重微博截圖
“鋻於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馮唐譯本《飛鳥集》出版後引起了國內文學界和譯界的極大爭議,我們決定:從即日起在全國各大書店及網路平臺下架召回該書。”2015年12月28日,浙江文藝出版社社長鄭重在其認證微博上如此表示。
此前幾天,關於青年作家馮唐翻譯印度詩人泰戈爾《飛鳥集》的各種聲音,頻頻見諸報端、微信和網際網路。一時間,因馮唐譯《飛鳥集》而引發的經典作品翻譯問題,再度成為業界的熱點話題。
“凝練”與“媚俗”,眾説紛紜
提到《飛鳥集》的譯者,讀者不約而同都會想到著名文學史家、作家、翻譯家鄭振鐸。早在1929年,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詩人、翻譯家冰心也曾翻譯過包括《飛鳥集》在內的多部泰戈爾作品,但目前市面上流傳較多的還是鄭振鐸譯本。
2015年下半年馮唐翻譯的《飛鳥集》出版,因為其中一些充滿個人色彩的譯句,馮唐以及馮唐譯本被推到風口浪尖,眾讀者對此褒貶不一。李銀河認為,馮唐版《飛鳥集》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中文譯本”。有網友説,“馮唐的翻譯並不差,其中很多翻譯很傳神”。也有網友説,馮譯更凝練,鄭譯更雅,各有韆鞦。甚至有網友比較了馮唐譯本和鄭振鐸譯本,認為鄭譯本有些句子有點生硬,但是通俗動人;而馮譯本有些譯句多了詩意,但有些翻譯太個人化,讀起來一下子覺得“這個泰戈爾”添了些憤世嫉俗的感覺。
譯林出版社原社長李景端對馮唐譯本感到相當遺憾,認為“這種翻譯出格了”。“馮唐的翻譯違背了翻譯原則,語言媚俗。一部作品,在歷史演變過程中,由不同譯者呈現出不同的翻譯風格,這一點也不奇怪。但是馮唐不顧經典名著本身的學術屬性,完全走市場化道路,超出了出版底線。著名翻譯家楊絳先生曾經將譯者、作者和讀者的關係稱作‘一仆二主’,認為譯者作為‘僕人’要為作者和讀者兩位主人服務。所以,譯者不能只顧討好讀者、吸引眼球。”李景端補充道。
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國際翻譯家聯盟前副主席黃友義分析説:“從目前的討論看,大家的注意力沒有離開追求再創作的個性和遵循信、達、雅的翻譯傳統這兩條主線。”作家創作作品要追求個性,同樣譯者翻譯也是再創作過程,也會追求個性。黃友義認為:“有個性,就會有爭論。需要特別關注的是,譯著的個性是否大大超越了原著的個性,從而背離了原著的思想資訊和創作背景。”
“翻譯沒有‘信’,譯文難‘達’‘雅’”
“我是中文超簡詩派創始人,詩歌長度通常比唐詩七絕五律還短。據説《飛鳥集》也是濃縮得不能再濃縮的詩集,我想仔細見識一下。”馮唐在其博文《翻譯泰戈爾〈飛鳥集〉的27個剎那》中如此記載。他坦言:“在翻譯過程中,我沒有百分之百尊重原文,但我覺得我有自由平衡信、達、雅。”
對於“信、達、雅”的標準,黃友義想起美籍華人張振玉教授的觀點。“張振玉曾經翻譯了《最美英文抒情詩》。在其自序中,他對翻譯界最著名的理論‘信、達、雅’有一番精闢的解讀。張振玉認為,‘信’不是單純追求原作表面形式的信,翻譯得吃透原文的精髓,譯者必須準確理解原文、忠實傳達原文所包含的文化資訊,才能實現‘信’和‘達’的目的。至於‘雅’,則是有了‘信’和‘達’之後的一種藝術水準的體現。”黃友義總結為:翻譯沒有“信”,譯文難“達”“雅”。
“我們今天翻譯幾十年、上百年、幾百年以前的作品,首先有一個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問題。譯者身處今天的文化環境中,要認真體會和理解原著及作者在那個時代的思維習慣和社會環境。”按照黃友義的説法,如不揣摩當時的社會背景,譯者就不一定能準確掌握原著的意思,甚至會覺得原著表達的內容不可思議。作為再創作者,譯者既要深刻了解原著的創作時代和環境特點,也不能忽視時代的變遷和語言的變化。
黃友義邀請讀者思考一下:《飛鳥集》原著所使用的表達方式在當時的社會中屬於哪一種風格、哪一個流派、哪一個階層?其語言屬於通俗還是儒雅?同樣,讀者也可以考慮一下:馮唐的譯文是否與原著完全吻合?其譯文是否真實再現了原著的風格、流派和社會階層?譯文語言是否屬於當前的流行風格?
以黃友義從事翻譯事業40年的經歷來説,他感到在翻譯界,詩歌的翻譯往往爭議最大。“不同的譯者為同一部著作的譯文風格而爭論不休是十分常見的事情,這是學術上的一種常態。也許圍繞《飛鳥集》的討論對將來的詩歌翻譯會有積極作用。”
翻譯立法是解決之道?
“當前,翻譯界面臨的最大問題還遠不是《飛鳥集》所引發的討論這麼簡單。”黃友義強調,翻譯報酬低、翻譯作為再創作不被認可、翻譯處於一個産業鏈的末端得不到應有的理解,是職業翻譯們的普遍困惑。“同時,翻譯市場不設門檻、缺乏品質監督和評價機制,翻譯作品泥沙混雜、翻譯公司競相壓價也是現實。作為再創作,翻譯需要時間和空間等必備條件,但使用翻譯的單位,包括一些出版單位,卻不予理解和支援,也是影響翻譯品質的原因。”黃友義説,人們經常批評那些“離譜”的翻譯作品,並嘲笑所謂的翻譯人員,殊不知絕大部分“離譜的翻譯”根本就不是職業翻譯所為,而是略懂一點兒外文的“二把刀”。“翻譯人才職業化的培養、評價機制在我國才剛剛開始建立。一個經常依靠非職業人員從事的專業,出現爭議和問題完全在情理之中。”
一些翻譯界人士認為,從事翻譯工作需要有制度可循。律師辦案有律師法,會計算賬有會計法,醫生行業也有若干相關法律法規,而翻譯業卻完全沒有專門的法律。黃友義代表翻譯界呼籲翻譯立法已經多年:“由於翻譯工作分散在各個行業當中,我們國家沒有一個部門能夠統管各行各業的翻譯工作。沒有統管部門,翻譯立法也就寸步難行。我倒是希望,《飛鳥集》譯文事件能夠引起人們對翻譯事業的關注,推動翻譯立法,進而促進中國的整個翻譯業健康發展。”
(本報記者 劉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