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頻,畢業于蘭大中文系,現任雜誌編輯。代表作有中篇小説《同屋記》《醉長安》《玻璃唇》《隱形的女人》《淩波渡》等。曾獲2010年至2012年度“趙樹理文學獎”。
讀者對於80後女作家孫頻的印象,不僅是她的名字曾經頻繁地出現于各類文學期刊上,更是源於她的寫作風格。她對於女性心理,有著近乎執著于細膩而深入的刻畫,並且,她有著女作家不常見的兇狠的筆調,而其辭藻,竟然是艷麗的──這讓她的作品,帶著一種怪異的閱讀體驗,張愛玲所説,“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與這種體驗大抵相似。
前不久,孫頻的新作《三人成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這是繼2014年《隱形的女人》之後,她的又一部中篇小説集。在這部收錄了《三人成宴》《不速之客》《一萬種黎明》《瞳中人》和《骨節》五個中篇的小説集裏,孫頻以慣有的筆調,出眾的敘事才華,聚焦于城市男女的情感生活。儘管小説切入的視角不同,但每一個故事的重心,仍舊是那些在飽受情愛失衡之苦的女性。
作為近幾年才嶄露頭角的年輕作家,孫頻的側重於“女性敘事”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在於,頻繁地書寫女性,是否會帶來重復敘事的困擾?事關男女情感,為何在她的筆下總是糾結不堪?她著力於發掘“社會人”自身“困境”的寫作指向,又有著怎樣的寫作上的選擇?這一切,都在與記者的電話交流中,得以一一呈現。
我喜歡有力量的寫作,力量之中還帶有一些暴戾氣質
記者:看到《三人成宴》,免不了就會想起《隱形的女人》,因為在這兩部集子裏,有著相同的對於女性不遺餘力的書寫,這是因為你自己本身是女作家,還是純粹只是寫作上的選擇?
孫頻:我的作品裏主人公是女性的要多一點,但我並不是只寫女人。這次的五個故事都是關於女人的敘事,是因為出集子的時候,選擇的是同一個主題──都是關於男女情感類的。涉及男女情感的作品,其主人公無非就是男人和女人。當然,我可能會比較傾向於從女人的角度來寫,因為對女性更了解。
記者:我們經常會説到所謂的寫作慣性。頻繁地書寫女性,尤其是女性的情感困境,似乎會陷入重復敘事的境地。至少從《三人成宴》的五個故事來看,同樣糾結、矛盾且痛苦的情感,同樣絕望、茫然的尋找,很容易讓人産生近似的閱讀體驗。
孫頻:無論寫什麼,其實都是在反反覆復表達一個主題,這樣的作家很多,我覺得我的情況可能與這個類似。《三人成宴》裏的五個中篇並不是同一時期創作的,寫的時候我確實沒有意識到它們之間的相似性,當然結集之後給別人看,可能就能看出來。出現這種重復敘事,我覺得,可能與我自己對某些事情的看法以及內心的糾結是有關係的。你的內心一直在強烈關注的一個問題,在你的作品裏展現出來之後,就會看到同一個思維的影子。
記者:我所説的,其實不僅是指這種題材上的重復。在《不速之客》裏,紀米萍每過一段時間就要遠道而來探望蘇小軍,而在《一萬種黎明》裏,張銀枝則分春夏秋冬四季去看望桑立明。這種模式的雷同,更加會讓人産生疑問。
孫頻:可能是因為我覺得,在這種模式裏,能把兩性在一種非常絕望非常受虐的情況下比較另類的一面表現出來。也就是説,我不把他們放在很平靜的環境之下,我喜歡讓他們處於一種帶一點受虐的環境裏,這樣才能把相對殘酷的東西寫出來。
記者:你會考慮它們的極端性嗎?我們所理解的生活裏,你所設定的環境畢竟不是一個常態。
孫頻:在平時的寫作裏,我一般都會選擇相對比較極端的題材,把人往絕境裏走。我不是很喜歡類似于門羅小説的那種比較清淡的寫法,寫一些細小瑣碎的常態的東西。每個寫作者的氣質是不同的,我喜歡更有力量的寫作。但你説小説裏的力量感是怎麼出來的?我覺得,就是在這種劇烈的衝突之下,在絕境之下,人物的命運和心理的扭轉才會更容易給人衝擊感。個人氣質也罷,閱讀範圍也罷,我都會比較喜歡這類小説,所以在自己創作的時候,也會往這個方向走。記者:你提到了個人閱讀,你受誰的影響比較多?孫頻:我非常喜歡奧康納,他非常有才華。我也喜歡安妮?普魯、三島由紀夫,當然還有胡安?魯爾福。這些作家來自於不同的國家,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題材上和處理情節上,都屬於那種比較有力量的類型。我就喜歡這種風格,力量之中有時候還會帶有一些暴戾氣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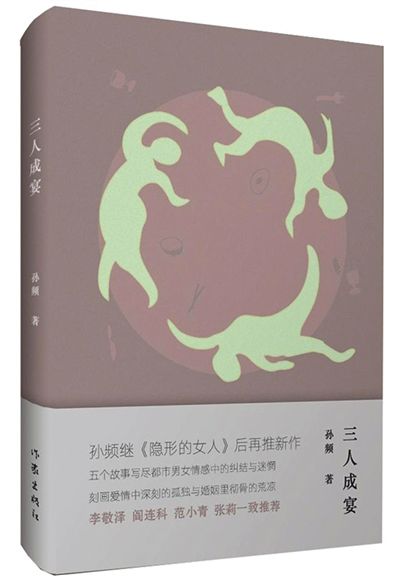
我希望筆下的人物,複雜而有深度
記者:在《》裏,感情受傷的鄧亞西,預料到自己會精神分裂,匆忙地“抓住了李塘”,《不速之客》裏的蘇小軍之於紀米萍,也無非是一個可以“抓住”的對象。她們不是為了錢財,為的只是可以産生的那一丁點依賴感。
孫頻:你説的依賴感,沒有錯。但我想強調一點,在我的小説裏,比較喜歡往人的精神深處甚至病態方向去探索。一方面,在小説題材上,我的小説不屬於那種宏大敘事型。我不喜歡所謂的緊扣時代,抓住時代的命運,我的小説屬於往精神深處走的比較“內化”的小説,我只對研究人的心理感興趣。另一方面,這也與我個人有關──其實也並非是我個人,很多人都是如此──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疾病或者病態人格,我心理上有什麼問題,就把它外化成一部小説,對我自己來説,寫作的過程就是一個治愈的過程。對於讀者而言,閱讀的過程,同樣也是一種治愈。我的小説裏心理學的特質是相對比較明顯的。不僅是《三人成宴》,我的很多作品裏都有。
記者:所以,人物才會如此設定?鄧亞西、紀米萍、張銀枝,又或者余亞靜、夏肖丹,每一個都有心理問題。
孫頻:對。我在寫一個人物的時候,這個人物當然是虛構出來的,但這個人物所賦予的某種性格或者某種心理特徵是我提前就想好的。我就是要寫這樣一個人,才把性格特徵和心理特徵安到這個人身上去。
記者:像《不速之客》裏的紀米萍,她用和異性發生關係卻不收錢來證明自己不是妓女,用和人發生關係但沒有接吻來證明自己的純潔。為什麼你要將小説寫得這樣有衝擊力?
孫頻:這是小説,不是心靈雞湯,不是為了塑造一個美好純潔的東西去安慰人。小説是怎麼産生的?我覺得,是因為內心不平衡,有了衝突,然後又試圖把這些衝突和不平衡內化地處理掉,才會出現文學藝術的形式。儘管,文學嬗變到今天,已經附加了很多外在的要求,但我認為,文學從來就不是光明的東西,文學最初的動機,就是要表現人物內心非常黑暗的一面。
記者:可是也有很多作家,在生活裏發現小人物的美和善意。你為什麼願意選擇這種比較糾結、粗暴的東西?
孫頻:我的小説中,也有女性那種很溫暖的東西。我並不是完全不寫,只不過,我不會把它作為一個主調去寫。對我來説,面對女性如何善良溫暖的命題,我沒有表達的慾望。如果每個人都去寫那種小美德小感動,都給文章加上溫暖的尾巴,所有的人讀著都要淚流滿面,這會有什麼意思?總得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形態出現吧。
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很多非常優秀的作品都不是在寫人的善。在我的小説中,的確是經常寫猥瑣陰暗的東西,但也並不純粹都是猥瑣陰暗的,他們的身上,美與醜是並存的。我並不是要寫人性的醜惡,而是要寫人性的複雜。我的標準是,越複雜越好,因為越複雜,才越接近於人性的本質。評價這個人多麼的好或者多麼的壞,都是把人過於簡單化了。我希望筆下的人物,複雜一點再複雜一點;內心的深度,深一點,再深一點。
我跨越青春書寫,直接就進入成人寫作
記者:在你的小説中,使用比喻的頻率很高。《三人成宴》的第二段,開頭是這樣的:“樓道像廢棄的空罐頭瓶一樣荒涼,腳步聲一裝入其中便四處是丁零當啷的回聲,像是發酵過了一樣,溢得到處都是。這腳步聲從一樓慢慢升起來,回聲像鈴鐺一樣係在上面一直跟了上來。這腳步聲裏夾著些躊躇和陌生,像未熟的米粒堅硬地夾在一鍋飯裏,硌著她的耳朵。”用這種物化的比喻,來描摹情境或者是人物的心態,這種感覺,明顯帶著某種炫技的色彩。
孫頻:每一個作者可能都在尋找一種相對獨立的寫作風格,讓自己的文字帶有很強的識別性,別人一看就知道是誰寫的。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找到一種自己習慣的修辭手法,然後這樣能夠更好地表達你的意圖。我可能就是選擇了比喻。但是像你説的,有時候用的的確太多太密集。
記者:一個絕妙的比喻,會給文章增加很多趣味和內涵,你的小説是要內化的,需要勾勒很多不可言傳的情緒,這是不是你不得不多用比喻的原因?
孫頻:可能還是我自己比較喜歡這樣。有時候寫出一個相對比較美妙的比喻,自己也會有愉悅感,然後就會流連其中。
記者:有評論説,孫頻的小説,不同於80後多寫青春困惑、成長煩惱的書寫特徵,反而著力於發掘表現社會人自身的困境。你怎麼看?
孫頻:青春成長小説,那是屬於“新概念”一派擅長的東西。他們出道早,出名也早,以他們當時的年紀,也就只能寫這種東西。但我是二十五六歲才開始寫作,早已過了青春困惑的年紀。在我看來,寫青春困惑的人,家庭出身一定是相對較好的,一般是在城市長大,沒有經歷過多少挫折,才會那麼執著地寫青春困惑。我一直自稱是城鄉結合衝撞出的"屌絲寫作",在縣城長大,所接觸到的也都是一些小人物和相對比較困苦的底層生活。從小接觸到這些東西,決定了我不可能帶著撒嬌和優越感去悼念青春。我沒有經過那一步,直接就進入成人寫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