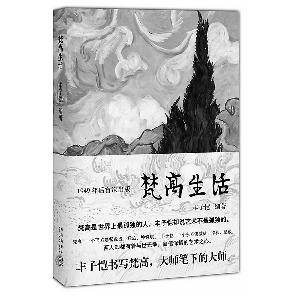
古往今來,從事同一行業的人彼此間都有這樣那樣的矛盾。這種“同行相輕”在文人、藝術家中間更為明顯。他們將彼此視為對手,暗自較勁,相互拆臺。不過凡事總有例外,因為創作上的認同,他們之間往往能産生一種超越種族、跨越地域的情誼,這就是所謂的“惺惺相惜”。憑著這樣的情感,豐子愷寫下《梵谷生活》也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了。在這本出版于1929年的傳記裏,豐子愷以獨特的東方視角還原梵谷跌宕起伏的一生。豐子愷説畫,自己也精於繪畫。他寫梵谷,猶如提筆作畫。作畫時他常常選取普通市井人生的某個場景入畫,寫梵谷時他沒有以常規的藝術評論家口吻對其作品大加評論,而是將視線對準其人其事其生活,以生活還原人物,進而復原藝術。
豐子愷自稱在梵谷作品裏讀出了一種“東洋”的神韻。他認為,西洋繪畫與東方繪畫的區別不僅僅在於線條、構圖、技法,更在於畫家的態度。西洋畫講究技法,畫家窮盡一生力氣研究如何以精妙的畫筆復原真實,使“所描繪的形象與客觀對象取得最完善的一致”;東方畫講究情,畫不在形似,但求神似。西方藝術中創作者與作品之間總是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作品是作品,人是人。而東方繪畫則恰恰相反,常常是人畫合一,因而格外講究內在的感觀。出生於牧師家庭的梵谷從小就擁有悲憫世人的胸懷,立志拯救世人于水火之中。他從未接受過專業繪畫訓練,因為熱愛而拿起畫筆。在他一生裏,從來沒有為創作而創作、為表現而表現。因而梵谷的畫作並無匠人之氣,不是“技術的産物”,而是“熱情的産物”,其中“自有一種法則以外的正確與真實”。
如果將梵谷的作品視為脫離生活的創作,豐子愷一定不會同意。在梵谷的一生中,他並未脫離過這鮮活的世間。“梵谷的生活是其作品的説明文”,是熱血所染成的“人生記錄”。梵谷的人生與作畫卻是合為一體的。他的作品是創作,人生是另一種創作,兩者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作品濃縮了他的人生,人生又是畫作的注腳。在梵谷早期作品裏不乏對貧苦人生的直接描繪,諸如米勒的《拾穗者》似的人物比比皆是。《吃馬鈴薯的人》以壓抑暗沉的色調與後期金黃色的麥田、藍色的星空形成強烈反差。反觀當時大受歡迎的印象派畫家的作品(比如莫奈的《日出�印象》)美則美矣,卻像是機械複製的風景,總是少了一絲生氣。而梵谷卻不然,他滿懷對生活的熱愛,火紅的鮮花、深濃的綠葉、炎炎的烈日,生存之苦都化作筆下的濃墨重彩——早期他將生活所見融入創作,晚期又以畫作排解人生之苦;活得越是苦悶,色彩反倒越是濃烈。
在豐子愷看來,梵谷“人品既高,氣韻不得不高”,他從不迎合市場,從未以手中畫筆取悅市場,創作為世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他拒絕參與製造沒有生命力的繪畫,砸碎石膏像,更痛斥“商賣是圖利,圖利是上品的盜竊”。也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創作理念最終導致了梵谷的不幸結局。當時的人們寧可選擇中規中矩的畫作,也不接受天才標新立異的獨創。在《侏儒警語》裏,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將自己比做“醉春日之酒誦金縷之歌的侏儒”。梵谷也是這樣。他的聲名與他生前的待遇是不對等的。這位影響過後世諸多畫家的畫壇“巨人”,生前卻是籍籍無名的“侏儒”。梵谷27歲才開始繪畫,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創作了數千幅油畫。吊詭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裏,他的作品乏人問津,只賣出一幅油畫、兩張素描。直到1889年梵谷才等來了第一個讚美。這讚美來得太遲,僅僅幾個月之後,他就因為精神崩潰而自殺身亡。
畫家解讀畫家,本來就不能以常理來衡量,何況又是喜歡的對象。傳記本應是中立的、客觀的,《梵谷生活》實際上並不客觀。這不是一本通常意義上的藝術家傳記。豐子愷常常忘記身份將自己對於藝術的理解帶入寫作之中。豐子愷讀梵谷,其實讀出的是他自己。他以畫識人,由畫及人,慢慢進入梵谷的內心。他以清淡、樸實的語言記錄梵谷的一生,也傾吐他的感想。《梵谷生活》雜糅欣賞、讚美、狂喜、惋惜、悲傷等多種情緒,遠遠超出一本傳記的容量。豐子愷和梵谷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瘋。當寫到梵谷因為不堪忍受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折磨選擇自殺了結之時,我們甚至可以從字裏行間聽到豐子愷的一聲嘆息:他以頗具東方中庸之道的解讀,為西方畫家梵谷平添上一抹東方的韻味。谷立立
《梵谷生活》
豐子愷編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