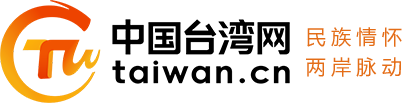不負責任的美式民主
曾有不少人相信,美式民主是一種負責任的制度,他們的理由無外乎“有選舉才有問責”“法治程式帶來責任制”。事實上,美式民主是一種高度類似于有限公司的制度,制度的初心並非對人民負責,而是僅僅服務於作為“股東”的資産階級和各種特殊利益集團。
從時間上看,缺乏代際責任
一個國家是這塊土地上人們的共同空間,其制度也應反映當代人與後人之間的有機聯繫。但在這方面,美式民主存在缺乏代際責任的弊端。
美國選舉是一種即時性授權制度,所授予的是某一政黨有效期四年的權力。在美式民主下,政黨不是一個能夠代表人民長期、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其服務於資本集團早已是公開的事實,其最高利益就是通過執政影響政府決策,但這種決策,如發行貨幣、借債投資、發動戰爭、開發資源等,不僅影響四年,而且會對後代人的命運影響深遠。
美國兩黨輪流坐莊加劇了這個問題。在兩個政黨爭取選舉授權的情況下,執政者缺乏制定執行長期政策的動機和能力,頻繁的政府更替帶來的最直接後果就是政策的短視,無法對長期發展負責。壞的政策可以通過政府更替來停止,但好的政策同樣會被廢除,這就是美國每四年發生的事情。
另外,政策效果的呈現需要複雜的傳導過程,所以政策通常會有滯後效應。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權力中心進行耐心的觀察、試錯、管理,就無法依據政策的中長期後果進行反饋調節,這可能導致振蕩現象。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多黨競爭制度不僅無法做到反週期調節,反而會加劇政策搖擺。
從空間上看,消解整體責任
從空間角度看,美國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地方性”因素過重,缺乏整體責任。美國最初是由十三個州拼接而成,中央權力的産生源於各州權力的向上讓渡。這種結構導致了權力“其專在下”的問題,而美式民主的選舉代議制度就是産生於這個結構,因而無法克服其先天短板。
選舉制度將地方利益傳導至國家政治中。美國選舉制度以選區為基礎。一個選區的代表自然首先要代表該選區的利益。各級選舉將地方性利益一層層向上傳導,最終輸入國家政治生活之中。在日常立法和政策制定過程中,各種地方利益的博弈和交易會造成低效、浪費及各種荒唐現象,例如美國國會中常見的“豬肉桶法案”現象。一旦發生嚴重的國內利益衝突,國家政治生活就會發生顯著分裂,如體現為立法機關中的分裂極化。在這種制度下,如果再疊加上兩黨競爭和贏家通吃型的投票制度,還會導致地方性的不斷自我強化。
“多元主義”政治過程為特殊利益輸入大開方便之門。所謂“政治多元主義”,名義上是指各種社會力量可以公平競爭、影響政策,實際上只有各種特殊利益集團才能夠廣泛深入介入政治過程之中。“政治多元主義”除了傾向於將腐敗行為合法化、服務於權錢交易外,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危害國家的整體性責任。任何一種規則與制度都絕非中性,強者和精英天然更擅長充分利用制度的規則為自己謀利,因而在多元主義政治過程中,政策和法律極易被各種權勢集團所綁架,導致特殊利益壓倒整體利益。
兩黨競選加劇社會和文化撕裂。美國的兩黨制天然具有宗派性。在國家發展比較平穩、政治比較健康的時期,兩黨制的弊端尚不明顯。但是每當共識消失、國內社會分裂時,兩黨力量又勢均力敵,就會形成對峙局面。這在美國是常態。當此之際,兩黨為了贏得選舉,政客為了個人的政治生命,均傾向於抓住和利用選民中的分裂性因素,挑起紛爭,強化自己的政治優勢。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無論左翼的文化多元主義和各種身份政治的興起,還是右翼保守主義掀起的“文化戰爭”,都離不開兩黨政治的刺激和強化。今天這種文化戰爭已經成了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的根源之一。
從結構上看,規避主體責任
除了時間和空間維度,美國政府的設置在結構維度上也豁免了政府的主體責任。表面上看,美國制度是以選舉為基礎,但是民選機關只擁有一部分權力,還有大量的重要權力由非民選機關,甚至是以私人組織為基礎的機關來行使,這些機關既然不是由選舉産生,自然就不對選民負責。
司法權力不受選舉民主的約束。自美國建國之初,最高法院就獲得了對國會立法進行憲法審查的權力,不僅獲得了美國政治中的最高權力——憲法的解釋權,而且實際上擁有了部分立法權力。另外美國政治生活本身具有法律化的傾向,這也導致司法權在很多方面可以侵入行政權的範圍之內,法官取代行政官員決定重大行政事務的現象在二十世紀以來十分普遍,甚至導致行政機關本身的律師化以及整個美國的“律師治國”現象。如此重要的法律權力,卻以專業和中立的名義游離于任何民主程式的監督之外,不用對選民承擔任何直接的責任。
貨幣權力不承擔任何民主責任。美國的貨幣發行權由私人銀行組成的美聯儲掌握,政府發行貨幣實際上是向美聯儲借債。正如威廉�格雷德《美聯儲》一書所説,美國的體系更多靠的是交易而非選舉,美聯儲就是一個不受選舉約束的機構,一個緩解“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本質對立的機構。這個掌握著美國人的財富和命運的機構,在設計上就標榜與政治權力絕緣,但實質上卻是一個以“獨立”的名義控制貨幣和金融權力的、為資本集團深刻控制的機構。在這個意義上,選舉、民意、輿論都與它無關,人民既難以影響它,也無法加以監督,它除了代表資本的利益,根本沒有對於人民的責任。
文官集團掌握實際權力而不承擔政治責任。美國建國之後並無正式的官僚制度,也無專業的文官群體,國家管理模式是“政治分贓制”。每次選舉之後,由獲勝政客的私人扈從和職業黨棍掌控國家權力,腐敗不堪。1883年之後,美國才有了職業文官,但這個群體完全處於選舉式民主程式之外,暗中掌握著實際的權力。他們是非政治性的,名義上是為了不受選舉政治的影響,維持國家的穩定和政策的專業性、延續性,但是這也使他們豁免了政治性的責任。他們與大企業、大銀行及各種利益集團、議題集團保持著密切關係,維護著圈子裏人員、金錢和資訊的流動,形成華盛頓特區環路內的“沼澤地”。純粹民選的政客對他們而言是“圈外人”,政客們在舞臺聚光燈下表演,官僚集團則躲在“深層國家”後面暗中操縱。
從以上三個維度看,美式民主制度並非真正的民主,其不承擔對於人民的責任。這種制度在政治上自然秉承著有限責任的原則:三權分立,就是讓責任無處可尋;聯邦政府權力的有限性,就是對其責任的豁免;選舉制度、兩黨制等加劇了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責任缺位;司法權、貨幣權和行政權則處在人民的監督和控制之外,成功規避了實現良好治理和保障人民權利的政治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