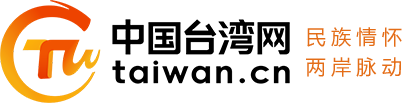擺攤之餘出了2本書 菜市場裏的女作家:生活永遠第一位
本報記者鄭夢雨
陳慧沒有想過會成為作家。
媒體鏡頭突然對準她,她沒感到多麼驚喜。“你跟賣燒餅的説你上電視了,燒餅會便宜嗎?出了兩本書,日子沒什麼改變。”她一直認為自己就是一個菜市場裏的“二道販子”,“寫作是愛好,生活永遠是第一位的。”
曆盡生活的捶打,她在菜市場細數人間百態,用文字撫平心裏的褶皺,將生活的疙瘩捋順。
日子在熱鬧和安靜間迴圈往復。當切身之痛轉化成深層的自我抵抗,一個鄉村婦人的韌性,從原始中生長出來。
“很多個陽光燦爛的午後,我只是像一朵黑乎乎的香菇一樣,端坐在我位於小溪邊的山間房子裏,慢吞吞地寫著我想寫的文字。”陳慧寫道。
她坐在窗口,臉上落滿大山的影子。
長長短短的家事:
菜市場是值得的
“過去的一陣非常擁擠”,陳慧在最近的文章裏寫道,“我的世界正在逐年地削減,剛剛濃縮成了一枚與我期望相吻合的琥珀,忽然有扛著錄影機舉著話筒的人陸陸續續地從外部鑽了進來。”
過去一段時間裏,接待媒體來訪變成了她的任務,想寫的文章拖拖拉拉沒有完成,“老有記者來打斷我”。有人到她家探訪,她只能讓他們在家門口等著,沒有人能阻礙她做完上午的生意,“他們來了走了,就像一陣風過去了,但我要賺錢的呀。”
我在菜市場見到陳慧時,她正被一圈人圍著,一根短辮低低紮在腦後,皮膚黢黑,嗓門洪亮,拿貨、找錢、寒暄,爽脆利落,挎在身上的黑色腰包裏裝著一疊五塊十塊的鈔票和一些鋼镚兒。
因為排行老三,在余姚梁弄菜市場,大家都叫她“阿三”。每天清晨不到6點,她推上自己改裝的推車,裏面塞滿了上百種生活百貨。菜市場裏的攤主們、梁弄鎮上的鄉親們都知道,擺攤的“阿三”風風火火,“像個男人一樣”。
她常年擺攤的那條小街在菜市場邊,因為她而出名,人們都説買百貨就去“阿三擺攤的街上”。她的小攤子像是一個被留在時代遠處的地方——來往的大都是老年人,嘴裏説方言,用現金交易。她賣的也是一些生活的角落裏用到的東西:砂鍋夾、蒼蠅紙、螞蟻藥、做衣服的頂針、打肉的錘子、割稻的鐮刀、魚鉋子、暖瓶塞,甚至剪刀都分成好幾種:剪指甲的、殺雞的、陪嫁用的……
26歲時,阿三從老家江蘇如皋嫁到浙東小鎮。在此生活的17年間學會了地道的梁弄方言,在菜市場不僅能和村裏的老人無障礙溝通,親切地喚每個婆婆“姆嬤(當地方言‘媽媽’的意思)”,更是提供“售後服務”,給每個老人把東西裝好,教給他們用法,用壞了免費幫他們更換。
孩子9個月大時,生活所迫,陳慧出來擺攤。她覺得面子放哪兒也沒用,受了委屈就忍著,吃了虧也不叫喚。十幾年來,路上遇到的都是熟人,她的生意不斷被這裡的人照顧著,路過的姆嬤説,“她人好啊,找她放心。”
她喜歡菜市場,那是一個親切、溫暖、充滿善意、生機勃勃的好地方。人與人的關係簡單,她客氣地對待顧客,也經常得到顧客的惦記。“那些年紀大的人,十多年了一直找我買東西,找不到我的話,會一直問我去哪了,那種感覺讓我覺得人間是值得的,菜市場是值得的。”陳慧説。
她也能找到小時候“熟悉的東西”,賣吃食的小攤、麥芽糖、棒冰……這讓她想起人生中最美好的童年時光。“生活不盡如人意,我願意往回看。”
在菜市場裏,她汲取寫作的靈感。養父母“拉拉扯扯半生的婚姻”、銅匠遭大病後終於戒了煙、開雜貨舖的老闆娘説起瘋兒子紅了眼眶……這些成為她筆下的人物。菜市場裏的物什也變成了她的修辭:燈泡像“乾癟的橙子”,自己則是“貼地生長的牛筋草”。
從菜市場回家的路,要經過一條長長的斜坡。陳慧使出全身力氣,推動一兩百斤重的一車“生活”向前走。
有了點積蓄,她往家裏搬了臺冰箱,房間裏裝上了空調,“想活得舒坦一些”。
在這個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裏,她的日子簡單得分不出昨天、今天和明天。過去的生活像是困在一口井中。“其實我每次只翻動一塊磚,我不停翻,就想透些光亮、讓新鮮空氣進來。”陳慧説。
那一天,她嘗試著,從井裏鑿開一道光。
筆下皆是身邊人:
真實粗糲,結實又有活力
上午10點左右,梁弄菜市場的熱鬧勁兒散了。收了攤,菜場裏的熱鬧活絡連同攤車上的百貨一併被收起。陳慧拎著兒子愛吃的西瓜,跨上一架男士摩托車,騎到東溪橋頭,拐入一條村道,通向幾百米外的小萬家村。
一條小溪旁的小平房就是陳慧的家。
凳子長久沒有人坐,擱“荒了”;客廳電扇的腿也壞了,醉漢般地搖搖晃晃。一台老舊的臺式電腦擺在臥室窗口邊,黑色外殼,鍵盤縫隙裏積了厚灰,鍵面被磨得锃亮。
十幾年間,除了在菜市場擺攤外,她大多數時候就這樣待在房間裏。
2010年冬天,她從菜市場抱回一台電腦,牽上網線,註冊了一個QQ號,在自己的QQ空間裏斷斷續續敲下一些文字:
“我想燙頭,我想修眉,我想顛覆自己,我想還是算了。”
“內衣是女人的佩槍。菜市場的內衣店裏賣花花綠綠的內衣,但是我只穿不帶海綿的內衣。”
……
最初的寫作無關文學,流水一樣,斷句、篇幅隨心。她對著電腦傾瀉一通,覺得“心裏好舒服”。一年多後,文章的雛形出來了。
“寫作就像學走路,我是跟著邁邁步子。”陳慧説。
擺攤的熱鬧和寫作的安靜在她身上形成一種互補和對照。去縣城進貨、等公交的空當,她從站臺對面的攤位上買兩本雜誌,囫圇讀一讀。平日裏打發時間,她喜歡拿起書看,沈從文、汪曾祺……他們筆下的故事生動質樸,跟自己的生活很像,她讀著覺得親切,“跟吃菜一樣”。在寫作上,她沒有宏大的選題和深刻的野心,筆下皆是身邊人。
“想寫的故事一直惦記著,在腦子裏播來播去。”結束擺攤,回到家,午休醒來,創作開始。屋外靜悄悄,只有遠處傳來幾聲土狗的吠叫。
有讀者在網上看到文章,誇她寫作有靈氣,“真實粗糲,結實又有活力”“有一股子韌勁兒”。架不住表揚,她馬上挽起袖子再接再厲往前寫。
在自己書的後記中,她寫下這樣的文字:“我從沒想過寫作有什麼用途,就是想讓自己安靜下來,覺得不那麼孤獨。專注碼字時,仿佛自己是《西遊記》裏的老妖,肺腑裏吐出的舍利球常常能熨平日子裏翹起的雞毛。”
“我有兩個窗口。一個讓我趴著,窺視近在咫尺的凡間;一個用來飄著,放縱靈魂四處徜徉。”
窗外,青山的脊背抬眼可望,窗戶打開,溪水聲就順著流進屋裏,流向下游的四明湖。陳慧長日坐在窗口,在溪水聲中分辨雨聲,伴著雨聲敲打鍵盤。近百篇故事從她的指尖誕生,她記錄下生命的無奈和莊嚴,卑微與貴重。
電腦就放在她床邊的窗戶下面,有時候寫累了,或者寫不下去的時候,她就向窗外看看。窗外有田野和小溪,小溪旁還有一個中風的女人。
陳慧經常看著她。她像一個擠不乾淨的拖把一樣拖著不能動的半邊身體在田裏幹活。
“我眺望她,像在眺望一個珍稀的同類。”陳慧説。
“寬闊的土地是她的退路,細碎的文字是我的救贖。”
收攤後,用文字
解決生活裏的不如意
幾天前,陳慧的腿上生了瘡,疼在骨頭上。不能走路和擺攤,她躺在家休息了十多天,難得地用起了社交賬號,在上面吆喝著賣自己的書。
“我的應變能力很強,但我不能不生活。靠寫文章不能生活,不擺攤沒有收入了我就得賣書。”她手上拿著剛收到的三張綠色稿費單,單子有些發皺,是當地報紙刊登她的文章後寄來的。
“可以多給兒子買一個西瓜。”陳慧説,“我不忌諱對錢的熱愛,這也是對生活的熱愛。我自己托不起的我也不惦記。”她覺得她的書就像她推車裏賣的商品一樣,都是努力生活的佐證,她賣力地吆喝,也得到別人的尊重。
已經出版的兩本書《渡你的人再久也會來》和《世間的小兒女》,余姚市政府的文學精品扶持項目替她負擔了出版費用,除去贈予親朋好友的,剩下的加起來賣了3萬多塊錢。
她始終認為,如果她是“順遂”的,可能當不了作家。既是身體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3歲被父母送人,在養父母家長大,又因為生病須終身服藥。職校畢業,做過裁縫,開過百貨店,26歲從蘇中平原的家鄉嫁到浙江,遭遇婚變,40歲離婚,獨自帶著孩子生活,“人生的牌都推掉了”。她用一句話概括自己:“坎坷人生,孤單如影隨形。”
摩托車經過村旁的四明湖,她常常停在湖邊站一會兒。
“普通人的生活渾身都是線頭,一拉都散了。”陳慧説。十幾年來,她一直騎著那輛鈴木摩托車進貨,車一開轟隆一聲,看上去瀟灑颯爽。
“一個女人看似堅強,但原本應該是柔軟的樣子啊。”她的話音之外似有遺憾,“如果能不當騎車的,而是去當坐車的該多幸福啊。”
因為無可依靠,所以看著灑脫,這種“堅強”,是硬扛著的。
一個天性柔軟的人,被生活“打鐵”打硬了。在菜市場裏風風火火,好像是在掩蓋生活中的委屈;她往返于家與菜市場,也往返于筆下的文字和辛勞的日子。
那段時間她更加依賴菜市場,那裏熱氣騰騰,可以找人説説話,收集生活的靈氣;收攤後,她就獨自關上房門寫作,用文字解決生活裏的不如意。這成為她和生活間一場秘而不宣的博弈。
孤單生活在這個小鎮的幾年,她過得激進又迷惘。有找她合作出書的、要當學生的、讓她開直播的……面對改變生活的可能性,她感到警惕和不安。“那些網紅,賺了大錢就回不到原來的世界了。心思浮了,沒法靜下心寫東西。”
生活的磨煉,鍛造出一個固執強硬、謹慎防備,卻又無比清醒的人。“我安安靜靜地過,心裏舒服。”“我只賺我能賺的錢,我選擇寧靜的生活。”在她看來,謹慎也是美德,她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堅定回歸到一種“生活主義”。
“他們低估了一個長期浸淫在孤寂中的中年婦女的定力。熱鬧是別人的,我只想舒舒服服地躺平了睡我的午覺。”
唯獨有件事是她接受的——兒子就讀的余姚市第三中學請她去講一堂寫作課,她樂意去。她覺得自己靠努力贏得了別人的尊重,能讓兒子看看不一樣的媽媽,給兒子當個榜樣,讓他更自信。“我是他腳下的石頭,墊著他往前走。”
主動從婚姻中出走,選擇一種清簡規律的生活……剝去冗雜的旁枝末節,她覺得現在的日子輕鬆又舒展。
異鄉生活17年
散漫寫作11年
前兩天,陳慧收到一台電腦,卻一直找不到寄出電腦的好心人。她想,或許做這件事的人壓根不打算接受她的謝意。
在異鄉生活17年,菜場擺攤15年,散漫地寫作11年。“誰也不能觸摸到我內心深處哪怕微小的一個噴嚏,然而,當這些我沒有預想過的善意如同雪夜的火種那樣輾轉到我的手上時,我才明白自己一直就深陷在戀戀紅塵中,從來沒有拔出過自己的雙腳。”陳慧寫道。
在情感上,她是一個保守派,願意承認自己的弱小。這個生活了十幾年的地方,她沒有把它當作“家”,只是暫住的地方。但她也無法回到自己的家鄉了。
從小在養父母家被悉心照顧,擁有“豐沛而散漫的童年”。那些最常出現在腦海的畫面是小小的她坐在青瓦平房的門檻上看書,大門右側有一排很大的水杉樹,到了夏天,大人們會在河邊淘米、洗菜、洗衣服,孩子們會下河游泳。農閒時,村裏的人背著包裹卷出門,農忙時他們又像候鳥一樣飛回來,鄰里間常常一起吃飯,互相幫忙。
那個“遙遠”的童年,依舊讓她感到幸福。
她認為“飯桌是生活裏最大的地方”,生活是所有東西的根本,是她的“主業”。“我只要能站著,肯定不會撿菜葉子吃,肯定要吃紅燒肉的。”
吃頓東西是最實在的。她在任何時候都對吃的東西懷著一捧歡天喜地的熱情。“如果沒有這點小家子氣的熱情,我都不知道我簡單的生活還有什麼樂趣。食物給人能量,讓我們活著;食物也傳遞情感,使我們溫暖。”人間煙火,有情有義。
陳慧説,生活幸福程度不取決於生活的境遇,而是生活的態度。“我不幸福,所以多做一些與幸福有關的事情,吃點好吃的東西,帶孩子看個電影,回家和媽媽吵吵架。我不幸福,但我還和生活對付著,人的心是不滿的,我看清生活後依然熱愛她。”
她開始學習二胡,以免日後身體不好了推不動推車,還可以拉二胡去菜市場“賣藝”討生活。這是她對生活的部署和退路。進入菜市場之後,她便不再有高貴低賤的判斷了。
她也不覺得寫作有什麼高貴的,“生活才是最高貴的,我們可以編排文字,但生活是在編排我們。”
“你有能力跟生活叫板嗎?生活才是最高級的,你沒有選擇。我不是戰士了,不去抗爭了,它給了我什麼我就順著、貼著,讓自己不那麼難受。生活不會哄你,你只能認清它,融入它。”
十幾年過去,“阿三擺攤的街上”人來人往,有的人來了又走了。她始終沒有搬進一個正式的店面,也沒有選擇利潤更高的生意。她依然推著推車在這條街邊賣小百貨。她感覺踏實,你給我錢我給你貨,一塊錢一塊錢握在手裏,就像她生活和為人的道理。
在家的幾年,她不種花,種蔥、薄荷、絲瓜,都是她平日最喜歡吃的。絲瓜苗裏見縫插針栽幾根蔥,拔起的瓜藤攀上了她的窗,開出幾朵金黃色的小花。
從飯桌,到小院,再到生活的邊界,陳慧過得越來越清晰。她不願被冠上“逃離”“覺醒”這樣的詞,覺得這些“太大了”,“做人還是老老實實的好”。
在真實的人間生活,如何能全都稱心如意?她説,生活是一個容器,她是水,跳進哪個瓶子就成為哪個形狀。
“我是坐著小船在河裏漂的人,漂到哪是哪。”陳慧説,“在路上遇到一朵小花,我就把它收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