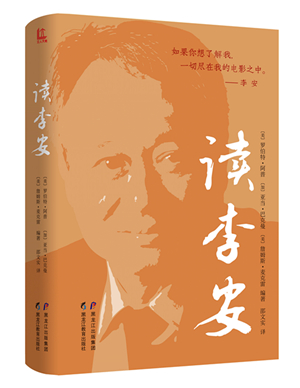
本文摘自《讀李安》 羅伯特·阿普(Robert Arp)、詹姆斯·麥克雷(James McRae)、亞當·巴克曼(Adam Barkman)編著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李安以多才多藝和無憂無懼的電影攝制者著稱,他不斷努力,借助由運動畫面構成的中介,探索復雜的哲學主題,從而開辟了新的疆域。他的電影之所以能夠引起觀眾的共鳴,不僅因為他身為導演的技巧,而且因為這些電影探討了對人類來說普遍重要的問題。正如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克里托》(Crito)篇中所雲:“未經檢驗的生活是不值得一提的生活。”電影是哲學的重要介質,因為它鮮活生動地向我們發起挑戰,使我們重新評估我們的生活基于其上的根本假設。李安電影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它們是藝術的傑作,還在于它們是進行哲學探尋的機會。
一、本真的自我修為
一幅題為《三酸圖》(The Three Vinegar Tasters)的著名中國畫描繪了中國三大哲學體係—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創始人在品嘗一缸醋。孔子和如來覺得這醋苦澀難當,難以下咽,而道家的老子則對這醋甘之如飴。盡管此圖的要旨是揭示這三種傳統對于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但它也被闡釋為道家對其他兩個體係的批評,尤其是對儒家思想的批評。孔子相信,人的本性是酸澀的,必須通過教育、規則和社會規范來加以糾正,而老子則認為,處于自然狀態的人是最好的。
李安的電影《臥虎藏龍》(2000年)探索了有關自我發展的儒家和道家哲學間的張力。 盡管這兩種傳統在許多方面都意見一致,但在社會于君子的修為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方面,則是各持己見。本章旨在探討這兩種傳統間的張力如何促成了電影中的衝突和角色發展。第一部分討論儒教和道教共有的、基本的形而上學思想。第二部分將電影中體現出的儒家和道家的自我修為概念加以比較和對比。最後一部分指出,源于社會局限的自由是本真的自我修為之根本,但它的代價是:每個角色都必須為獲得解放而作出犧牲。最終,《臥虎藏龍》昭示,本真的自我修為是一個人的天性自由與社會角色、關係和責任之間的平衡。
二、中國的形而上學:相互關聯的宇宙與焦點—場域自我
老子(生于約公元前604年)和孔子(前551—前479)是生活在周朝(前1122—前256)的同時代人。 兩位都是學者,都積極從政:老子是周朝宮室的守藏室之史,而孔子則在魯定公朝代有過簡短的任職經歷。 《史記》和《莊子》這兩部經典著作都聲稱,這兩位學者至少有過一次會面,會面時,孔子向老子請教了禮儀之事,並對老子的智慧讚賞有加。 因為《臥虎藏龍》的場景設置在清朝(1644—1911)1779年,所以這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已在文化上變得根深蒂固,這從電影人物身上一望而知。盡管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哲學的許多方面都各持己見,但它們的宇宙觀的確被所有中國哲學體係視為有當然的共通之處。
由儒家和道家思想構成的古代中國本體論從根本上而言是反宇宙論的:“它們根本沒有宇宙的概念,既然那一概念被限定為一個附加上任何意義或定義的連續一致、秩序單一的世界。” 西方哲學中的宇宙思維一直都問題重重,假設了無益的觀點:篤信一個井然有序的代理機構,對比現實與表象之間的差異,關注轉變過程的永久性,傾向于推導感知經驗。作為反宇宙論哲學,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自認為是井然有序的代理機構,也不承認現實與表象間的差異,聚焦于變化、轉變的過程以及有關純理性思維的感知經驗。 艾默斯和羅斯蒙德勾勒了西方關係概念與中國相互關聯概念間的區別。 西方認識論通常關注的是關係論,其中,一個獨立的自我會將其環境當作一個分離的實體來觀察。因為個體與環境相互分離,人們就必須擁有一套范疇,通過它來組織和闡釋經驗。在中國相互關係的概念中,認知者和被認知者之間從根本上說是相互關聯的,因為認知者是其環境的一部分。
兩個關鍵術語被用于定義自然環境:“天”和“道”。這兩個概念中沒有一個在儒家或道家哲學中得到清晰定義,因為這兩個傳統強調的是形而上的道德規范。 艾默斯和羅斯蒙德選擇將“天”翻譯為“自然界的內在秩序”,盡管許多學者也將它翻譯為“天國”或“天空”。 “天”通常被用作復合詞“天命”的一部分,而天命指的是“境況的傾向”,即事情的自然趨勢。“道”可以被翻譯為“道路”、“通道”或“途徑”,它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中意義略有不同。儒家將其解釋為自我修為的方法,如“悟道即體驗、闡釋和影響世界,其方式是強化並擴展來自于一個人的文化先輩的生活方式。” 在道家看來,“道”指的是自然之道:它是存在的、絕對而首要的原則—無差別的、整體的、完全的無限可能性。《道德經》的開篇語是:“道可道,非常道。”一旦我們開始理智地對事情加以歸類,我們便將它們抽離了其真實的、互相依存的本質。“天”和“道”合起來指的是“自然界的運動和模式”。 在道家和儒家思想中,凡使用“天”這一術語時,都是指自然界和處于自然秩序之內事物的相互關聯。儒家思想中,在使用“道”這一術語時,通常指的是一個人為了成為君子而必須遵循的修為方式。 在道家思想中,“道”不僅指這一過程,而且還指世界的自然秩序;“道”和“天”可以互換使用。 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道家思想中,只有當人使自身行為與自然界和諧相融時,他才可以真正成為一個有修為的人。這一道家觀點與儒家觀點並不衝突,相反,它通過將“天”與“道”這一概念的結合,擴展了儒家對于“天”的闡釋。盡管“天”與“道”的寓意略有不同,但這兩個術語在道家文獻中得到了交替使用。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對人的理解是:人會受到他或她的語境與處于那一語境中的人之間的焦點—場域關係的定義。霍爾和艾默斯描述了中國文化和哲學中的焦點—場域自我:
人們基本上是處于語境中的人,這種語境是他們在一個由特殊的社會、文化和自然條件所定義的世界中的固有語境。人們塑造他們居于其中的事情和事件之場域,又被這個場域所塑造 這種焦點和場域語言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論及人類和在儒家世界觀中得到預先假定的、“天”的連續性和相互依賴性的方法。“天”是場域,是社會、文化和自然語境,在某種意義上,要大于一個具體的人 同時又會被那個具體的人所牽連,帶入焦點之中。
“天”是所有事物都居于其中的語境,也是所有事物都必須以此為對照,來定義自身的背景。在古代中國,自我發展被理解為語境化的藝術—培養人與環境之關係的藝術。因為道家思想中的反宇宙論結構,所以不會有一個所有事物在其中都會得到分門別類的單一大語境。相反,世界由“無數事物”構成,層出不窮的特殊性可以從多種各不相同的視角加以理解。因此,既然世界是由“許多有關它們的場域的特殊焦點構成”,那麼“語境化藝術便會涉及無數 構成世界的 細節的和諧關聯之產物”。 這些“無數的細節”包括自然界和其他人(既是家庭的也是社會政治的關係)。通過使自我與其語境相協調,一個人可以為那種語境所塑造,並反過來致力于通過在那語境中的行為而塑造那一語境。
這種將統一性理解為焦點—場域關係之功能的做法在《道德經》第三十九章中最為明顯: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這段文字描述了一切事物被其語境(道)之焦點—場域關係所定義的方法。一切事物都必須在與“道”(自然界)的關係中理解自己,培養自己。每個事物—天、地、神、谷以及侯王—都只有在它理解與自身環境統一性的關係時,才可得到真正的發展。任何缺乏這種語境化理解的、自我修為的努力都會導致災難。因此,給世界帶來穩定和繁榮的,正是人與“道”的統一性關係。
電影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由他們與各自的關係以及與自然界的關係來定義的。碧眼狐狸(鄭佩佩飾)代表著非自然:她根據圖畫來學習武當功夫,卻不理解潛藏于其下的原則;她利用紫陰針使李慕白的血液和生命的能量逆天倒流,從而毒殺了他;她通過將玉嬌龍(章子怡飾)變成一個罪犯(一條毒龍)來腐蝕她的個性。相反,李慕白(周潤發飾)是自然之事的代表。他一再地與綠竹林(它是與自然相適應的象徵)相結為伴:他的劍名中有“青”字;在與玉嬌龍的第一次交鋒之中,他使用樹枝來阻擋玉嬌龍的刀鋒;他後來又在與玉嬌龍宏大壯麗的決鬥中利用了綠竹林。
三、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自我修為
在李慕白與玉嬌龍初次相遇時,他提供了一段有關武術真諦的教訓:自我修為。“勿助,勿長。不應,不辯。無制,無欲。舍己從人才能我順人背。教你一點做人處事的道理。” 玉嬌龍顯然有打鬥的技巧,但缺乏控制自己能力的特性。說到底,武術訓練最終在于修養人的個性,正是在這一點上,道家和儒家在對自我修為的態度上生成了一種張力。盡管儒家和道家同為一種宇宙學之基礎,但在自我修為方面追求的卻是不同的目標。儒家思想之所以可被歸為人文主義,正是因為它聚焦于人和社會,將之視為自我修為借以生成的中介:人的社群是價值的主要來源。道家思想是一種自然主義,其中,自我修為是在效法自然之道。
儒家思想中的自我修為
儒家思想認為,自我被動態地構建為它與環境和他人之關係的功能。除了社會影響,並不存在一個人必須加以實現的永恆的、根本的自我;相反,自我是靈活的,會不斷地變化,以迎合其環境的需求,從而在此環境中茁壯成長。 孔子不在意本體論上一個人是誰;相反,他感興趣的是一個人如何通過變化的世界不斷變遷來培養自我。在《論語》中,孔子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一個人的自我並非基于某種人必須實現的、永恆的、在本體上固定不變的存在,而是基于人在世界上恰如其分的生存活動。通過培養自我,使之達到最高水平,一個人會帶給他人在其中處于焦點的場域以豐富性。因此,通過培養自我,一個人可以弘道。每個人語境的一個重要方面都是處于那一語境中的他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在孔子看來,自我修為的達成必須與處于同一語境中的他人相互關聯。認識(“知”)自我是個“知人”的過程,正如理解可信之舉(“仁”)是個“愛人”的過程。
儒家自我修為的目標是變為“君子”,即堪為模范之人,這是大多數人都希望達成的最高目標。更高的目標是“聖人”,即聖賢之人,這樣的人是最偉大的君子,極其罕見。普通人是“士”,是邁向德行道路上的學者兼學徒,而腐化墮落之人為“小人”,是微不足道的人。 當俞秀蓮(楊紫瓊飾)和李慕白討論武當派在禁止訓練女人的情況下接受玉嬌龍為徒的可能性時,李慕白評論說:“為她 也許破個例吧。如果不成,這個姑娘 將來恐怕成為一條毒龍。”“毒龍”一詞指道德品性腐敗的武士(用孔子的話來說,即“小人”)。正如羅伯特 卡爾特(Robert Carter)所言,儒學本身即是個“總是向自我完善、自我轉變和成為聖賢之徒的教育成長開放的過程”。 因此,盡管玉嬌龍的個性一直以來遭到了她與碧眼狐狸關係的腐蝕,但仍有可能通過正確的教導,使她成為君子。李慕白和俞秀蓮都是君子(或幾近君子),但他們對彼此愛慕的壓抑使他們過著悲哀而遺憾的、非充實美滿的生活。總之,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變成“君子”,如果所有人都努力成為模范,則我們便有可能擁有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
一個人要成為君子,還必須培養幾種德行。首先—無疑也是最重要的—是“仁”。 “仁”指仁慈、仁善、富于道德的個性,或稱仁心(盡管艾默斯和羅斯蒙德更願意將之翻譯為“可信之舉”)。“仁”的漢字是由“人”和“二”兩個部分構成,這意味著,一個人單靠自己成不了一個有修養的人。據認為,這個字最初的寫法是“人”加“上”,表明“仁”指的是一個更高層面的人的特徵。它是使人成為完人的最終道德準則。一個善良的人擁有天生的道德感,這使之對他人的需求以及自身的角色和責任(“仁兼”)十分敏感。因此,“仁”反應了焦點—場域自我的相互關聯的本質。 在電影中,李慕白和俞秀蓮都是可信之舉的典范,這體現在他們對玉嬌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仁慈之舉中。李慕白力求她成為徒弟,盡管她與之格鬥,而且她曾是殺害了自己師傅的碧眼狐狸的徒弟。俞秀蓮同意與玉嬌龍結拜為姐妹,盡管玉嬌龍盜走了青冥劍,且在俞試圖阻止其盜劍時,與之進行了格鬥。
儒家思想的第二個關鍵德行是“義”,即“合宜”,它指的是引導善行的道德準則。這個字由“羊”和“我”兩個部分構成,指為了社群之利益而犧牲自我。 這些不是康德所指的無上的道德律令,而更像是羅莎琳德 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為德行倫理學所描述的品行法則:推動道德目標,並輔助解決道德困境的、普遍的道德準則。 一個人可以通過理解其語境來學習在其中富于建樹地生活。就此意義而言,“義”是一種現實智慧形式,這種智慧對于人的生活有著實際的金錢價值。這個行為引導概念反映在俞秀蓮對玉嬌龍所說的話中:“走江湖,靠的是人熟,講信,講義 不講信義,可就玩不長了。” 在電影中,玉嬌龍自始至終都在努力接受這個概念。在盜取了青冥劍後,她在茶亭和聚星樓向武士們發起了挑戰。這些行為既粗魯又輕率—完全違背了江湖道義。 她對此道義的漠視最終導致了李慕白之死。
儒家思想的第三個重要德行是“禮”,它指的是有利于人際互動的禮儀、典禮、風俗和禮節。 “禮”是體現和促進“仁”實現的日常實踐,包括宗教禮儀、社會風俗和一般的行為規矩。艾默斯和羅斯蒙德將“禮”形容為“那些具有意義的角色、關係和制度,它們可促進交流,培養社群感。” 這些不同于我們通過將其嵌入習慣而“自己制定出來的”意義上的法律。“禮”是包括了倫理(“義”)和禮節(“禮”)兩者的、連續統一體的組成部分:兩者對于促進社會和諧都是必不可少的。“禮”與第四個儒家德行“孝”密切相關。家庭構成了兒童的近身社會環境,對于人的道德修養至關重要。對自己最親近的人的尊重會以五種基本關係同心地向外輻射至其他群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孝”不僅指照顧像父母這樣的他者,而且是一種奉獻,幫助他們成為健康幸福之人。 “禮”和“孝”兩者的要求都顯見于《臥虎藏龍》之中。李慕白和俞秀蓮覺得他們不能表達對彼此的愛慕,因為他們害怕這樣做會給俞秀蓮的未婚夫孟思昭(他為了救李慕白而喪命)臉上抹黑。玉嬌龍與碧眼狐狸的關係因為這樣一個事實而變得混亂:後者既是玉嬌龍的仆人,又是她的師傅,而當玉嬌龍超過了碧眼狐狸且與李慕白結為師徒時,這種關係變得更加錯綜復雜。玉嬌龍和俞秀蓮同意結為姐妹,而玉嬌龍發現,自己很難服從俞秀蓮的權威。作為一個遵從儒教的女子,玉嬌龍本該接受一場政治聯姻,可她卻與羅小虎(張震飾演的半天雲)兩情相悅。總之,正是社會期望與人的自然欲望之間的張力為故事提供了衝突。
第五個基本的儒家德行是“信”,它可以指誠實、誠信、忠誠或正直。就字面而言,這個字指的是一個說話的人,而這意味著一個言而有信的人。 誠實不僅涉及外在行為與內在活動間的對應性(對他人誠實), 而且也涉及內在的一致性(對自己誠實)。這與“正名”(修正名稱)這一概念密切相關:一個人必須理解定義一種角色的標準,隨後傾其一生,全力實現它。 武術不僅涉及對打鬥技巧的掌握,而且涉及品行道德的培養:一個只擁有其中一方面的人不能真正被稱為習武之人。在電影中,李慕白和俞秀蓮都為包括誠實和正直在內的江湖道義所約束。這正是他們覺得無法親近彼此的原因:這樣做會違背他們對孟思昭的誓言,而後者是李慕白的摯友,又是俞秀蓮的未婚夫。
【書籍信息】
[作者簡介]
羅伯特 阿普(Robert Arp),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哲學博士,多倫多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
亞當 巴克曼(Adam Barkman),加拿大耶穌基督學院哲學副教授,韓國延世大學哲學教授
詹姆斯 麥克雷(James McRae),威斯敏斯特學院亞洲哲學及宗教副教授,亞洲研究課程協調人。
[內容簡介]
《讀李安》運用東西方兩種不同哲學傳統評析李安導演的作品。圖書第一部分聚焦李安的華語影片中所蘊含的中國傳統道、儒及佛學哲學主題,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其導演的英語影片中所體現的西方哲思想主題:然而,全書的終極目標在于探索李安糅合這兩種文化、架構中西文化溝通橋梁(即為表現電影主旨內容,策略性的汲取中西文化思想)的電影導演哲學。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