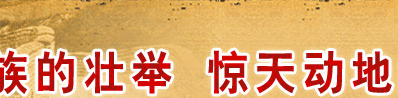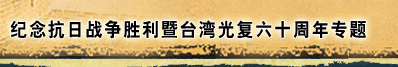“臺灣三部曲”作者閻延文
臺灣同胞的抗日鬥爭前前後後持續了五十年,比起祖國大陸來,時間更長。五十年間,臺胞犧牲了約五十萬人,連同其他時期共約六十萬人,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毫無疑問,臺灣同胞的抗日鬥爭是整個中華民族抗日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同胞為全面抗戰的勝利作出的貢獻不可磨滅,青史可鑒。
大陸女作家閻延文以“臺灣三部曲”再現了那段可歌可泣的臺灣同胞抗日曆史,“三部曲”也是第一部正面描寫臺灣抗日的長篇小説。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臺灣光復60週年之際,本網記者對閻延文進行了獨家專訪。
記者:現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的文藝作品非常豐富,你的“臺灣三部曲”系列的《臺灣風雲》和《青史青山》,是第一次正面描寫臺灣抗日的長篇小説,引起世界華人華僑的強烈反響。這幾天我細讀了評價你的作品《臺灣風雲》和《滄海神話》的有關資料,內心受到震動。您能介紹一下情況嗎?
閻延文:《臺灣風雲》、《滄海神話》和《青史青山》是三部系列長篇歷史小説,總計140萬字。第一部《臺灣風雲》抒寫1895年中日簽定《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日本,臺灣人民“願人人戰死而割臺,決不拱手而讓臺”的悲壯畫卷;《滄海神話》以“百年孤獨”式的結構,描寫了臺灣先民三百年間拓荒傳奇的祖先神話,復現一個家族九代人對家國信仰的皈依;第三部《青史青山》寫1895年到1945年日據50年間,一批堅守文化抗爭的臺灣知識分子,特別是愛國詩人《臺灣通史》作者連橫,在日本文化殖民環境下一生都在英勇抗爭,以個人的力量,做艱難的文化突圍。我希望,用筆鋒完成從拓荒、興臺、割臺、保臺到光復的“臺灣三部曲”,書寫民族的百年滄桑。
1995年,我走進“臺灣三部曲”的創作。《臺灣風雲》和《滄海神話》分別於2001年和2004年出版,《青史青山》準備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出版。《臺灣風雲》和《滄海神話》出版後,引起海內外的關注,這是我始料未及的。2001年,長篇小説《臺灣風雲》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2004年9月,入選中宣部、團中央等七部門推介的三個一百“百部愛國主義圖書”;2003年4月,長篇小説《臺灣風雲》在臺灣出版了中文繁體版。那時正值非典恣肆,小説在臺灣仍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發行業績,被臺灣出版界稱為“二月河之後最好看的歷史小説”,令我十分感動。2003年7月6號,全美中國作聯、強磊出版社和美國“中國作家之家”等五家機構在美國康州麥迪遜聯合召開新書發佈會,向美國漢學界、新聞媒體和讀者推介我的“臺灣三部曲”。新華社聯合國分社和中國新聞社美國分社向全球發佈了電訊稿,美國《僑報》、《星島日報》、《芝加哥華語論壇報》、《新象週刊》、《華聲報》等相繼在顯要位置刊登報道。《滄海神話》出版後,2004年12月,全美中國作聯再次召開新書發佈會,向美國漢學界、新聞媒體和讀者推介《滄海神話》。更令我興奮的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趙浩生教授等,對《臺灣風雲》和《滄海神話》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和期待。
記者:《臺灣風雲》引起許多中國人,尤其你的同齡人的強烈共鳴。有人“幾度掩卷,拍案長嘆,無法卒讀”,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引起了這麼多中國人的共鳴?
閻延文:我認為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成功,而是中華民族對臺灣抗日這段痛史的追憶,對丘逢甲、徐驤等一代抗日民族英雄的敬仰和懷念,是對維護世界和平、期待兩岸統一的熱切呼喚。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各路人馬“水陸交綏,戰無一勝”。1895年4月,中日在日本廣島簽定《馬關條約》:將臺灣全島、澎湖列島和所有附屬島嶼“及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消息傳來,全臺震駭。臺灣人民先是“椎心泣血,北向痛哭”,千方百計阻止清政府割臺棄臺;繼而“奮空拳、拼殘軀”,以自己的血肉之軀與6萬日本正規軍相搏擊,捍衛祖國寶島。在這場波瀾壯闊的歷史壯劇中,400萬台灣人民以自己的赤子之心,傾訴對祖國的衷情,引發了震驚中外的公車上書,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近代化覺醒。中國近代的兩大政黨??資産階級改良派和資産階級革命派,都在甲午戰後臺灣人民浴血保臺的漫天硝煙中登上了歷史舞臺。中華民族的自救運動從此開始了。《臺灣風雲》傾力描寫的就是這段歷史。
以往,我們更多地關注甲午戰爭的大陸戰場,對臺灣抗日戰場表現較少。其實,臺灣抗日是一段真正的血火壯史,從1895年6月至10月,在4個半月的保臺抗戰中,臺灣軍民激戰大小一百多仗,抗擊了日本三個近代化師團和一支海軍艦隊,打死打傷日軍三萬兩千多人。這個數字是甲午戰爭大陸戰場日軍傷亡總數的兩倍,佔日本當時全國總兵力的四分之一。日本皇室代表、北白川能久中將,陸軍少將山根信成等高級將領紛紛拋屍臺灣。而他們的對手,竟然是只有大刀、土槍,沒有糧餉,也沒有預備隊的普通臺灣百姓。這無疑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因此,侵臺日軍在戰報中也不得不嘆息:“在臺北到新竹間,人民就是士兵,其數目不得而知。他們破壞鐵路,割斷電線。無論何時,只要我軍一齣現,附近村民就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一點也不怕死……”這是1895年的臺灣,距大陸全面抗日還有42年,距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還有36年。臺灣人民是最早承受戰爭苦難的人群,也是最早抗擊日本侵略的中國人。臺灣抗日與大陸抗日一脈相承,最充分表現了中國人的血氣和骨骼。我個人認為,中華民族的抗日不是傳統意義的八年,甚至也不只是九一八事變後的十四年,而是從1895年臺灣抗日肇始的五十年。
傾力雕塑隱身在歷史深處的臺灣抗日英雄
記者:關於“三部曲”第一部《臺灣風雲》,主人公丘逢甲這個人物如何打動了你?你對他有何評價?通過對他的刻畫,你最想表達怎樣的情感?
閻延文:以往對臺灣這段歷史,往往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進行關照的。用文藝作品來展現臺灣三百年史,尤其是1895年以來的五十年臺灣抗日史,“臺灣三部曲”還是第一次。我面臨的困難,是如何將一段今天大陸讀者並不熟悉的歷史,用長篇小説的藝術形式加以生動復現,把隱身在歷史烽煙中的臺灣抗日英雄們,雕塑成青銅般的藝術形象。這是極大的挑戰,更是作家的責任。
在創作《臺灣風雲》時,難度首先來自主人公的選擇。這樣一部全景式、多視角、時間跨度長達60年的長篇小説,誰作為主人公才最能體現歷史的風雲壯闊?經過反覆構思,我的筆最終定位到主人公丘逢甲的身上。與一般藝術作品不同的是,丘逢甲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在爬梳《臺灣通史》、《臺灣詩乘》、《嶺雲海日樓詩鈔》、《先兄倉海行狀》等歷史資料後,丘逢甲的形象逐漸清晰起來。他是天才詩人,又在國難當頭時以文弱之軀挺身而出,擔任臺灣義軍總頭領。這是歷史的真實記錄。但他作為文藝作品中的人物,作為生命璀璨的詩人,其藝術形象還遠遠不夠。這就需要大膽虛構和藝術想像。我在《臺灣風雲》中對主人公丘逢甲是這樣塑造的:他幼年聰明早慧,13歲科場奪魁,一鳴驚人。10年後,逢甲已是才華冠世,心高氣傲的青年,世稱“東寧才子”。在官場與人生的苦旅中,他經歷了一系列坎坷磨難。故事情節圍繞著主人公從科場、官場、詩場到血火戰場的傳奇經歷,漸漸展開……我在創作中力圖既保有傳統文化,又包涵強烈的現代氣息和人文關懷,強調主人公對他人的關愛和理解。比如丘逢甲對愛情的選擇,是以一生的情感痛苦為代價,惟其如此,他才是百年前充滿中國文化氣息的英雄。
作為主人公,丘逢甲最打動我的部分,是他身上粲然閃爍的中國文化品格。他不僅是上個世紀的傑出詩人,也是中國文化最富有光彩的因子。他體現的道德理想和國家情懷,正是我們這些70、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最需要注入的血液。丘逢甲的文化人格,也就是作為中華赤子的臺灣人性格。這是一種昂揚入世的儒家文化人格和樂觀開朗的海洋性文化情調的融合,既富有浪漫詩情,又堅韌剛烈,體現著對大陸祖國強烈的歸屬感和依戀感。日據五十年中,日本統治者使盡一切手段淡化這種民族文化精神,用血腥屠殺和同時進行的“皇民化”運動雙重策略,妄圖扼殺中華民族情結在臺灣的延續。然而,中國人固有的文化人格從來沒有被征服過。
由於在《詩刊》工作,常年和詩人及詩歌讀者打交道,我對詩有一種職業性的敏感和喜愛。主人公丘逢甲是我非常崇拜的詩人。作為近代傑出的天才詩人,丘逢甲曾與黃遵憲合稱“晚清詩界革命二巨子”,並預言二十世紀“必有合刻丘黃合稿者”。柳亞子先生甚至認為,丘逢甲的成就更在黃遵憲之上??“時人競説黃公度,英氣終輸滄海君”(丘逢甲晚年號滄海君)。而丘逢甲最光彩的詩篇,則是表現臺灣對祖國的皈依。“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丘逢甲的別臺詩,幾乎是四百萬台灣人發自心底的吶喊;而他的“大九州歸大一統”的夙願,也最恰切地表達了《臺灣風雲》的主題。我在小説中對他的詩歌著墨相當多,先後寫入了幾十首詩歌對聯。丘逢甲的詩是從胸腔中嘔出、從血淚中流出,凝聚了詩人的高蹈情懷和博大胸襟。通過這些閃爍著勵志、哲理光芒的詩篇及其貫穿起來的故事,可以看出詩人一生幾乎被塵埋的宏大抱負和壯麗事功。在寫作中,我力圖不把丘逢甲僅僅寫成風雲時代的歷史人物,而是作為富有高貴情懷的詩人,作為民族文化的精髓來解讀;甚至他的弱點和局限,也是富含詩性的樂章,包孕著活生生的血性與呼吸。
記者:在完成《臺灣風雲》和《滄海神話》後,你為什麼還要寫《青史青山》。臺灣抗日五十年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你是如何表現的?
閻延文:從1895年到1945年,臺灣日據五十年,也是臺灣抗日五十年。從創作上,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選擇了《戰爭風雲》式的寫法,用一個真實歷史人物,貫穿臺灣這段時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北埔起義、羅福星革命事件、西來庵起義、霧社起義、文化抗戰等。這個貫穿人物就是《臺灣通史》作者、著名詩人連橫。作為《青史青山》的主要人物,他是進行文化抗爭的傑出代表。臺灣割讓後,為了抗日保臺,連家曾把老宅讓出一半,作為抗日名將劉永福指揮黑旗軍的臨時大帥府。臺灣陷落後,連橫的父親連永昌悲憤交加,不幸與世長辭。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馬太得知後,強令警備署徵用連家老宅,作為臺南地方法院。面對國破家亡、喪父毀家的傷痛,連橫作為一介文弱書生只能以筆為劍,傳播漢文化,記錄臺灣的痛史成了他不懈的追求。經歷千辛萬苦,連橫終於寫成了《臺灣通史》。亂世痛史,以史為鑒。《臺灣通史》第一次用歷史定位了臺灣的中國歸屬。在《臺灣通史》中,連橫秉筆直書,為抗日英雄劉永福、丘逢甲、徐驤、姜紹祖、吳湯興立傳,並倡言“夫史者,民族之精神……國可滅,而史不可滅。”
我在小説中,力圖全景式描寫臺灣五十年間的重大抗日事件。1895?1915年,遍及全島的抗日武裝鬥爭,從簡大獅、柯鐵、林少貓到羅福星、江定、余清芳領導的抗日武裝,風起雲湧;1915年以後,武力抗日轉化為文化抗日,臺灣民族資産階級和知識分子,領導臺灣人民進行了堅決的文化抵抗,林獻堂、蔣渭水等,是名震全臺的文化抗戰指導者。在臺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的鬥爭中,心繫祖國是臺灣民眾內心中最深厚的情感,回歸祖國是他們的共同心願。簡大獅泣血悲訴:“我簡大獅,係臺灣清國之民……聚眾萬餘,血戰百次,生為大清之人,死為大清之鬼。”柯鐵在大坪頂上豎起的旗幟上書寫著“奉清徵倭”;余清芳發表《反日檄文》,指出“倭賊倡狂,侵犯臺疆。”號召愛國同胞:“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臺灣”。以連橫為主人公的臺灣文化人,更以畢生心血宣揚中華文化,抵制日本同化政策,加強與祖國的聯繫,期待祖國能早日收復臺灣。
日本對中國人民的血腥鎮壓,也是從臺灣開始的;或者説,日本在大陸的血腥政策,只是他們在臺灣鐵血政策的延續與翻版。例如,在余清芳、江定領導的噍吧年起義失敗後,日本軍將臺灣噍吧年一帶的竹圍、番仔厝、內莊子、左鎮等20多個村莊包圍,進行血腥慘殺,死亡人數超過30000人,造成噍吧年一帶三十年無男丁的血案。著名的泰雅人霧社起義後,日本殘酷滅絕了起義的馬荷坡社,將15歲以上的倖存者全部殺害。日本的血腥政策只激起了臺灣人民更大的反抗,在日本侵略臺灣的50年間,臺灣共發生了大小一百多次起義,為抗日犧牲的人數多達65萬人。日本在據臺之初,曾向世界宣佈三個月平定臺灣;但臺灣在日據的50年中,從來沒有被平定過。我的作品中寫了這樣一段對話,北白川對乃木希典説:“在臺民心中,中國是他們的祖國,這一點無可質疑。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文化、一條血脈,一部無法更改的歷史,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怕呢?”
1895年10月27日,侵臺日軍統帥北白川能久親王在臺南被臺灣義軍擊斃。日本當局規定每年10月27日為“臺灣神社祭”,紀念這位侵臺日軍罪魁。也許是歷史的巧合,35年後,1930年10月27日,臺灣高山族同胞正是利用北白川“神社祭”,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霧社起義。《青史青山》對霧社起義進行了大篇幅的描寫,將主要領袖莫那魯道作為主人公之一。在一個月的激戰中,日本當局動用了飛機大炮,更慘無人道的是,日本人使用了糜爛性炮彈、毒瓦斯和氰酸催淚彈。死亡人數上千人,不少婦女為了使正在激戰的丈夫無後顧之憂,含淚自殺。霧社起義領袖莫那魯道,為了不被俘虜,走進原始森林,再也沒有回來。他的頭顱後來被日本人運到臺北帝國大學製成標本,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才得以安葬。我在小説中最想表達的是,霧社起義的選擇,就是中國的文化人格。
我的“臺灣三部曲”結束于臺灣光復,1945年《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臺灣終於回歸中國。
臺灣抗日,不該被歷史遺忘的一頁
記者:你在創作中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閻延文:臺灣抗日英雄簡大獅罹難後,當時人創作了一首詩:“痛絕英雄灑淚時,海潮山涌泣蛟螭。他年國史題忠義,莫忘臺灣簡大獅。”也許,一百年前的這位詩人已經感覺到歷史的蒼茫,因此用了“莫忘”二字,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遠隔海峽的臺灣抗日英雄們。1995年進入臺灣題材創作後,我覺得臺灣抗日的歷史,今天了解還是太少,甚至有些模糊了。許多塵封在歷史深處的英雄,今人已經淡忘了他們的輝煌。比如東方會議形成的《田中奏折》,是日本侵華的重要證據,今天已經成為抗戰史料的重要部分。但鮮為人知的是,最初將《田中奏折》揭露於世界的,正是臺灣愛國者。1927年4月,日本田中義一組閣,他是強硬的大陸主義者,一貫主張侵略中國。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內閣召開“東方會議”,田中提出了明確的侵華方針《對華政策綱領》。在日本侵華史上,東方會議是一次決定“國策”的重要會議,勾畫出田中內閣企圖攫取“滿蒙”和武力侵華的“積極政策”的基本輪廓,成為後來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的理論根據。7月25日,田中義一向日本天皇又呈奏了一份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極其露骨地提出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總戰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揭露《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計劃的,就是臺灣義士蔡智堪。他是臺灣移居日本的華僑,出身富豪之家。為了揭露戰爭陰謀維護和平,他冒著生命危險,化裝潛入日本皇宮圖書館,長達四十多天,手寫抄錄了《田中奏折》全本,于1929年12月由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英、美、蘇等國報紙也相繼予以披露。日本當權人物矢口否認《田中奏折》的存在,然而事實證明,《田中奏折》勾畫了日本的“大陸擴張政策”,以後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發展,正是按照這一軌道運作的。
這段歷史,使我激動不已,決定在《青史青山》中第一次用文學藝術,再現蔡智堪這個代表中國文化人格的無名英雄。蔡智堪作為小説的重要人物之一,我用了幾章的篇幅描寫他的坎坷命運,他豐富的內心世界和最終的毅然抉擇。蔡智堪被日本警察逮捕後,深情地説:“我這樣做,有十分是愛中國,也有一分愛日本。”因為戰爭發動,將是兩國的災難。這句話表達了他用生命和財富換取和平的偉大情懷。正是這樣的無名英雄,構成了臺灣抗日的真實歷史。青山不滅,青史不滅,作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女作家,我只是用筆走進了歷史,鮮活了他們的生命和夢想。
十年青春,打造“臺灣三部曲”
記者:我知道,“臺灣三部曲”這史詩巨著您從1995年就開始創作,至今整整10年了,您的創作初衷是什麼?我還注意到當時您只有23歲,以您當時的年齡是怎樣去把握這樣一個深重的題材呢?我看到李準先生曾説,您的小説創作是與歷史研究同步的,填補了創作題材上的重大空白。聯繫到你曾是中國最年輕的文學博士,我想這能否説是作家學者化的一種體現?
閻延文:我想自己還算不上學者作家,就算個博士作家吧。我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受了八年的專業訓練。在搞創作之前,一直從事理論研究,曾發表過近百篇的理論評論文章。1995年,我正在準備博士論文,一個偶然的機會承接了《中國三十年代文學史》臺港部分的寫作,開始了臺灣文化史的研究。逐漸,一種興奮感籠罩了我。海峽兩岸驚人的文化同構性,似乎預示著某種歷史的奇跡。出於心靈的召喚,我開始回溯歷史,爬梳有關臺灣歷史的縣誌、奏折、家書甚至日方資料,一步步走近那些叱吒風雲的時代與人物。我當時只有23歲,以這樣的年齡,承擔如此沉重的創作主題,的確感到太沉重了。然而,強烈的創作衝動,使我欲罷不能。近代臺灣史,展示了最強烈的民族歸屬感。正是這種民族靈魂的激勵,使我開始了漫長的創作歷程。在一個輕鬆娛樂的時代,這無疑是痛苦已極的選擇。土地、家園、民族……當我沉浸這種椎心刺骨的歷史沉思時,生命便進入了另一個時空。10年漫長的創作過程,其艱辛一言難盡。歷史進入了一種廣漠的開闊地帶,使我感到震驚。漫無涯際的態勢,汪洋恣肆的激情,艱苦倍嘗的摸索困擾……我不斷經歷著精神的淬礪,也不斷承受著意外的驚喜。為了這部作品,我已經習慣於放棄休息、放棄娛樂、放棄了許多機遇和屬於年輕人的快樂。可以説,自己是在用青春年華構築著《臺灣三部曲》。
記者:通過以上幾個問題的交談,真的使我感到:您在創作中充滿激情和感情,好像不是一般文學題材能表現的。請您提供一些在您創作或小説發行過程中讓您感動或印象深刻的事例或細節。
閻延文:《臺灣風雲》、《滄海神話》的出版和《青史青山》的創作,得益於許多文化前輩、友人和新聞界朋友的無私幫助和鼓勵。《臺灣風雲》兩位序言作者翟泰豐先生和李準先生,都是文化界的前輩名宿,卻在酷暑中揮汗成文,用精緻的書法小楷為本書作序,令我倍受感動。
《臺灣風雲》出版後,主人公丘逢甲的後代兩岸聚會,舉行了隆重的家族紀念儀式;主要人物“公車上書”第一人、臺灣進士汪春源的四世孫、福建省副省長汪毅夫先生還到北京找到我,熱情地表示感謝。他説,福州廈門兩處的《臺灣風雲》幾乎被蒐購一空,汪氏家族的後代差不多人手一冊。最令我感動的是,臺灣霧峰林家傳人、八十四歲的林雙憶女士看到《臺灣風雲》的相關報道後,專程從臺灣趕來,拿出日據時期的珍貴資料,向我講述了另一段塵封的悲壯歷史。記得當時,滾熱的淚水浸潤了我的眼眶。我感到一種信任,一種職責,一種從未有過的沉重感。這是我在創作之初沒有想到,也不敢想像的。很快,我再次沉入寫作狀態,開始創作《滄海神話》的姊妹篇、36集電視劇《滄海百年》的創作。2004年10月,《滄海百年》電視連續劇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段播出。
應該説,“臺灣三部曲”孕育於民族文化的脈搏。這種文化的血脈,與民族本身一樣源遠流長,生生不息;這種文化象徵,既有悲劇的美感,也有堅硬的骨骼。它不是什麼神話敘事,而是在大地上生長的民族精神本身。我感到,自己的作品仿佛蔥蘢大樹上一株鮮綠的葉片,不斷吸取著大地的營養,通過光合作用遍佈全身,催生出精神的蓓蕾。還有許許多多感人至深的細節,已無法一一列舉了。幾年來,在創作“臺灣三部曲”的過程中,淚水曾一次次濕潤了我的眼眶。這些令我感動、更令我難忘的經歷,已經不僅僅影響我的創作,更成為一種寶貴的生命體驗。它們時時提醒我,要對文學保持神聖的誠摯之情,用心靈恒久的寧靜,實現心中的文學夢想:要用自己的青春年華,傾心打造“臺灣三部曲”,把她寫成一部無愧於時代與民族的作品。
走進臺灣歷史的艱辛與遺憾
記者:你用十年時間創作“臺灣三部曲”,什麼在激勵你堅持下來?
閻延文:從1995年開始,“臺灣三部曲”的創作已持續10年,這種創作孤獨艱辛,很多壓力是女作家難以承擔的。首先是資料的短缺,其次是創作領域的獨到,我沒有得到過任何創作資助,沒有進入過任何創作扶持計劃。雖然處在北京文化中心,我卻仿佛行走在文學的邊疆。這種孤立無援的狀態,需要內心的力量。
在最艱難的時候,我總是想一想他們,想想那些在臺灣抗日中死去或依然活著,經歷了血火歷史,卻默默無名的人們;想想那些塵封在歷史深處的民族精魂,那些最應該被文學描寫,而一直沒有得到描寫的英雄。通過我的筆,通過長篇小説和電視劇本,他們變得鮮活而生動起來。我的艱難寫作,成為他們走出歷史的一扇窗口。這是我最大的動力。想想他們,自己的艱難又算什麼呢?
正像連橫先生在詩中所言:“青山青史未能忘”。臺灣抗日曆史的藝術復現,強烈地震撼了今天的中國人。一個在加拿大訪學的自然科學教授偶然看到《臺灣風雲》,淩晨五點發來電子郵件。他説:“我們民族太需要這樣的聲音了,沒有精神信仰的國度將會在新世紀被開除出地球村。”一位臺灣詩人聽説我創作了這本書,淚水浸潤了眼眶,連説:“謝謝你為臺灣寫了這本書。這段歷史是臺灣的痛史,臺灣人不敢寫,日本人不願寫,大陸人再不寫,誰來記錄歷史?”全美中國作聯主席冰淩先生,在海外看到《臺灣風雲》繁體字版後,激動地表示:“這是一部彰顯民族文化和民族自豪的作品。”就是這些海內外的知音們,這些和我一樣被歷史感動的人們,使我忍受了無法忍受的困難,堅持了下來。
在一篇創作手記中,我曾經寫過:“我的筆所以堅硬,因為我身後站著一個山脈般不屈的民族。”對華夏民族而言,個人與國家不是單純的從屬關係,而是母子般飽含養育深情和血緣色彩的生命歸宿。漫漫五十年的臺灣抗日史,展示了最強烈的民族歸屬感。當中華民族遭受劫難時,她的子民們卻沒有一個願意分離出去,而是倔強地擔當起拯救的責任,自願地拋卻家園、財産、愛情甚至生命,直面血淋淋的殺戮和殘酷的命運。因為他們身上有一根無法掙脫的血緣紐帶,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所賦予他們的民族靈魂。
記者:十年磨一劍,現在“臺灣三部曲”第三部《青史青山》即將出版,您用十年青春書寫臺灣歷史的計劃已經基本實現。今天,您還有什麼遺憾?
閻延文:在紀念抗日戰爭六十週年之際,反映臺灣抗日的影視作品《臺灣風雲》未能拍攝,這是我今天最大的遺憾。《臺灣風雲》2000年底出版後,在一個月內即有七家最有實力的中央和省級電視臺及影視製作單位希望投拍。我接受了中國作協黨組金炳華書記的推薦,將《臺灣風雲》電視劇投拍權售給了國臺辦下屬的九洲音像出版公司。2001年2月27日,我和九洲音像簽署了有效期兩年的《臺灣風雲》電視連續劇投拍合同。因為這是一部具有時效性的作品,在合同中還特意簽定了,如果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兩年不投拍,作者有權自行將投拍權轉售第三方。可是時至今日,4年已經過去了,《臺灣風雲》的拍攝還杳無音訊。
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一部部相關題材的影視片被搬上銀屏。近日,我不斷接到海內外新聞界朋友、讀者和同行們打來的電話,紛紛詢問電視連續劇《臺灣風雲》的拍攝情況。當得知杳無音訊時,無不遺憾,甚至感到憤慨。從2001年2月27日,我一直期待著,等了整整4年。我內心中何止是遺憾,而是錐心刺骨的傷痛……我似乎聽到了臺灣抗日英靈悲天泣血的嘆息聲,聽到了沉埋大海的青山青史掀起狂濤。在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的日子裏,卻沒有一部反映臺灣人民抗日的影視作品,這不能不説是空缺和遺憾。《臺灣風雲》擱置四年之久未能開拍,這是我今天最大的遺憾。2005年也就是今年,是臺灣人民抗日反割臺110週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六十週年。一部臺灣抗日作品被擱置整整四年,我們的影視人又如何告慰海峽兩岸的抗日英靈呢?
【閻延文簡介】
閻延文,女,青年作家,文學博士、副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茅盾文學研究會會員、北京市雜文學會會員;現為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編輯部副主任。1997年25歲獲文學博士學位,時為全國最年輕的文學博士。
歷時十年創作“臺灣三部曲”:《臺灣風雲》、《滄海神話》、《青史青山》,抒寫臺灣三百年滄桑。歷時兩年四易其稿,創作36集電視連續劇《滄海百年》,該劇于2004年10月,在中央電視臺一頻道黃金時段播出。自90年代中期開始影視創作,曾創作《臺灣風雲》25集電視文學劇本和《臺灣風雲》電影文學劇本。《臺灣風雲》2001年獲第八屆中宣部 “五個一”工程獎、2004年9月入選中宣部、國家廣電總局、文化部等七部委向社會聯合推薦愛國主義教育“三個一百”“百種愛國主義教育圖書”。2004年6月《滄海神話》已出版。 2003年4月《臺灣風雲》繁體字版在臺灣出版,再次獲得轟動,被臺灣出版界稱為“二月河之後最好看的歷史小説”。《臺灣風雲》和《滄海神話》引起國際漢學界熱烈關注,2003年7月6日和2004年12月5日,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等多家機構,先後兩次在美國聯合召開新聞發佈會,向美國漢學界、新聞媒體和讀者隆重推介“臺灣三部曲”;新聞發佈會上,同時播放了兩集《滄海百年》。美國《僑報》、《澳門日報》、香港《明報》、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香港鳳凰衛視等海內外80余家報刊、電視臺、電臺及數百家網站進行連續報道。(人民網記者 吳亞明)
長篇小説“臺灣三部曲”之二《滄海神話》出版
詩人拔劍唱大風---評閻延文《臺灣風雲》
(責任編輯: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