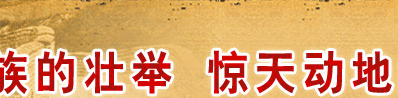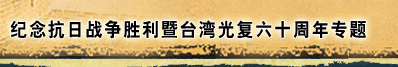新華網北京9月8日電(記者周婷玉)1937年7月25日清晨,一個人悄然披衣起床,走進書齋為妻兒寫好留言後離去。走上大道,他一步一回首地望著妻兒們所睡的家,眼淚忍不住地往外涌。
漂泊了十年的郭沫若終於“別婦拋雛”從日本回國。“七七事變”的槍聲,在他心中留下劇痛,同時也向他發出了回國的命令。冒著生命危險,他毅然踏上了歸途。
“其實他內心一直都想著回國。‘愛國’是貫穿他一生的主線,無論是創作還是其他活動。”郭沫若紀念館副館長蔡震説。
郭沫若一來到上海,就以筆當槍,投身於祖國抗日救亡的熱潮中。他對飛揚跋扈的日本軍人恨之入骨,視其為一群瘋狗。在飛機大炮轟擊中的上海,郭沫若寫下《我們為什麼抗戰》一文,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戰士,請你們一致起來和我們攜手,為世界的文化而戰,為全人類的福祉而戰,殲滅這東方的一大群瘋狗!”
一兩篇文章還不足以表達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1937年8月24日,郭沫若和夏衍、阿英在上海創辦《救亡日報》,發表大量的戰地採訪、新聞特寫,報道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跡。其間,郭沫若一連寫下了《前奏曲》《抗戰頌》《戰爭》等一批鼓舞氣勢的詩篇。是年底上海淪陷,《救亡日報》首先被迫停刊,那些以販賣抗戰書報盛極一時的小書攤也頓時改變了模樣。
1938年1月,郭沫若輾轉至武漢。“這年他經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蔡震説,“抗戰期間的經歷奠定了他後期的生活。”這件事就是組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郭沫若幾經周恩來的勸説擔任廳長。
1938年4月1日第三廳成立,郭沫若便請來了陽翰笙、傅抱石、田漢、胡愈之等一大批文藝界知名人士。“第三廳其實就是國共合作在組織上的表現形式,其職責是抗日救亡文化宣傳。”蔡震認為,郭沫若是“文化統一戰線上的領軍式人物。”他的經歷和在文化界的影響,使他成為國共公認的廳長人選。正如陽翰笙當年緬懷郭沫若時所説:“郭老不僅是革命文藝旗手……而且他首先是一位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的革命家。”
第三廳成立一週後即在武漢舉行“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每天用一種文藝形式進行抗戰宣傳,歌舞、音樂、美術、電影、戲劇……一系列活動讓軍民抗日熱情空前高漲,郭沫若也忙得不可開交。
在“七七事變”一週年時,郭沫若和周恩來商議後,第三廳又組織了“獻金運動”。《抗戰時期的郭沫若》一書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活動剛開始,摩肩接踵前來獻金的人就把設在三鎮的6座獻金臺圍得水泄不通,以致負責登記的工作人員由48人增加到約200人。最後總計獻金達100萬元。用這筆錢購買的軍需物資,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線。
第三廳的抗日宣傳活動震撼全國,抗戰期間郭沫若的文化成果也耀人眼目,除了《戰聲集》之外,還寫了200多首以抗日爭民主為主題的新舊體詩,但他當時最主要的文學成就還是歷史劇。蔡震説:“歷史劇是郭沫若整個創作的一個里程碑。”
1941年皖南事變後的兩年,郭沫若修改和創作了《屈原》《虎符》《孔雀膽》《棠棣之花》《高漸離》《南冠草》等六部歷史劇。它們就像一把把匕首,剖開歷史讓人看清現實;又似一盞盞明燈,點亮歷史指明抗戰的道路。周恩來在《我要説的話》一文中説:“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郭沫若自己則説:“在抗戰期中,一切文化活動都應該集中于抗戰有益的這一個焦點。”
在追憶陣亡師長王銘章時郭沫若曾説,“把有限的個體生命融化進無限的民族生命裏去”,而這正是他自己一生的實踐。(完)
(責任編輯:清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