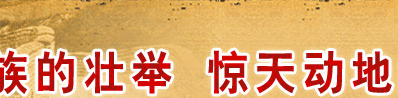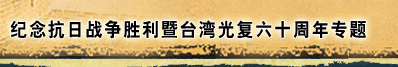國民黨前主席連戰。
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9月3日播出了白岩松專訪連戰節目,以下是節目內容:
解 説:這是臺灣地區的國民黨總部大樓,在這棟樓裏的7層正在舉行抗戰勝利60週年和臺灣光復的紀念展。這個名為“苦難的歲月,光榮的勝利”的紀念展從今年3月份就已經開始展出了。今年7月我們的攝製組也曾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過這個紀念展。
連 戰:你比如説到了這個櫥窗裏,你會特別地有感觸。旁邊就放了一個生銹的大刀片,還有一個小的匕首,而這塊非常有味道的是一個歌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刀進行曲》這樣的一個歌詞:“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武裝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連 戰:據籌辦這次展覽的國民黨內部的負責人,他跟我們介紹的時候也在説,其實在面對抗日的時候,國民黨、共産黨會聯手進行抗日,因此在這個展覽上也有所體現。你看在這個櫥窗的面前,就有當時在重慶共産黨辦的報紙《新華日報》。那在今天的這個展覽當中它也展出,感覺這也擁有內部的一些變化。
解 説:據工作人員介紹,開展5個月以來,每逢節假日都會有來自臺灣地區和大陸的遊客前來參觀。並且這裡已經成為在臺灣地區遊客最喜歡參觀的地方之一了。
白岩松:今年正好是抗戰勝利六十週年這樣一個紀念年。因為前一段時間我去臺灣的時候也看到,在國民黨的總部,搞了整個抗戰的紀念展覽;包括您也辦了很多的活動,包括座談會啊等等。您為什麼要舉辦這樣多的活動來紀念這樣的一個年份?
連 戰: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日子。“七�七抗戰”可以説是一種自發的、全民的一種奮起,對日的一種抵抗,這是頭一次。我相信在我們的歷史上面,是全民的一個奮鬥史。所以我認為,這對於臺灣今天尤其具有歷史的意義。今天,中國國民黨雖然是一個在野黨,我們的人力、物力,各方面的條件實在是有很大的一個局限;而今天,臺灣的“執政當局”,又可以説是非常明顯地有意來回避臺灣地區跟中國這種歷史的關聯,歷史的這種聯結。所以在這樣子一個的時刻,中國國民黨有這樣子歷史的一個責任,要來凸顯這個歷史的事實。雖然規模不夠大,但是我覺得,我的心意是盡了,而這個心意是應該必須要做的事情。
1936年8月,連戰出生於陜西西安。這張照片是他出生後不久與父親的合影。當時即將病逝的祖父連衡看到國難當頭,預料“中、日必將一戰。”於是,給孫子起名為戰,寄望這個三代單傳的獨孫將來能夠保家衛國。在連戰出生的第二年,就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對於在硝煙和炮火中長大的連戰來説,在西安8年的童年生活始終充滿著痛苦的記憶。
連 戰:抗戰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是在抗戰中長大的,我的婆婆還是被那個炸彈炸死的。那個時候還小,看到那個飛機來炸,我們就趕快跑。“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這首歌曲呢,學校還是持續地在教。
進入8月,中國國民黨還舉行了抗戰勝利60週年的座談會,攝影展,書畫展等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同時,臺灣民眾也用著不同的方式來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和臺灣光復這一特殊的日子。正巧在這個月,中國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也度過了他的69歲生日。
白岩松:連主席,首先雖然過去了好幾天了,但是要祝您生日快樂,健康長壽,心情愉快!
連 戰:謝謝你白先生。
白岩松:因為中國人講究是“過九不過十”,
我特意看了新聞,就是今年其實是您69歲的生日但是是過七十大壽。這個生日過得很隆重嗎連主席?
連 戰:還好了,就是家人、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吃吃飯,寒喧寒喧。
白岩松:這畢竟是您離開這個黨主席的位置後第一次過生日,心情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嗎連主席?
連 戰:我覺得還好。因為我還有很多的事情都在繼續地努力之中,生活的這個步伐並沒有慢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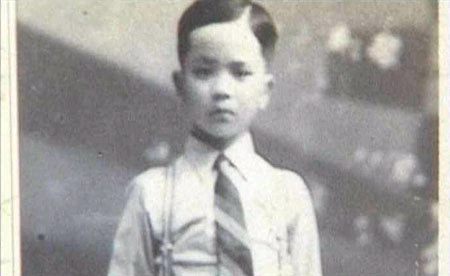
連戰幼時照片。
白岩松:連主席,其實一提到您8月27號這個生日,中國經常會説,兒子過生日的時候,是應該想起母親的這個日子。那麼當看到您的履歷的時候就能知道,您是臺灣的臺南人,但是為什麼六十九年前,1936年的8月27號您出生在西安呢?
連 戰:這個故事講來話長了。我們連家到我已經是第九代的臺南人,但是因為甲午戰爭之後,臺灣割讓給日本,所以我的祖父——他是一個富有強烈民族主義的一個人——所以不甘願在臺灣當日本人的奴隸,所以先把我的父親送回大陸,然後他自己也沒有多久之後,也回到大陸去。當時他送我父親回到大陸的時候,是跟當時的一個國民黨的元老——叫張溥泉先生(通信),他在這封信裏邊跟他講得很清楚,他説:“子胥在吳,寄子齊國。魯連蹈海,義不帝秦。況以軒黃之華胄,而為他族之賤奴,椎心泣血,其何能?”就是説堂堂正正的炎黃的子孫而為日本人的奴隸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就是好像在流血一樣,在錐心一樣,怎麼樣子能夠忍耐。所以把我祖父惟一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送到張溥泉先生的旁邊
追隨他。那麼後來因為要打仗,所以就從北京到了西安,我就是這樣子的原因所以在西安出生。
1936年8月,連戰出生於陜西西安。這張照片是他出生後不久與父親的合影。當時即將病逝的祖婦聯衡看到國難當頭,預料“中、日必將一戰。”於是,給孫子起名為戰,寄望這個三代單傳的獨孫將來能夠保家衛國。在連戰出生的第二年,就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對於在硝煙和炮火中長大的連戰來説,在西安8年的童年生活始終充滿著痛苦的記憶。
白岩松:您大陸行的時候,去西安的時候,是帶著感情地回到了自己的學校,然後去拜見自己祖母的墓地,然後包括去看您生活過好幾年的城市。是否經常回憶起來當初在戰爭狀況下給您留下的很多記憶?
連 戰:在這座城市當中,這次我到西安去,跟我記憶中間的這個西安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因為小的時候那個西安,是一個戰亂的西安,我大部分的時間除了在學校裏念小學就是躲警報,就是鑽在防空洞裏邊。那麼整個的這個環境,跟現在那可以説是完全是兩個世界。
白岩松:您在童年的時候躲警報,當面臨一個巨大戰爭的時候,是在大人的保護之下,其實您感覺沒看到很多殘酷的這種景象呢,還是當時也感受到了戰爭的這種殘酷?
連 戰:我想當然那個時候還小,躲警報也都是跟著父母,跟著學校的老師等等,防空洞離得也很近,都在城墻的下邊。就是因為日本人轟炸轟得太兇了,那個時候它已經佔了洛陽,轟炸重慶。去的時候也經過西安,回來的時候也經過西安,用不完的炸彈都掉到西安,所以陜西可以説滿目瘡痍。大馬路上面都是一個坑一個坑的,炸彈坑。那個炸彈片啊,沒辦法形容,大的炸彈片,小的炸彈片,那一碰到就完了。
白岩松:在您的記憶當中目睹過死亡跟鮮血嗎?
連 戰:直接去看到的並不多。但是我另外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個時候我是小學生,成千上萬的我們的中國的軍人——那個時候因為物質的條件很差——背著槍一步一步地走向前線。我身為一個小學生,跟我的同學都在路的兩旁邊經常地要歡送他們。
1944年,8歲的連戰隨父母從西安遷往重慶,重慶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所在地,日軍的空襲比西安來得更加頻繁。為了躲避轟炸,連戰和母親住在一所中學的宿舍裏,不久連戰被父母送往南山小學住校讀書。每週母親都會準備一小罐豬油,讓連戰帶到學校,就著鹽巴下飯。
白岩松:如果沒有記錯的話,1945年勝利的那一天,您已經搬家到了重慶。對勝利那一天的記憶現在清晰嗎?
連 戰:很清晰。因為那個時候我記得是在8月14號,透過廣播就是聽説日本人已經決定要投降了。反正那段時間先有這樣的消息,然後那個日本的天皇也透過廣播正式地宣佈日本無條件地投降,所以大家都非常地高興。我那個時候在南山小學,大概是四年級。
同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廣播講話譯文:戰局的發展未必對日本有利;世界的一般情勢更都和日本的利益相違。因此,我已命令我政府向中、美、英、蘇四國政府致送照會説,我帝國接受他們聯合宣言的條款……
白岩松:當時是正常地上課呢,還是跟家人或者跟學校去上街,參與到了這個狂歡的人群當中?
連 戰:上課還是要上的。那個時候,整個的重慶為了這個勝利張燈結綵,那麼還有一個9月3號的一個大遊行,滿街全部都是人,盟軍也很多,各省各地的老百姓、軍人等等,重慶從來沒有那麼熱鬧過。
抗日戰爭勝利後,連戰的父親奉命接收臺灣的治理工作,於是父親連震東帶著已經去世10年的祖父骨灰,由上海搭船返回臺灣,一年後,10歲的連戰也隨母親離開大陸。回到了臺灣。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清政府失敗告終。
白岩松:為什麼後來當抗日戰爭結束很快之後,你們這個家庭就選擇離開大陸回到臺灣?後來大人有沒有跟您講起這個決定是為什麼?
連 戰:因為臺灣是我們的故鄉嘛。抗戰勝利之後,日本人已經無條件地投降了,那麼當然我們要回到我們自己的家,回到我們自己的家園,重整我們的家園。這也是我的祖父、也是我的家人可以説是一貫的一個希望。當時不單是我們,有很多很多的人,臺籍的人士,也都是那個時候就前前後後地都回來了。
連戰的祖父連橫,是一位民族思想非常強烈的愛國史學家。1895年日本殖民者侵佔臺灣後,強迫所有的臺灣人都改成日本國籍。1914年1月連橫曾經主動向當時的國民政府申請恢復中國國籍。在連戰的眼中,祖父連橫不僅是一位愛國史學家,同時也是自己的思想寄託。前不久,中國國民黨訪問大陸的時候,連戰送給各界的禮物都是祖父連橫編著的《臺灣通史》。
白岩松:您的祖父當初其實在臺灣的時候就開始編著《臺灣通史》,當時您祖父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連 戰:最主要的就是希望民族的這種文化能夠永續而發展。因為當時日本佔領臺灣之後,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那麼日本在臺灣推動的殖民的工作裏面,很重要的一環就是所謂“皇民化”。簡單地來講,就是要把臺灣的人變成天皇的子民。這裡麵包括推動所謂“國語的運動”,就是講日本話;“改名的運動”,好好的中國人,名字變成日本化,日本的名字。透過文化——尤其是教育——讓下一代的人逐漸地忘記中國的傳統文化,凡此種種。所以要滅人家國家的人,第一首先要滅人家的歷史,我們的祖父大概也是根據這樣子的一個出發點。所以以他個人的力量,在那個非常困難的環境裏面,收集各種樣子的文獻,走遍了所有應該走的地方,那麼完成了他的巨著《臺灣通史》。
1895年4月17日,中日甲午戰爭以清政府失敗告終,李鴻章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其中的第二項就是,中國割讓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以及澎湖列島、遼東半島給日本。消息傳出全國譁然,臺灣人民更是悲憤交加,在馬關條約簽訂的第二天,臺北人民“鳴鑼罷市”抗議清政府賣國行徑。臺灣島上的抗日力量廣發抗日文告和檄文,鼓勵民眾抗戰到底。當時,連戰的祖父連橫只有18歲,面對國破家難,連橫感到唯有修史,才能證明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於是連橫用了13年的時間來蒐集資料,然後又經過10年的嘔心瀝血,終於在1918年完成了《臺灣通史》的編撰工作。

國民黨總部大樓。
白岩松:陸續最近也慢慢地大家知道,在您大陸行的時候,胡錦濤總書記在很親近地請您吃晚飯的時候,在臨別的時候送了您一個很特別的禮物,也跟您祖父有關。您是否可以把這個禮物背後的故事給我們的觀眾介紹一下?
連 戰:我非常地感謝胡錦濤總書記。他非常地週到,能夠給我這樣子一個富有歷史性的一個禮品。這個禮品就是在一個木頭的箱子裏面,他叫我打開,我打開以後,我看到的就是我祖父在民國大概是二年、三年的時候,申請恢復中國國籍的所有的文件。這個不容易的地方是,多少年了,差不多要一百年了,這些文件還那麼樣子地保存得那麼好,胡先生還這麼樣子地用心,大陸的朋友還這麼樣子地用心,能夠把它找出來。我是沒有話來形容我內心的這種感謝跟感動。
1914年2月,連戰的祖父連橫,在臺灣被日本殖民者侵佔了19年後,終於恢復了中國國籍。不僅如此,連戰的父親連震東也在抗戰前夕,恢復了中國國籍。
連 戰:那個時候中日已經要抗戰了,已經要八年抗戰了,馬上可能就要打了,所以他也毅然決然地向國民政府申請來恢復中國的國籍,還在陜西的日報上登了這個廣告。那個時候我們記得張溥泉先生,還有一個國民政府文官的文官長焦易堂先生兩個人給他作證,給他證明,恢復了他的國籍。所以我家裏面,過去在日本統治的時代,我們沒有日本人。我們都是中國人。
日本侵佔臺灣之後,臺灣人民以“誓不臣倭”的信心,用自己的力量武裝反抗日本佔領臺灣。從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中,臺灣同胞一直沒有停止過鬥爭。
連 戰:臺灣被割讓以後,臺灣的人民就開始了抗日的運動。所以不只是八年而已,是五十年都有。當然在,這五十年中間,那種血腥的統治、那種民族的歧視、那种經濟的剝削、那種政治的不公平等等,那是多得不得了,所以從臺灣割讓以來,大型規模的抗日的活動起碼也有二十幾次,至於那些小的衝突,那我就沒有辦法來加以估計了。所以我想,這個民族的大義是永遠存在的。有一位葉榮鍾先生,追隨林獻堂先生的一位葉先生,他的回憶錄裏面寫得就非常地清楚:在日據時代,因為日本殖民的高壓,所以在臺灣,這種民族的意識不但沒有降低,而是逐漸地高漲。
白岩松:提到臺灣光復呢,大家自然想到是因為抗戰勝利了。但是您説過一句話:臺灣的光復跟“七�七事變”是緊密連在一起的。我們該怎麼樣理解您説的這句話?
連 戰:在1943年,我們參加了開羅會議。在開羅會議上面,盟國正式地決定,戰爭結束之後,日本要把以前從中國所奪取的——或者説是竊取的——這些土地,包括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等等,都要還給——那個時候是明講的——還給中華民國。這是一個歷史。當然今天有一些無奈,有一些遺憾,因為有一些人,他把這個光復當為終戰,用日本人的話講的這是“終戰”,只不過是戰爭終止而已。這個對我們來講這是一個很遺憾的事情,也是一個很無奈的事情。因為他這個意識的形態蒙蔽了他對於歷史的了解。但是,我必須在這裡把我們整體的、正確的歷史的發展——尤其是在民族歷史上一個非常重大的、輝煌的一個成就——我必須在這裡再做一個強調。
白岩松:這也是您作為國民黨名譽主席,要隆重地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連 戰:當然,這個“七�七抗戰”還有其他的問題,還有其他的意義。我説這是第一次中國人民——大家的團結和奮起,在中國的戰場上面牽制了日本的皇軍至少有兩百萬人,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假如不是中國戰區進行這種抗戰,這兩百萬的日本兵到處地侵略、到處地燒殺搶掠,將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世界。這是戰略上的我們的貢獻。
第三我要講的,因為我們參戰,我們整個國家的地位大幅度地提升。那個時候可以説,百年以來不平等的條約一一地廢除。所以,“七�七抗戰”當然絕對不只是把臺灣光復了而已。在整個的世界上來看,宏觀地來加以觀察,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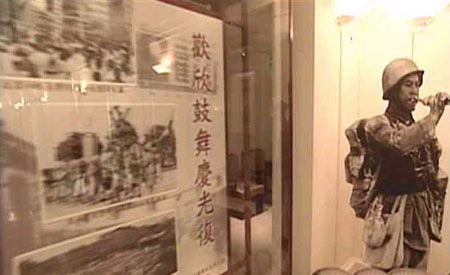
紀念館陳列展品。
白岩松:連主席,這些年,世界的各個國家慢慢也開始注意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中國戰區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做出的貢獻,它不是一個局部國家內的抗戰,您怎麼看待這樣的一種關注,您怎麼去認定的?
連 戰:八年的抗戰,我覺得我們犧牲得很大。粗估來講,三百萬的軍人跟將士犧牲了生命,三千萬以上的人老百姓犧牲了生命。真正所謂“白骨成山,流血成河”,這是我們所經過的一個歷史。但是我必須要講,那是全民的奮鬥,中國國民黨參與了正面的、正規軍的作戰,中國共産黨同樣地也參與了比如説平型關、百團大戰,這些都是歷史的過程。我們今天后人回顧過去,要以一個正面的態度來回憶這些歷史。所以我最近也感到蠻高興的,因為我看到在四川大邑縣,也有老百姓來成立“建川博物館群”,那麼也設立了國民黨抗日軍館。三千多萬的軍民犧牲了生命,不是為哪一個黨,是為中華民族犧牲了他的生命。是為了這個民族的生存、發展、尊嚴和子孫千年萬年的未來所做的犧牲,所以我們要把這個事情看得宏觀,要看得遠大,其實在那個時候,因為面臨的是民族的危亡,因此國共兩黨也聯起手來。
白岩松:剛才您又特別強調是全民的抗戰,那麼回過頭來看,當初大家都覺得中國已經這麼貧窮,這麼落後,怎麼可能打贏?當時日本是世界第七大工業國家,但是最後堅持了八年,我們贏了,你覺得通過這八年,看到了這個民族的一種什麼樣的精神是它勝利的重要的因素?
連 戰:在這整個的過程裏面我可以看到,這個民族是有它的韌性的,是艱忍卓絕、是堅韌不拔、是刻苦耐勞,我們的志氣實在是可嘉的。在這個過程裏面,那種犧牲、那種顛波流離,沒有辦法再形容了。今天,要把這段歷史要永遠地把它記憶下來,不但是承先,還要啟後,要讓後人知道,在這個年代裏面,這一群人,曾經做過這些事情,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歷史的進程。
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已堅持42年之久的抗日戰爭的臺灣同胞,從兩條戰線上參加了抗日戰爭,一條戰線是在臺灣地區堅持與日軍進行鬥爭,另一條戰線是奔赴大陸直接參加抗戰。抗戰時期在大陸還活躍著這樣一支部隊,他叫臺灣義勇隊。臺灣義勇隊成立後,在醫療,生産,宣傳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主動進攻打擊日軍。據統計,在8年的抗戰期間,直接地參與祖國大陸抗戰的臺灣同胞有5萬多人。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東京灣的美軍戰列艦密蘇裏號上,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書上向中,英,美,蘇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日本殖民者從臺灣地區撤離,至此,在中日甲午戰爭的60年後,臺灣光復。
白岩松:連主席,我曾經看到過在臺灣做的一個關於抗戰的片子,片名叫《一寸山河一寸血》,看完這七個字我就已經有一種熱淚盈眶、熱血沸騰的感覺。您覺得經歷過這樣一段歲月的民族,面對未來,應該收穫什麼?
連 戰:我們回憶過去、展望未來,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永遠不要再被人家所欺負。所以富強、康樂是我們應該追取的一個目標。但是,如何能夠來追取一個富強跟康樂的未來?我在北京大學也一再地強調,我們要為這個民族來立生命,為萬世來求太平,一定要大家在和平相處、合作、雙贏的這種局面之下。那麼共同地來促進和平,共同地來謀求發展,共同地來享受今後的繁榮。我相信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宏觀的一個期盼。
白岩松:連主席,最後兩個問題,一個是臺灣在六十年前因為抗戰勝利的光復,對於這個歷史來説,對於這個民族來説,意味著什麼呢?
連 戰:對於民族來講,我覺得,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是非常強烈的。吳濁流先生寫了一本書叫做《無花果》,他形容:在光復的時候,臺灣六百萬人民,那種歡心雀躍的那種心情,認為國家今天以後,大家能夠真正地來建立一個比日本統治時候還好的一個臺灣。未來是一片彩色的。所以我想,這些都是人的本性。那麼怎麼樣子能夠讓我們今天在這個大的環境裏面,能夠大家彼此用這種千載難逢的這種機會,來各自地、全力地衝刺,那麼這個整個中華民族啊,那種要脫胎換骨,那種可以説是享受一個安和樂立的一個生活的一個期盼,已經不是所謂一個夢想而已,是真正可以達到的一個時候,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所以在這個時候,讓我們這一代人用我們的智慧好好地來團結,來合作,來掌握這個機會。這是我的一點期盼。
白岩松:連主席,最後,記得您在抗戰勝利六十週年座談會上,你講過這樣的三句話:面對歷史可以寬恕,但不能忘記,更不能篡改。那我們今天是否可以拿您對這三句話的解釋,來當作今天我們節目的結束。
連 戰:非常地好。我非常地感謝。假如是能夠用這樣的話,大家來勉勵,我們對於我們過去的敵人可以寬恕,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夠忘記。那麼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説,我們對於過去的歷史,我們要給它一個正面的一個認識,我相信唯有正確地面對過去的歷史,才能夠有一個正確的面對未來的一個態度。
(責任編輯:清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