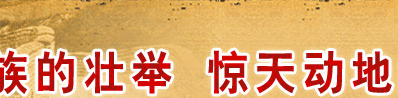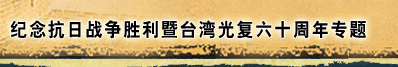| |
怒江東岸保山城,1944年滇西反攻的大本營。飛機甫一降落,走出艙門,氣象已是不同,四週群山環抱,雲低天高。
出保山向西,穿橫斷山支脈,跨怒江往南,有當年血戰之地松山和龍陵,再翻高黎貢山,就是抗日名城騰衝。繼續向西南走,經芒市,到達中緬邊境城鎮畹町,沿途已是一馬平川。
這是當年中國遠征軍滇西反攻的大致路線。今日重走一遍,格外感覺山河壯闊。車窗外,天空湛藍,高山體態敦實,其上一片蒼茫綠色,雲朵飄過形成大塊陰影,土地殷紅,熱帶作物茂密,雨後怒江色調昏黃,愈發顯得渾厚,江邊壩子卻是翠綠如洗。
10天中,在這幅大畫卷前,我聽著抗戰老兵們講述當年的血火親歷,聽普通百姓講當地名士的錚錚風骨,聽國殤墓園內鳥啼蟬鳴,聽松山峰頂松濤似海……宛若沉浸在一首宏大深沉的敘事曲中。
“如此大好河山,豈能淪喪倭寇手中?”同伴一聲感慨,道出此曲個中真情。
不屈老人
在滇西騰衝,有一座當地人視為精神家園的國殤墓園。墓園修建於1945年,當年7月7日落成,以紀念為收復騰衝,洗刷滇西人恥辱而犧牲的近萬中國遠征軍官兵。
墓園忠烈祠後,有一座不高的小土丘,上邊密密麻麻地樹滿了30多釐米高的石頭墓碑,墓碑上刻著紅色小字,説明陣亡者軍銜和姓名。
當年遠征軍36師106團2營便衣隊的14歲上等兵周光永告訴我:“其實,這裡每一塊墓碑下邊埋的並不就是墓碑上刻著名字的那個人。戰役結束後,20集團軍把收容的中國士兵骸骨放在一起火化,在每一塊墓碑下面撒了一把(骨灰)。”
戰史記載,騰衝之戰,1944年由夏徂秋,前後歷經大小40余戰,擊斃日軍6000余人,城內日軍無一逃脫。中國遠征軍傷亡官佐1334員,士兵17275名,其中大多滇西本地人。
抗戰前繁華的“極邊第一城”騰衝經此一戰已成一片焦土,但當地人卻無任何遺憾。因為,在他們看來,1942年5月,駐騰衝的騰龍(騰沖和龍陵)邊區行政監督、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三公子龍純武不戰而逃,讓292個日本兵不費一槍一彈佔據這座邊關要塞,才是奇恥大辱。
國難當頭,有人逃跑,更多的滇西人卻挺身而出,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國民黨元老、騰衝人李根源。在滇西採訪時,幾乎每個人都會提到他的名字。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養溪,生於高黎貢山。1905年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時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09年回國後任雲南講武堂教育長、校長,參與領導重九起義和護國討袁運動。
1939年,李出任雲貴監察使,面對老家淪陷,上書蔣介石要求成立一支“老子軍”奔赴滇西抗戰。在滇西淪陷至反攻的兩年多時間內,李根源隨抗戰軍隊轉戰滇西,把“雲貴監察署”的辦公地點一再往西遷,從大理一直搬到最前線騰衝,並以60歲高齡聯絡怒江兩岸中國軍隊和抗日遊擊隊共同作戰。
曾給李根源當過侍從的周光永至今難忘老人家所寫《告滇西父老書》中的語句:“雲南已成戰場,滇西即是前線……驅逐敵人退出騰衝,退出龍陵,甚至退出緬甸……始能保住滇西過去歷史上的光榮,始能保住雲南抗戰歷史上有光輝一頁……雖毀家紓難,赴湯蹈火亦在所不惜。”
而更多本地老兵則都對“李國老”在大理黃埔分校的每週講話印象深刻。1942年,國民政府採納李根源建議,在大理成立“滇西戰時工作培訓團”,後成為黃埔分校。在李的保薦下,近千名從滇西淪陷區逃出來的熱血青年進入這所學校,培訓之後,分入各支部隊,擔任少尉排長,參加光復家鄉的戰鬥。
已經83歲的劉志聲是保山人,當年從大理軍校畢業後進入第2軍9師27團,從保山一直打到緬北。他回憶説,大理受訓時,崇聖寺三塔下,每週李根源都會與20集團軍司令宋希廉一起訓話,“他們站在土臺上面,李根源長袍馬褂,宋則是一身軍裝。李根源講的都是一個意思,我們滇西人必須雪恥,必須打回老家去。我們在下面聽著個個熱血沸騰”。
直到現在,劉志聲還依稀記得李根源為他們所作的歌:
“仇比洱海深,意志比蒼山高。滇西青年奮起,雪恥救國責在雙肩,團結一致,勇敢向前,哪怕血染千里滇緬。”
騰衝光復後,又是李根源主張建立國殤墓園。現在,墓園最高處紀念碑上,“民族英雄”四個藍色大字,為李根源手書;陵園最低處,跪向墓碑的地方還有一個收集日軍屍骸的土墳,立有黑色“倭冢”二字,也是李根源手書。
以這位不屈老人為領袖,滇西各地鄉紳、土司紛紛投入抗日救國,其中還有一位頗為著名的張問德。此人62歲賦閒在家,見日本人佔了騰衝,竟臨危受命當了淪陷區的縣長,在騰衝發動全民抗戰。他敢於責令畏敵逃跑的前縣長交回印信,痛斥日軍誘降花招,為週旋生存,先後8次徒步翻越高黎貢山,當年被譽為全國淪陷區500個縣長中骨頭最硬的一個。
騰衝滇緬抗戰博物館中有一鎮館之寶,就是1943年李宗仁親贈張問德的紅藤杖,上面題了8個字:抗戰到底,步步前進。
同仇蟻民
60年前,曾有文如此記載滇西反攻時的場景:“天空機群蔽天,沿江卒伍遍地,支前民工,酷似蟻群”。讀罷不由豪氣頓生。
曾組織過後勤支援工作的85歲老人楊鴻恩告訴我,在這場壯闊的民族戰爭中,最讓人感動的就是滇西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他們太可憐,也太好了。高黎貢山海拔4000米,還有怒江天險阻隔,沒有老百姓提供的巨大後勤保障,反攻根本就沒有可能”。
楊鴻恩是保山人,曾任20集團軍後勤總監部運輸處第一分處少校主任。20集團軍是滇西反攻的右翼軍,總指揮宋希廉,主攻方向是騰衝。左翼軍為第11集團軍,主攻龍陵。
楊鴻恩説,其實早在1942年中日兩軍沿怒江對峙之後,就已著手反攻準備。期間,他勘察了保山所有通向怒江渡口的道路,道路都用工具進行測量,保證不低於2.5米,凡是不夠標準的道路,均有當地鄉鎮政府組織民工加以整修。
“反攻開始前,軍方確定4條支前線路。保山36個鄉中沒有淪陷的34個鄉全部動員起來,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前線。每個鄉都組成了一個民伕大隊,一共組成了17到18個黃牛運輸隊,25個騾馬運輸大隊。從戰前開始一直到勝利,每天都有2.5萬到3萬民伕一直在源源不斷地為前線供血。
“4條路線中,前兩條還好,後兩條,其實以前只是馬幫運貨走過,路途艱險,那時候走得慢呀,一去就要兩三天的時間。尤其反攻的時候是雨季,道路泥濘,根本就沒法走,每個民伕,或者用肩挑或者用背簍背,每個人都是幾十斤,一步一滑地走在崇山峻嶺之間。遠遠望去,在山間的小道上,不間斷的民工運輸隊真的就像一群螞蟻一樣。
“那時候,民伕每人每天二十四兩米(16兩為一斤)、三錢鹽巴,騾馬加倍。而那些馬幫的頭領,根本就不要錢糧。吃不飽,還要日夜不停地趕路,許多人是被累死在路上的,還有些人一個瞌睡就跌下了幾百米深的峽谷,一路都是死屍。騰衝淪陷之後,當地男人有的去打遊擊,有的被組織抬擔架,男人都沒有了,我親眼看到過,在運輸隊裏居然有很多小腳女人。她們哪走得了那種路呀,挑的東西一般就是軍糧和子彈,數量很少,但看見她們,我的眼淚一下就掉下來了。”
説到這裡,老人的眼圈又紅了。
在騰衝,還有家喻戶曉的戶帕送軍糧的故事。60萬斤軍糧,老百姓只用了五六天時間,翻越高黎貢山送到了騰衝城,很多人在路上活活餓死,卻沒有動背囊中的一粒糧食。
保山市滇西抗日戰爭紀念碑的銘文上,寫著這樣一段話:“(滇西反攻時)僅保山地區就出動支前民工二十多萬人。修公路、建機場、築工事、運軍糧、送彈藥、抬擔架,犧牲民工二萬四千六百多名。其中,保山縣就補充兵員兩萬多名,貢獻民工一千五百四十二萬工日,死亡民工三千八百五十余人,出動騾馬一百一十九萬多工日,馱牛三十二萬多工日,死亡牛馬五千九百多頭,供應軍糧大米三千五百八十萬公斤,馬料四百四十五萬公斤,豬牛肉二十三萬二千多公斤,其他物資不計其數。”
3850多人,這幾乎相當於一場戰役中一支軍隊的陣亡人數。要知道,那時候,保山縣全部人口不過30萬而已。也就是説,為收複國土,1%的當地人死在了支前路上。
所以,1945年1月27日中國遠征軍與中國駐印軍在緬甸芒友會師大會時,中國遠征軍總指揮衛立煌將軍總結滇西緬北抗戰勝利原因的第一條就是:滇西老百姓的無私支援。
“那些老百姓覺得保山沒有淪陷,我們沒有淪為日軍的奴隸,那是軍隊將士的功勞,所以只要能夠收復失地,只要能夠把日本人打出去,出多少錢多少力都是應該的。”楊鴻恩的話算是對滇西人民不計回報的付出作了註釋。
浴血松山
在滇西反攻中,一共有三場著名戰役,一是騰衝攻堅,二是松山大戰,三是收復龍陵。三戰無不慘烈異常,至今戰場遺跡仍保存完好的就是松山。
松山大戰,從1944年6月4日一直打到9月7日,中國遠征軍第71軍和第8軍先後上陣,一共發起了10多次總攻,傷亡官兵8000多人,最終使用坑道爆破的戰法,這才徹底消滅盤踞在這裡的日軍“拉孟守備隊”1260人,生俘敵28名,慰安婦數名,繳獲步槍437支,輕重機槍34挺,各種火炮16門,戰車3輛。
登上松山那天,恰逢7月7日。主峰子高地之上,兩個直徑近10米的巨大彈坑赫然在目,那是當年中國工兵部隊從地下掘進使用70箱共3噸炸藥將日軍主碉堡炸飛後留下的標示。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大小彈坑散落在山坡山頂各處,如今裏面落滿了乾枯的松針,淺淺的,只有幾十釐米深。掩體、散兵坑、戰壕和交通壕依舊相互通連,最深的一段交通壕深達2米,據説當時中國遠征軍為向地道裏搬運炸藥而挖。
住在主峰下的董姓村民有40多歲,他告訴我説,小的時候,他和其他夥伴經常上山挖彈片、彈殼換錢,他自己一共挖到過上百斤的戰爭廢品,都挖出了經驗——“那時候多得很,彈坑四週很容易找到彈片,子彈殼一般散落在戰壕中。我還挖到過迫擊炮彈後邊的尾翼,是銅做的。”
當年中日軍隊為何要在這座山上殊死拼殺呢?到了實地,答案一目了然。當時連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唯一一條補給線滇緬公路,就在松山半山腰盤旋而過,松山海拔大約為2150米,而滇緬公路這一段則為1600米左右,從公路仰望,松山頂峰幾乎直上直下,可謂扼守要衝,不可不爭。
當初日軍負責守松山的“拉孟守備隊”,兵力不算多,但是,自1942年佔據松山以來,他們已經在這座險峻山峰上準備了兩年。據戰史記載,日軍共在松山及附近山頭修築了20多個陣地和觀察所,每個陣地依地形在制高點構築1~3座主碉堡,在主堡兩側又構築若干子堡,並在陣地前構築側射潛伏小堡。陣地之間塹壕交錯,互相連通。
日軍碉堡大多分三層,上層用於射擊觀察,中層休息兼射擊,下層儲存彈藥。每個堡壘上掩蓋數十釐米直徑原木4到5層,再鋪上3毫米厚鋼板數層,鋼板上再堆厚度1米以上的沙土。堡壘露出地面部分四週,又安置盛滿沙石的大汽油桶3層,桶間同樣復加鋼板數層,桶外被土。這樣的堡壘,38釐米榴彈炮直接命中都不能摧毀。
日軍曾揚言:“中國軍隊不死亡10萬人休想攻克松山。”最後,中國軍隊的犧牲數字雖然沒有這麼誇張,但經歷那一仗的第8軍103師309團衛生員李文德説,他從沒見過那麼多死人。
309團是最後投入戰場的預備隊,那時戰鬥已經打到子高地之下,距離峰頂只有100米而已,但中國軍隊卻再也無法取得進展。其中原因,親臨實地就會明白——在子高地近60�的百米斜坡之下,是一處寬約20米的山間坪地,沒有任何遮蔽物。坪地之下,又是近70�的斜坡,日軍守在此處,上邊有火力掩護。即使中國軍隊攻上山坪,也會完全暴露在子高地機槍火力之下。
李文德説,那時候,他就從那塊山坪向下抬傷員和死屍。有中國士兵的,也有日本士兵的。傷員一般需要經過軍醫檢驗,檢驗死亡後,衛生員們就把屍體拖到現在高地下的水塘裏。
“那時候沒有水塘,那是一個美國飛機炸的大彈坑,後來下雨才變成水塘的。”他回憶説:“我自己最多的一天拖過七八具屍體,拖過去摞在一起,有一人多高。仗打得激烈,那些死人的軍裝都沒機會脫,武器裝備也不拿下來,連臂章都沒得摘,就那樣帶著手榴彈,穿著衣服,扎著皮帶堆在一起。”
現在,在水塘邊山還有一塊墓碑,為103師松山戰役陣亡將士公墓。墓誌銘記載,其下所埋忠骸未及當日犧牲者數目之一半。
“那些日本人的屍體就往山下的峽谷裏一扔,所以很多都被水沖走了。打了那麼長時間,有1個月,我從來沒洗過臉,沒換過衣服,每天拖傷員、死屍,那時候,兩隻胳膊袖子上的血都結在一起變硬了。”老人説。
李文德記得,子高地被攻下來那天是8月20日。頭天,團長把全團還能作戰的人員都集中在了一起,包括李文德這樣的衛生兵。點名結果,全團還剩下450來人。
“團長什麼也沒説,就問了一句:‘誰願意當敢死隊舉手。’”李文德回憶説,“有150人舉了手,我也舉了手。團長下命令説,這150個人分成三組,他自己、副團長和另外一個營長一人帶一組,剩下沒舉手的人一樣也得衝鋒,就是跟在敢死隊員後邊。”
老人説,團長當場給敢死隊員們每人發了2000塊“國幣”。當時,在保山城裏,吃一碗耳絲的價格是5塊“國幣”。
戰史記載,整個戰役,103師參戰兩個月,所有直屬部隊都拉上前線,師屬特務連和工兵連傷亡殆盡,普通的步兵連,最慘的只剩下2個人。而李文德的數字則更為感性,他所在的衛生隊,本應最為安全,但一仗下來,40人中也只八九個人沒有受傷,光軍醫就打死好幾個。
採訪後,我曾如此感嘆:壯闊滇西,壯闊勝利。那可以説,是對這片土地榮耀歷史的一種由衷咏嘆。然而,當我在深山中面對一個又一個貧困卻自足的抗戰老兵時,我又聽到了樂曲中最低回的聲音。
好,不説慚愧,不究過往。我只想每個願意傾聽這首滇西敘事曲的人去動手寫下新的音符。我清楚地記得,那個被稱為“打不死”的寸時中老人,當提起遙遠的北京,有一個老兵論壇(www.52laobing.com),有人每月募捐給他50元生活費時,他笑得像個受寵的孩子一樣。
(責任編輯:齊曉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