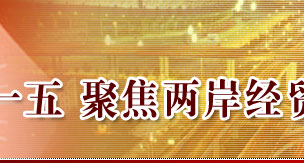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將於10月召開,中央全會每年例行一次,早已為公眾所熟悉,但每次全會到底承擔何種任務,這次五中全會相較往屆,是否有特殊意義,中央每次會議的關注點有何變化,本報記者走訪專家學者,對此解讀。
“計劃”改為“規劃”
8月初,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和家人一起到北戴河度假,沒想到碰上許多中央部委的“老熟人”,原來他們是國家“十一五”規劃起草小組成員,已經在那裏呆了十多天,正在討論、起草“十一五”規劃。
“十一五”規劃是十六屆五中全會的主要議題,規劃經本次中央全會討論通過後,將於明年3月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與前面十個“五年”明顯不同,第十一個“五年”由“計劃”變成了“規劃”。
“雖一字之差,內涵卻不盡相同。顯示出黨對發展內涵的認識已有變化。”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博士辛鳴説。
以“五年”為單位進行國家建設的“五年計劃”模式,起源於前蘇聯。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全面學習,自1952至1953年,多次派出包括周恩來總理等人在內的代表團到蘇聯學習,在他們的幫助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自1953年起實施。
“一五”計劃主要是指令性的經濟計劃,事無巨細,涵蓋了方方面面的經濟增長指標,從工業總産值增長98.3%、手工業增長60.9%、大型工礦項目施工694個到具體的鋼鐵産量增加多少、煤炭産量增加多少等等。
“當時中央政府管2萬個硬指標,計劃就是法律,硬得很。”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回憶,蘇聯當時派出數千位專家到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幫助實施“一五”計劃。僅當時中央黨校的蘇聯專家,就有十多位。
改革開放後,中國從計劃向市場轉軌。五年計劃從“一五”推進到“十五”,強制性和指令性逐漸消失。但作為一種習慣,五年計劃仍得以沿用,規劃國家經濟的整體發展。
“計劃變規劃,是一個進步,表明計劃經濟體制基本破除了。”沈寶祥説,“但像歐美那些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它們並沒有這種大而全的計劃。”
辛鳴認為,社會發展有階段性,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社會發展已基本定型,“我們適當有一些通盤考慮。心中有數,效果會更好一些。”
新發展模式
對此次五中全會,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認為,“十一五”規劃將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方面作出重大努力。
經過20多年的漸進式改革,中國的改革發展已經進入關鍵階段,貧富分化、城鄉差距、腐敗等多年積累的問題開始集中暴露,“十一五”規劃的五年正與此同時。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消除社會的不和諧因素,事關改革開放大局。
“五年一次計劃修編,看似例行公事,但從‘十一五’來看,更多意味著一種重要轉折。”葉篤初認為,新一代領導集體已有一整套社會發展和執政理念,“十一五”規劃將是一次集中的展示。
在辛鳴看來,“十一五”規劃的出臺,將意味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全面轉型。“綜觀近年來的經濟發展,通常只看到量的增長,相當比例的社會民眾並沒有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本來發展經濟只是實現社會富裕和人民幸福的手段,但一些地方領導不自覺把它當成目標,一切事情給經濟發展讓路,群眾的福利、人的尊嚴被認為是可以付出的代價。”
葉篤初感覺,“這回討論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骨子裏更重視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據他透露,主持“十一五”規劃編制工作的負責人曾透露:編制的出發點,要從偏重物質財富增長,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強化有關擴大就業,加強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規劃,增加人文和社會指標。
宏觀調控的不解之緣
回顧以往幾屆五中全會,無一例外是研究經濟問題,間或有重大人事問題。葉篤初解釋,這與黨和國家的政治安排有關,“每年的全會承擔不同的任務”。
“一中全會一般在代表大會結束後舉行,帶有例會性質,主要是人事問題,如確定中央領導班子,中央領導的格局、分工,以及相應的工作團隊或制度。
“二中全會往往‘承前啟後’,頭一年開黨代會選出新領導集體,確保黨對國家的領導;次年的人代會,則選舉委員長和政府總理,落實黨對國家的領導。
“新一屆領導集體真正進入角色,開始在經濟建設上謀篇佈局,一般要到三中和四中全會。”中央黨校一位教授舉例,吹響改革號角的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出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是十二屆三中全會。
而到五中全會召開時,已是一輪經濟發展的一個節點,又往往與“宏觀調控”結下不解之緣。今年五中全會召開前,中央政府從“鐵本事件”到“房産新政”,剛剛踩過一次剎車。
回顧我國的五次宏觀調控,有四次在五中全會之前,例如1989年11月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決定對經濟進行治理整頓。是為第三次宏觀調控,而1995年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九五”計劃,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主持進行了改革開放來的第四次宏觀調控,實現經濟“軟著陸”。
葉篤初認為新一屆領導集體風格務實,“十一五規劃”如果通過,中央將在兩年時間內力求抓出政績和實效,向十七大獻禮。(李梁 許桐琿)
來源:南方週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