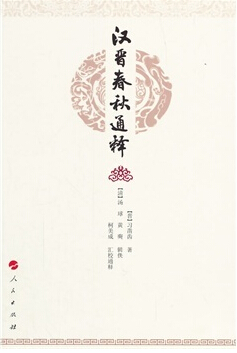
本文為《漢晉春秋通釋》前言,柯美成匯校通釋,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
一、習鑿齒以及漢晉襄陽習氏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東晉史學家、文學家。其生卒年説法不一:一説約生於晉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卒于晉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一説約生於晉明帝太寧五年(325年),約卒于太元十八年(393年);更有一説生於晉成帝鹹和三年(328年),卒于晉安帝義熙九年(413年),等等。本前言敘事暫取前一種説法。
襄陽為習氏郡望。據唐林寶撰《元和姓纂》卷十《二十六緝�習》:“《風俗通》雲:習,國名也。漢習響為陳相。”下標郡望“襄陽”,並晉習鑿齒著《漢晉春秋》雲。南宋鄭樵撰《通志二十略》,其《氏族略第二》將習氏歸入“以國為氏�夏、商以前國”類,引據與《元和姓纂》略同。又《資治通鑒》卷七十二《魏紀四》元胡三省注:“《姓譜》:‘習,國名,後以為姓。’《風俗通》:‘漢有習響,為陳相。’”至清王仁俊輯《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其《補編》錄宋何承天撰《姓苑》曰:“襄陽有習氏,後漢有習響。”始言習響為後漢人。而民初臧勵龢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著錄習鬱、習鑿齒等歷代習氏十一人,獨不錄習響其人。該書附錄《姓氏考略》則雲:“習,少習。本地名,析縣東之武關,見《左傳》杜注,是習氏以地為氏。望出襄陽。”究竟是以國為姓還是以地為氏,以國為姓則國在何處,習響生當前漢抑或後漢及其籍裏何處,而今皆已不可詳考;有籍裏、宦跡可考並澤被後人的習氏始祖,當推後漢初襄陽習鬱。
習鬱,字文通,習融之子。據習鑿齒著《襄陽耆舊記》雲:“習融,襄陽人。有德行,不仕。”(卷一《人物�習融》)融子鬱,漢光武帝時為侍中、黃門侍郎。“鬱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同夢見蘇嶺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卷三《山川�鹿門山》)後習鬱依范蠡養魚法在襄陽城南數裏之峴山南麓造大魚池,中築一釣臺。池邊有高堤,皆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鬱將亡,敕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為起冢于池之北,去池四十步。”(卷三《山川�習家魚池》)後世因名其池為習家池,省稱習池。而峴山、習池自古為賢達勝士賞心遊宴之處。晉羊祜鎮襄陽,“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咏,終日不倦。……祜卒後,襄陽百姓于祜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羊、杜並美,“預好留身後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乃刻石為二碑,記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沉峴山之下,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山季倫鎮襄陽,“每出嘻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曰:‘此我高陽池也!’”(卷五《牧守�羊祜、杜預、山簡》)習家池因又別名高陽池。而鹿門山與峴山隔漢江相望,為漢末名士龐德公及唐代詩人孟浩然、皮日休隱居之地。唐宋以降,峴山、鹿門山不知賺取文人騷客幾多翰墨,一時名家巨擘如陳子昂、張九齡、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皮日休、范仲淹、歐陽修、曾鞏、三蘇父子等皆赫然在列。而二山與習氏已結緣在先。
習家池則歷經近二千年,至今風物依然。她背倚峴首,群峰環峙,俯臨漢江,帆檣隱現。北望襄城,樓閣崢嶸;東眺鹿門,重巒疊嶂。池苑內,祠館臺榭,飛檐走角,竹林清幽,山泉流碧。陽春柳浪聞鶯,炎夏荷風送香,金秋碧池印月,隆冬暖雪沃松。四時八節,皆有賞心悅目之境界。
自習鬱以降,襄陽習氏“宗族富盛,世為鄉豪”(《晉書�習鑿齒傳》)。漢末,天下大亂,群雄兵爭,諸習氏因緣際會,多有一時俊傑,名著簡冊。其中,又以追隨劉備、諸葛亮征戰,從龍入川,立功仕蜀者居多。據《襄陽耆舊記》載,習承業博學有才鑒,歷仕蜀漢江陽、汶山太守,都督龍鶴諸軍事。習珍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襲殺關羽,遣潘濬討珍,濬欲面見喻降,珍謂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不可逼也!”臨難之際,仗劍自裁,劉備追贈之為邵陵太守。“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卷一《人物�習承業、習珍》)《三國志�蜀志�楊戲傳》載《季漢輔臣讚》曰:“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任雒、郫令,廣漢太守。子忠,官至尚書郎。”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曰:“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按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為禁軍首領“五校”之一,秩比二千石,表示其已職居朝廷樞機。《蜀志�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雲:“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范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這無疑是一件非常得人心的大事。另有“習詢、習竺,才氣鋒爽”,“習藹有威儀,善談論”,(《襄陽耆舊記》卷一《人物�習詢附習竺》)而皆不詳其宦跡。而習珍之子溫陷於吳,以“識度廣大,歷長沙、武昌太守,選曹尚書,廣州刺史。從容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跡,不結權豪。”後為荊州大公平,入晉仍居大中正之職。(《襄陽耆舊記》卷一《人物�習溫》)大約就在蜀漢政權時期,襄陽習氏這一漢世土著舊族,已悄然躋身於新興士族階層。
然而,習氏家族的這種屬性轉換在入晉後似乎停滯了,這或許與其家族成員主要仕于蜀漢,亡國臣民仕進之路必然受阻有關。根據現有史料,襄陽習氏在兩晉時期並未成為像江南王、謝那樣的高門士族,仍是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鄉豪”。習鑿齒即自言:“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卷五《牧守�山簡》)西晉時,諸習氏見於史乘者除習溫外尚有一習嘏:“習嘏為臨湘令﹑山簡征南功曹。蒞官舉大綱而已,不拘文法。”(卷二《人物�習嘏》)一介縣令、將軍府功曹,與習承業、習隆等蜀漢時為顯宦,已不可同日而語。東晉時,這種情況亦未見大的改觀。這從習鑿齒本人曾受到的歧視可以説明。據《世説新語�忿狷篇》雲:“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並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孝標注引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王令即王獻之,字子敬,以曾為中書令,故人稱王大令、王令。謝公謂謝安,胡兒謂安侄謝朗。今人余嘉錫箋疏曰:“習鑿齒人才學問獨出冠時,而子敬不與之並榻,鄙其出身寒士,且有足疾耳。所謂‘不交非類’者如此。”(《世説新語箋疏�忿狷第三十一》)徐震堮則箋注曰:“晉人講門第,士庶不同坐。謝安見獻之不肯與習同榻,故以拘于習俗譏之。”(《世説新語校箋�忿狷第三十一》)話雖如此,這也恰好證明了襄陽習氏在南渡中原士族一些人眼裏,仍屬於“寒門”、“庶族”一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