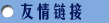《大國學:季羨林口述史》
北大一別後,我因為工作關係聯繫過季老幾次,每次交往的過程都讓我頗感意外,卻也了解到季老謙虛嚴謹的治學態度。
1986年,我負責主持《世界哲學家辭典》的編寫,編委會準備把季老列入辭典,於是向季老約稿,但一連幾次都遭到拒絕。季老表示,我不是什麼哲學家,在哲學上沒有什麼主要觀點,不敢在《世界哲學家辭典》中濫竽充數。我只好使盡渾身解數,“費盡心機”,才説服季老讓當時的助手李錚提供了一份簡介。
1992年,我的《阿拉伯哲學史》新書在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求季老寫評介文章,為這本書“吹噓吹噓”,但是季老很快回信,説自己“對阿拉伯哲學一竅不通,你問我的意見,等於問道于盲”。
隨後,我一直在山東大學哲學系工作,和季老屢有學術交往,《文史哲》主編丁冠之教授曾經委託我幾次向季老約稿,季老致信説:《文史哲》我一向認為是一份有水準的學術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這是一種光榮。但是我寫的東西,只要我認真從事的,其中難免有一些古怪字母。這種文章送給人家,給排印造成困難,我心裏每每感到不安。結果季老都以自己搞的東西古怪而婉拒了。1994年,《文史哲》再次請季老提供學者談治學的稿件,季老仍然拒絕。在“軟磨硬泡”下,季老終於答應可以提供資料給我,於是有了我的那篇《學貫中外的季羨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發表。後來,季老評價這篇文章“超出了他的期望”,我當然很欣慰。
此後,我萌生了為季老寫傳的想法。當時很多人都在想做這件事,季老都沒同意,我心裏也直打鼓。一次去北大朗潤園看望季老時,本準備正式提及此事,卻一直猶豫著不敢開口。直到季老對我所寫的文章和學術表示肯定,並且寫信給我願意讓我寫傳時,我才有了底氣。
1996年1月份,我在季老家彙報有關傳記的準備情況,季老説自己沒有時間,便讓秘書李玉潔女士請我在勺園吃飯。要了幾個菜,落座以後,李玉潔老師單刀直入,站起來用手指著我質問:“蔡德貴,你有什麼資格寫《季羨林傳》?”
我當時一時語塞,沉默一會禮後,我説:“要論資格,北大有那麼多季老的同事、學生,有研究季學的教授,我還真是沒有資格。但是有一點,我和季老同是山東人,我想我可以從山東的文化底蘊來解讀季老的治學和為人。我可能能夠理解季羨林先生成長的環境,所受齊魯文化的影響。”李玉潔女士聽了這番話,再沒有説什麼。
就這樣,我準備半年多後,將《季羨林傳》的提綱,找了一個下午,到季老家,念給季老聽,季老將濟南一中改為濟南高中,要求我寫作時“實事求是,不要溢美”。隨後,我執筆書寫,終於在1998年初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季羨林傳》出版以後,?版社準備在北大舉辦一次活動,為書作宣傳,想邀請季老出席。季老堅決不同意,説:“我肯定不去,老師和學生互相吹捧,像什麼話!”季老沒有評價這本書,但他去臺灣學術訪問時,帶去了20本《季羨林傳》作為禮物,送給朋友。
這之後,我和季老的交往就越來越多。
我得以在季老晚年的最後十個月裏,幾乎每隔幾天都在他身邊,聽取他的教誨,記錄他的人生經歷。這是季老給我的榮譽和信任。
可以説,40多年以來我和季老的交往真正屬於那種淡如水的。當然,季老對山東的感情太深,對我厚愛有加。對別人、尤其是老鄉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他經常應邀為別人題字,而題得最多的就是“愛國、孝親、尊師、重友”,這八個字,他題了不下百遍。
很多人關心季老的口述歷史,我深知責任重大,再非常慎重地整理,還要一些時日。但是很多朋友急於了解季老口述歷史的內容,於是我取材于季老在這十個月裏的口述,從中選取了一部分內容預先出版,以滿足急於了解季老口述歷史的讀者需要。
《胡適口述自傳》的作者唐德剛,借用朱熹之言:記人言語最難,不得其意,則往往以己意出之,以説明口述歷史的局限。唐德剛也不敢保證,自己絕對沒有“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為一?口述歷史,往往都是如此的。他提到,甚至古聖先哲,亦所難免。《禮記�檀弓篇》裏,就有一段孔門弟子,誤記“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胡適口述自傳》,北京華文出版社1992年,第7—8頁)我想眼前的這本與口述歷史有關的書,也難免這種情況。如果有罪我者,我當然不會感到驚奇,而且我也會虛心聽取罪我者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