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無悔:我的“右派”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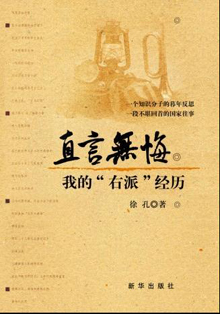
小組會主要是要大家揭發問題,發言並不踴躍,揭出來的也都是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問題,因為沒有什麼有根有據的重要問題,會場的情緒並不熱烈。不料,小組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出現了爆炸式的場面。
“爆炸”是由電影隊一個年輕隊員小馬的發言引起的。小馬揭發張山背地裏講丁主任的壞話,説聽丁主任作報告是活受罪,盡説車轱轆話,反反覆復、啰哩啰嗦,簡直是對聽報告的一種精神懲罰。
其實,政治部一些年輕幹部背地裏議論領導——包括丁萊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點的人,並非稀有現象,而且小馬揭發張山的問題,在肅反運動中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不料,坐在張山旁邊的韓部長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記錄本往桌子上一摔,紅頭漲臉地衝小馬,説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徐逸人成心破壞領導和幹部的關係。
韓部長這爆髮式的一聲吼,揭發張山問題卻沒來由的給原來的副部長徐逸人扣上一頂反革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時都怔住了。過了一會兒,就有幾個曾對徐逸人有意見的人,紛紛揭發“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諸如:徐逸人態度粗暴,給他彙報工作的時候,動不動就吹鬍子瞪眼睛、拍桌子;幾次找文工團女團員打麻將,影響惡劣等等,雖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風問題,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動的高度。
韓部長這爆髮式的一聲吼,雖然師出無名,但引導效果是明顯的,我越想越覺得情況不正常。小馬在會上揭發張山的不過是背地裏議論領導的“怪話”,韓部長為什麼發那麼大的火,而且把槍口轉向了徐逸人?是為了保護張山免受群眾的衝擊?不是沒有可能,張山一直是韓部長跟前的“紅人”。張山這人我了解,他並非沒有主見、人云亦云的人。他對韓部長的領導也有很多意見,而且語言尖刻,在下邊講韓部長的怪話比別人還“精彩”。但在韓部長面前絕對是謙恭的,韓部長向他佈置工作時,儘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從不提出異議,總是嚴肅地虔誠點著頭,好像他已完全領會,並將堅決執行。所以韓部長一直把張山看成聽話的、得力的幹部。為了保護張山及時轉移群眾的“火力”,不是沒有可能。問題是,為什麼把槍口轉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麼大的帽子?。
徐逸人這個人,在副部長當中比較年輕,恃才傲物,對上對下的關係都不大好,尤其是對上,比如與丁萊夫副主任時常發生碰撞。但像韓部長那樣的老同志總應該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敵人,這頂帽子是不能隨便扣的。特別是作為運動的領導人,更不能無根據地給人亂扣帽子,否則,就容易形成對運動的誤導。韓部長那一聲吼以後,不少人跟著“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長,“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亂喊叫,明顯地是走火了。
當時我是政治部黨支部的宣傳委員,覺得應該向韓部長把自己的看法提出來。我一想到給韓部長提意見,心裏又有些發怵。雖然韓部長來到宣傳部的時間不長,但不多的幾次接觸和過去在韓部長身邊工作的人所説的情況,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韓部長這個人對上、對下是兩副面孔。我這個人説話作事一向直來直去,最怕和這種人打交道,可按組織程式,反映對宣傳部運動情況的意見又不能繞過韓部長。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見,還是要説。
晚飯以後,酷暑難消。韓部長拿著一把蒲扇,坐在宣傳部辦公室旁邊一棵大樹下乘涼。宣傳部辦公室正在我住所的對面。我來到韓部長身邊,説:“部長,我想對今天的小組會提點意見。”
韓部長冷冷地看著我:“你有什麼意見?”
我説:“運動剛剛開始,如果沒有什麼證據就説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當,特別是你作為運動的領導人,首先給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適,容易對運動産生誤導。”
韓部長的臉色突然變了,厲聲問我和徐逸人是什麼關係。
我也火了,反問:“你是部長,你説我和徐逸人是什麼關係?”
他又問我為什麼替徐逸人講話。
我説:“我不是替徐逸人講話,我沒有這個想法,也沒有這個必要。我是對你和幾個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提意見。這次運動是肅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關係和工作、作風問題混淆成敵我問題。”
韓部長説現在還沒有給徐逸人做結論,還沒有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
我説:“韓部長,你和幾個人喊出來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沒做結論,為什麼給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韓部長反問我,徐逸人的言行是革命的嗎?
我説:“是否反革命分子是個組織問題,必須有證據,單憑今天大家揭發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風問題,能給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嗎?”
韓部長語塞,狠狠地一揮蒲扇,讓我不用管運動中的事,還讓我好好想想,準備交待自己的問題。和我預感的一樣,這次説話不歡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