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沈從文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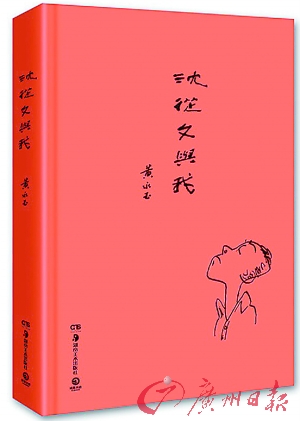
13
黃永玉 著
湖南美術出版社
新書摘
內容簡介
世上能讓黃永玉心悅誠服的人並不多,在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中,沈從文無疑排在最前面。在黃永玉的生活中,表叔一直佔據著頗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時間裏,他們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來、傾談、影響。他欽佩表叔精神層面的堅韌,欣賞表叔那種從容不迫的人生姿態。親情、故鄉、身份……多種因素使得他們兩人交談頗深,哪怕在艱難日子裏,往來也一直延續著。
沈九娘
聽我的母親説,我小的時候,沈家九娘時時抱我。以後我稍大的時候,經常看得到她跟姑婆、從文表叔諸人在北京照的相片。她大眼睛像姑婆,嘴像從文表叔,一頭好看的長頭髮。那時候時興這種蓋著半邊臉的長髮,像躲在門背後露半邊臉看人。我覺得她真美。右手臂夾著一兩部精裝書站在湖邊尤其好看。
我小時候,姑婆租了大橋頭靠裏的朱家巷有石板天井的住處。常陪姑婆聊天的有兩個,一個是我爸爸,一個是聶姑婆她妹妹的兒子,外號叫“聶胖子”的,也是我爸爸的表弟。
九娘那時候不在,她一定是跟著從文表叔已經在北京大學了。九娘在北京跟表叔住了好些年。很難説當時由誰照顧誰。料理生活,好像都不在行。從文表叔對飲食不在乎,能入口的東西大概都咽得下去。而九娘呢?一個鳳凰妹仔,山野性格,耐著性子為哥哥做點家務是難以想像的,只好經常上法國麵包房。
她當時自然是泡在哥哥的生活圈子裏,教授、作家、文學青年、大學生、報社編輯、記者、出版家川流不息。她認真和不認真地讀了一些書,跳躍式地吸收從家中來往的人中獲得的系統不一的知識和立場不一的思想。她也寫了不少的散文和短篇小説。一時有所悟,一時又有所失,困擾在一種奇特的美麗的不安中。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九娘的性格,只是運氣好,加上是個男人,有幸得以逃脫失落感的擺布。
她一天天地長大,成熟,有愛,卻又無所依歸。如《風塵三俠》中之紅拂,令人失之迷茫。有的青年為她帶著幽怨的深情遠遠地走了,難得有消息來往;有的出了國,倒是經常捎來輕浮而得意的口信。她抓住的少,失落的多。
這時,從文表叔結婚了。一個朝夕相處的哥哥身邊忽然加入了一個比自己更親近的女人,相當長期的生活突然名正言順地起了質的變化,沒有任何適當而及時的、有分量的情感來填補這迫切的空白。女孩子情感上的災難是多方面的。
我完全不能理解年輕的表嬸在新的家庭裏如何對付這兩個同一來源而性格完全不同的山裏人。表嬸那麼文靜。做表侄兒的我已經六十多歲的人了,幾十年來只聽見她用C調的女聲説話,著急的時候也只是降D調,沒見她用常人的G大調或A調、B調的嗓門生過氣。我不免懷疑,她究竟這一輩子生過氣沒有?於是在日常生活中就細心地觀察體會,在令她生氣的某種情況下,她是如何“冷處理”的,可惜連這種機會也沒有。這並非忍耐和涵養功夫,而是多种家庭因素培養出來的德行和教養,是幾代人形成的習慣。她一跨進沈家門檻就要接受那麼嚴峻的挑戰,真替她捏一把事後諸葛亮的汗。
抗戰使九娘和往昔的生活越離越遠,新的動蕩增加了她的恐懼和不安。巴魯三表叔正在浴血的前線,姑婆和姑公都已不在人間,雲麓大表叔是一位不從事藝術創造的藝術家型的人,往往自顧不暇。當發現九娘的精神越來越不正常的時候,送她回湘西倒成為較好的辦法。
九娘從昆明回到湘西的沅陵。他們兄弟在沅陵的江邊以“蕓廬”命名蓋了一座房子。沅陵離故鄉鳳凰百餘公里,是湘西一帶的大城之一。亂離的生活中,我的父母帶著除我以外的四個孩子都在沅陵謀生。當然,“蕓廬”自然而然地成為親戚活動的中心。巴魯表叔那時正從第一個激烈的回合中重傷回來,也住在沅陵養傷。眼見送回來的是一個精神失常的妹妹,不禁拔出槍來要找從文二表叔算賬。他是個軍人,也有縝密思考的經驗,但妹妹的現狀觸動了他最原始的情感。妹妹呆滯的眼神、失常的喜樂、不得體的語言是一種極複雜的社會化學結構。有一本名叫《精神病學原理》的厚厚的大書第一句就説:“作為社會的人,每一個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精神病。”像社會發展和歷史可以觸發出“天才”一樣,也産生著精神病患者。事實上天才和精神病者之間,只不過隔著一層薄薄的病歷。每一個人只要冷靜想一想都能明白九娘精神分裂的社會和生理緣由。巴魯表叔從此也沉默起來,不久又奔赴江西前線去了。
九娘的病在偏僻的山城很難找到合適藥物。抗戰的沸騰令她時常上街閒蕩,結果是身後跟著一大群看熱鬧的閒人。雲麓大表叔和我的弟弟擔當了全城尋找九娘的任務。直到有一天,九娘真的應驗了從文表叔《邊城》的末一句“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不回來”的讖言,我們從此再也沒有見到九娘。在沅水的上游有一個遙遠的小村,名叫“烏宿”,河灘上用石頭架著一隻破船。九娘跟一個破了産改行燒瓦的划船漢住在一起已經很多年了,生的兒子已經長大。
多少年來,在從文表叔面前,我從來不提巴魯表叔和九娘的事,也從不讓從文表叔發現我清楚這些底細。從文表叔仿佛從未有過弟弟妹妹。他內心承受的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所寫出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悲劇性。他不提,我們也不敢提;眼見他捏著三個燒紅的故事,哼也不哼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