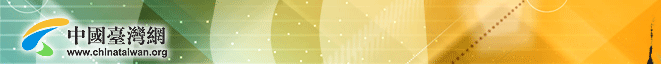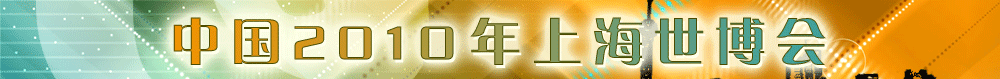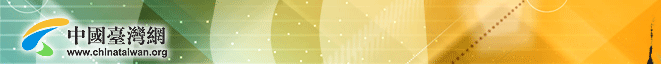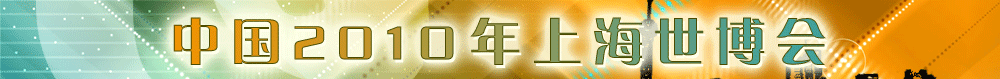世博會——世界博覽會,中國人在19世紀末上世紀初曾經叫做“炫奇會”、“賽奇會”,後來叫做“萬國博覽會”;世博會最早出現在歐洲,現在人們公認的首屆世博會是1851年5月1日的英國倫敦博覽會,當時在海德公園有10多公頃面積25國參加600萬遊客。不過若往前追朔,早在1756年英國藝術學會就在倫敦舉辦過農業機械展覽會,1798年和1802年法國也在巴黎舉辦過藝術品和製造品展覽會,此後歐洲漸開展覽會和博覽會的風氣。
自那以後,雖然世界歷經了多次戰爭災難,但是從總體上看,仍然呈現出各大國競相爭辦,參展國數量、人次、投入資金和規模面積都不斷擴大的趨勢。一百五十年來,全世界一共舉辦了58次世博會,1798年的拿破侖法國,1893年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400週年的芝加哥萬國博覽會,1900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以美國舉辦次數最多,1939年紐約世博會的面積最大,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的投入資金最多規模最大。
歷屆世博會上,從早期的打字機、火車、無線電、縫紉機、汽車到電視機和電腦,諸如埃菲爾鐵塔、亞歷山大三世橋等等,無不一次次地引起世界性的轟動,無不成為科學技術先進生産力的展臺,無不成為社會經濟、科技文化和建築景觀等等的時代標誌,無不成為推動世界尤其主辦國社會經濟的強心劑。世博會打破自然障礙和人為樊籬,克服民族種族和宗教信仰的界限,成為全人類的和平友好盛會。
徐德瓊、王韜和李圭三名商人——中國人第一次走進“賽奇會”
一直到不久前,我們還以為第一個有幸參觀“炫奇會”的中國人是清末洋務運動著名的的先驅者王韜。當年逃亡海外負罪在身的他因禍得福週游世界,在法國適逢186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不過這一切他只是個人遊客身份。
曾經也有人錯以為中國第一次參加世博會是1873年的維也納博覽會。時任清政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派了一個名叫包臘(E.C.Bowra)的英國人代表參會。不過很顯然,因為包臘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清政府所派遣,所以他並不具備作為中國參會代表的資格。
我們還曾認為是一個名叫李圭的清朝商人,第一個作為正式代表參加了世博會。可是,最近上海“世博網”發佈的一條驚人的消息,刷新了這個紀錄:去年一個叫徐潤的市民報告他的祖先曾經參加過倫敦第一屆世博會,並獲得了金、銀大獎。於是,上海申博辦在茫茫的清史資料中尋找佐證。終於,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中心的張偉等人從徐姓家譜中找到了這位名叫徐德瓊的買辦在1851年把湖州絲綢送到英國世博會上參展並獲金獎的記錄,從英國皇家協會1852年出版的《英國倫敦第一屆世博會評獎委員會報告書》上查到了相關的記載:來自上海的榮記湖絲得到好評,評獎委員會決定授予獎牌。徐德瓊(1822-1873年),名瑞珩,號榮村,廣東香山人,是上海開埠後第一批來滬闖蕩的廣東商人。1851年,他以自己經營的中國特産“榮記湖絲”參加在倫敦的首屆世博會,引起重視,一舉摘得維多利亞女王頒發的金、銀獎牌各一枚。
雖然如此,雖然中國人走進世博會的歷史隨著不斷地發掘還會更加地豐富,但李圭畢竟是最早帶著中國展品走進世博會並留下歷史足跡的人之一:那是在1876年舉辦的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來自中國江蘇的李圭參賽並親歷了盛會。那次博覽會的主題是慶祝美國建國一百週年,在以後的很長時間裏都是規模最大的一屆盛會。李圭的更具價值的貢獻還表現在回來後寫了一本名叫《環遊地球新錄》的書,其中記道:“中國赴會之物,計七百二十箱,值銀約二十萬兩。陳地之地,小于日本,頗不敷用。此非會與地不均,蓋我原定僅八千正方尺,初不意來物若是多也。”原來遠涉重洋運去的展品,大大超過了預期數量,結果連原計劃的展場都不夠用了。
李圭作為清朝工商業界代表,是由北洋大臣李鴻章派遣的,所以李大人還專為這本書作了序:“大清光緒紀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為美利堅立國百年之期美人設會院于費裏地費城,廣集各國珍玩古器,日用服飾生潛動植物諸賽奇公會將欲考究物産修好睦鄰蓋倣歐洲賽會而紉為是舉也江寧李圭以東海關稅務司德君璀琳國家者甚遠且大又豈僅一名一物為足互資考鏡也哉……”
這篇短序雖然寫得簡單,但是對於世博會的內容意義,概括得還是可以。想李圭一介商賈的文字,居然能夠得到當朝重臣的親筆題序,或許也體現了當年洋務大臣對於世博會的理解和重視吧。
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中國人的世紀留影
據説1900年清政府曾經派員參與過巴黎萬國博覽會,但是沒有能夠真正參展。那一年戊戌剛過,先是義和團接著八國聯軍入侵,連慈禧太后也逃亡西遷;朝將不朝國將不國,國難民窮那裏有閒錢那裏顧得了遠赴法國的事情!
到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城萬國博覽會時,正值戊戌風雲與辛亥革命之間的相對平靜時期,慈禧渡過難關被迫實行新政,打開大門面向世界的機會使清政府參加聖路易萬國博覽會成為可能。據載: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十二月七日派溥倫為赴美國散魯伊城(作者注:即聖路易斯城)博覽會正監督。”“一九零四年(光緒三十年甲辰):四月二十五日派駐比使臣楊兆前往黎業斯(作者注:即聖路易斯Liegt)萬國賽會。派駐英使臣張德彝將萬國紅十字會原約劃押。四月二十六日,貝子溥倫覲見美國總統。”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國際博覽會”條目中有一句話的簡單介紹:“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博覽會是1904年聖路易國際博覽會,在會場上展出了北京頤和園的模型。”
清末的太上皇慈禧也與這屆博覽會有過某種關係,在《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晚清宮廷》書中記過:“當有人第一次提議為她畫像並送往聖路易期博覽會時,慈禧太后十分驚訝。康格夫人向她做了好一番遊説,説歐洲各國首腦的畫像都在那兒展出,其中包括大英帝國維多利亞的畫像,還説如果慈禧太后的畫像大量在海外流傳,也有利於糾正外人對她的錯誤印象。經過康格夫人的這一番勸説,慈禧太后才答應和慶親王商量商量再説。此事好象就到此擱淺了。但很快她就派人傳話給康格夫人,説她準備邀請卡爾小姐進京為她畫像。”這幾句話,大概是慈禧太后直接與萬國博覽會有關的唯一的歷史記載了。
溥倫(1869—1927),字順齋,滿族鑲紅旗人,1896年任鑲黃族副都統,1907年後歷任北京崇文門監督,資政院總裁、農工商大臣,參與政務大臣。民國後曾任北京大總統府政治顧問,1915年任過北京政府參政院院長,1927年58歲時早逝。雖然後人的評論都説溥倫的能力和政績非常平庸,但是他的時運卻是非常的幸運,以皇室貴胄的身份中國近代史上的一系列機遇送給了他面前,還註定要在世博史甚至奧運史上佔據一頁——可嘆這位早逝的清國的最後一任大臣,當他鬱悶不樂地看著傾倒的皇朝和失去的一切時,或許想像不到也理解不了曾經的世博會對後世具有多大的意義
但是中國人這次遠涉重洋到美國參展,還是在國內外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展品也獲過獎;清末開辦的著名的啟新洋灰公司的馬牌洋灰(注:就是現在的水泥)就獲得了賽會的頭等金獎。可惜今天已經很難找到國人記載中國參加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文字,僅看到的一點也多是失望、批評和責難,幾乎是完全之否定,更難找到讚美的文字。可見非怪溥倫非怪時代,是耶非耶,毀耶譽耶?
百年過去時至今天,那次參賽的影響和成績如何?倒真叫人很費思索,是非功過該作如何評説?今天站得更遠更高一些,我們能否比以前看得更清楚,包括裏面非常有趣的問題┅┅
貝勒爺的皇室克隆——野史裏的清國參會
正史的記載太過簡單,可能因為那是朝廷的態度;而野史的述説生動豐富,恐怕是代表了世俗和輿論。讓我們看一看其中一則“記聖路易賽會副監督”:“某京卿者,中國最初出洋遊學生中之傑出才也。雖無專門學問,亦未受卒業文憑,而于儕輩中,當時固已首屈一指……復拜使命,為美國賽會副監督。於是創議于會場特建中國宮室,糜物至四十五萬金。既成,視之,非宮非殿,非廟非衙,殊不能名其狀。且以卑小之室,置諸各國崇樓宏宇間,”
關於這篇野史點名的“副監督”姓甚名誰,姑且就事論事不去説他。倒是那座引發責難的“廢物至四十五萬元”的“于會場特建中國宮室”是個什麼樣子?實在是令人好奇。
據查:關於賽會上的清國館,世博會設計者的要求是在裏面佈置一套清王朝的皇室內宅。這真是個説容易很容易,説難又非常困難的題目。因為從建築技術看,這只算小菜一碟,實在不成問題。但是王朝的深宮內廷從來是不能向外人更別説向外國人展示的,那一處敢拿出去?這就實在是非同小可太不好辦。再説還要遠隔重洋橫跨千山萬水,委實是難之又難了!
溥倫苦思冥想所採納的辦法,是在清國館裏完全照樣複製了一套自己家的客廳和臥室,也算是非常的聰明。就這樣世博會第一次破天荒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皇家內宅,留下了一則貝勒爺居室的克隆故事。
當時就有英文報章興奮地向世界報道:溥倫王子住室的華麗的複製品位於英國和比利時展區之間。斜峭的屋頂四角向上翹起,燦爛的色彩是博覽會上東方建築的漂亮樣品┅┅用中國龍、神和英雄的圖案裝飾┅┅中國住宅和寺廟模型非常有意義,這些是在中國分塊製造的┅┅在萬國博覽會上,中國皇室的展品是溥倫王子住所的複製品。在寢室中間放著一個開啟的寶亭,有一座寶塔,還有插著百合、牡丹和玟瑰的金魚池;王子的寢床、客廳和畫室,到處是世界最高雅的刺繡極品,中國的地毯製造藝術就是在地板上也能看到——建築物在紅色、金色和蘭色中集中地裝飾出華麗,同樣的奢華在花園中也表現出來,那後花園是由專員夫人(指溥倫夫人)親自設計的。”
雖然當年沒有記錄電影,沒有電視轉播之類;不過幸而已有攝影照相,留下了當年拍攝的珍貴歷史鏡頭,可供後人鑒賞。從博覽會的展區大照片中可以看到,門前裁著兩根中國式旗幡的牌坊裏面正是清國館,就是野史説的那座“非宮非殿,非廟非衙”;看上去,它的確既不像宮也不像殿,既不是廟也不是衙。雖然從建築體量看,與其他一些西方大國甚至日本館比,面積規模確實是小了一些┅┅
但是,從照片也清楚看到:清國館的總體佈置和形象並不難看,甚至可以説很有中國特色非常高雅;牌樓宮殿的輝煌結合了江南庭院的典雅,讓人一覽之下就能聯想到特有的皇權、宗教、政治和文化;借方寸天地,營構如臨其境的效果,或許倒是它的成功之處。當時把清國館設計成這樣,不論設計者是誰是中國人或是外國人,恐怕最基本的出發點都是樹立一座代表當時中國的綜合形象;如此來看,也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清國館本就不是宮殿廟衙,當然就該是“非宮非殿,非廟非衙”,其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相比近些年的許多現代建築,我們能夠發現到某種雷同之處;遺憾的是,我們花了多少年走了多少路,才終於意識到自己的傳統和特色。我們似乎更應該感謝百年前的那位建築師,或許會覺得那野史所代表的思想是不是太狹隘太封建,太大驚小怪了?
“人類學日”是耶?非耶?——中國戲劇第一次走向世界?
上面野史所説畢竟只是一國之事,其實對於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評價,還真有一樁公案,招致了各方面的公憤,並且沿習至今——那就是博覽會組織的“文化人類學日”展覽和比賽:比如讓非洲黑人、印第安人、菲律賓人、阿伊努人、土耳其人和敘利亞人表演、比賽爬竿等等——這屆博覽會從此擔上了種族污染的千古罪名。
奇巧的是,清末的另一則野史“中國赴聖路易賽品”竟也與此不謀而合:“聖路易賽會,中國政府館之卑陋,既如前所述。而最足以章吾國恥者,則赴賽物品是焉。茲錄其尤甚者如左:煙槍十余技,煙燈數枚,滿面煙容之官員一。殺人刀數柄,殺人小照數方,雛形知縣署一。各種酷刑俱備,枷一。上海、北京、廣東、寧波裝小足婦人各一。小木人數百枚,乞丐、煙鬼、囚犯、苦工、娼妓之類。小草屋十余間。苗蠻七,綠營兵一。翰林、進土、舉人、秀才各一,均高四尺以上,背駝面目枯瘠。奎星樓一,小城隍廟一,城隍鬼判俱備。教會學校照片數十方,藥王財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嗚呼!政府糜數百萬鉅款,而所徵出品,乃悉為卑陋劣粗之物件,或代表陋俗迷信之具。是非赴賽,直白求辱耳!論者所乙太息痛恨于承辦官吏之毫無心肝也。”
野史的作者在痛數清國館建築的“卑陋”之餘,列數清國展品的粗俗:除卻煙槍、刑具、小腳婦人、苦役、乞丐和娼妓等等以外,甚至連知縣衙門、奎星樓和城隍廟的模型都搬了去,完全展示的是野蠻和落後,簡直是自取其辱,毫無心肝!
在我們的歷史常識中,腐朽的清王朝常常做出喪權辱國的事情,本在我們印象之中。應當承認,對人本身的研究,在過去很長時間裏除了醫學和宗教之外,還有所謂的人種學人類學。而且過去的人種學,多是在堂皇的外衣下隱藏著大欺小、強淩弱、反人道和邪惡,甚至成為種族滅絕的理由和藉口,成為宣揚種族優劣論和種族歧視的幌子。
但是讓人奇怪的是,單就清國館而論,國外的看法與國人的責難竟絕然不同,看法之懸殊令人吃驚!英文報道説:中國鎮是中國商會提供的一個有吸引力的地方。這兒有一個擁有本土演員的中國劇場,一座寺廟,講解員會為您解釋宗教儀式和符號的意義。一個茶室裏有本土來的侍者,還有一個集市,聚集著本土來的商人、木匠、畫家和油漆匠。這兒有絲綢織工和象牙雕師展示著手藝,在劇場裏從北京來的男演員表演具有高超技巧的藝術,使遊客能夠理解了除了語言以外所有的內容。館裏的花園優美得使西方情趣感到陌生┅┅中國鎮是用表演使遊客高興和滿意的臨時的家。讚美之詞溢於言表——並且很可能成為中國戲劇(最可能是京劇)第一次走向世界的最早的證據!
時過境遷,人們認識可能冷靜一些:早期的人類學研究劃分得並非那麼清楚,經常是與社會學、民俗學或文化史牽扯在一起的。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上的“文化人類學”的展覽和比賽,並沒有直接與早期的人種學挂勾,也是人類的一份民俗遺産,很多都可以説是民族民俗文化,屬於社會學、民俗學和文化研究的對象,正是極其需要保存和保護下來的。
大約百年過去,當我們正在彌補著這方面欠缺的時候,才意識到當年的文化人類學展覽或許也保存和保護了世界的文化史,或許也有它積極的一面——當然這是需要假以時日,只有在整個世界的文化生活水準提高後,才能遂漸地認識到的……
聖路易斯萬博會與奧運會——是中國最早參加的奧運會嗎?
在北京申奧的日子裏,挖掘我們歷史上與奧運會的關係也是一項重大的課題,其中頭一個令人特別關注的問題,可以説就是中國最早參加奧運會的問題。最早參加的奧運會是那一屆的人是誰?
目前已經得到共識的是:1896年在雅典舉行的首屆奧運會曾經向清國發出過邀請,但是清王朝當時不清楚“奧運會”是什麼意思,沒有積極響應“未予回復”,沒有能夠派出政府代表參加。後來,中國政府與奧運會的正式官方接觸,最早是在1921年的上海第5屆遠東運動會上,當時國際奧會委派過日本的奧委委員代表致詞;直到“1928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第9屆奧運會上,中國政府才首次派出了觀察員。”
但是當我們研究了世博會的歷史後,可能需要修改上述看法。原因在於:歷史上的第二和第三屆奧運會曾經是與世博會聯繫在一起的,並且是世博會的附屬項目。試想草創期的奧運會如同初生的嬰兒,比世博會晚了約50年,不可能一誕生就如後來就如今天這麼風光;作為一項純粹的體育比賽,當初的影響遠遠不及世博會。所以初生的奧運會借助世博會的影響來發展,也是一個良策。
顧拜旦在1894年的巴黎國際體育會議上,就建議首屆奧運會與世界博覽會同時在巴黎舉行,藉以擴大奧運會的影響,當時這種意見遭到了否決。後來鋻於顧拜旦為復活奧林匹克運動所作的貢獻,奧委會代表決定尊重他的意見,決定1900年奧運會既第二屆奧運會與世界博覽會同時在巴黎舉行。
儘管顧拜旦和奧委會委員們不情願,後來也不滿意。但是因為幼小的奧運會尚不能獨立;第二屆奧運會是作為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的附屬項目,第三屆奧運會隨之成為1904年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的附屬項目,這是無法回避的客觀的事實。
按照以下最簡單的理由和邏輯:一個國家或政府委派的出席世博會的代表自然也是該世博會下屬各個項目的代表。一個國家只要是派出了參會代表,不論其有沒有運動員參加比賽,也認為是參加了奧運大家庭的盛會。
那麼,溥倫作為清政府委派的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的正式代表,當然是同時舉辦的第三屆奧運會的代表。何況他作為一國之代表率領著一個不算太小的代表團(因為遠隔重洋交通不便,還有許多國家甚至沒有派人參加)會見過美國總統,逗留了很長時間;從道理上講,也不可能不參與奧運會的活動,不觀看同在一城舉行的奧運會吧。
據説,利用世博會擴大奧運會影響的計劃並不如願。主辦方對新生的奧運會小弟弟還不屑于顧。顧拜旦在日記裏對第二屆巴黎奧運會抱怨道:“世界上有一個對奧運會非常冷淡的地方,這就是巴黎。”掩飾不了心中的失望。或許可以猜測:這可能就是他作為主席竟然沒有去美國參加聖路易斯第三屆奧運會的真正原因。
那一年,雖然聖路易斯城為了世博會竟把慶祝開市一百週年的活動推遲一年到1904年,奧運會還隨同世博會,延續了5個多月,為的是讓博覽會和奧運會相映生輝全城狂歡。
聖路易斯奧運會與上屆巴黎奧運會一樣,人們的興趣主要集中於世博會,奧運會比賽場地和運動設施等等都非常簡陋,奧運會也受到博覽會的衝擊成了陪襯。尤其遺憾的是,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和國際奧會主席顧拜旦竟然都未出席開幕式。這一切預示著,日後奧運會與世博會的分道揚鏢是不可避免的了。
目前,中國的有關部門還在挖掘和考查中國參加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歷史材料,看來接著應該著重瞄準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暨奧運會。1900年和1904年兩者必具其一,如果找不到參加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暨奧運會的證據,那麼中國最早參加奧運會的記錄或許就能夠確認:是幸運的溥倫作為正式代表參加了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 (文/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