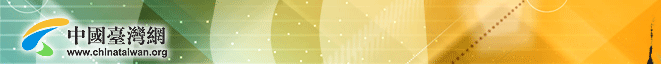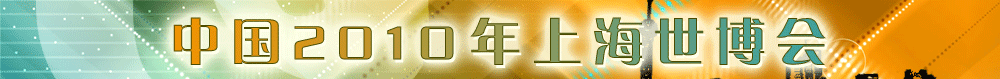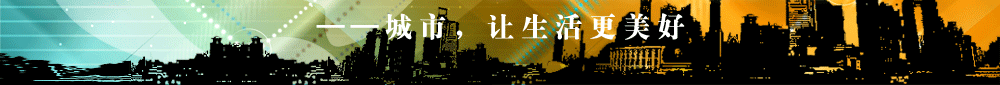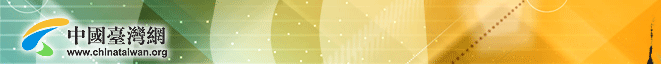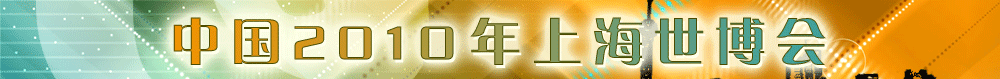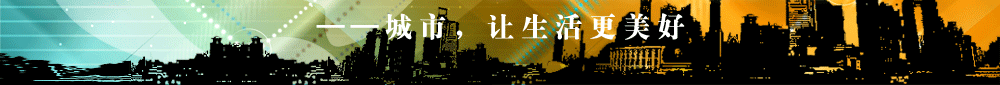世博被上海寄予厚望,被視為上海進行産業轉型的一次重要契機。
編者按:
還有不到一週的時間,為期184天的世博會將落下帷幕,精美的場館將被拆除,蜂擁的遊人也將散去。當繁華歸於平靜,對於世博效應的追問顯得尤為急迫:世博為上海帶來了什麼?“後世博”時代的上海將向何處去?這是上海不能不冷靜面對的問題。
毫無疑問,世博概念為上海帶了龐大的投資,拉動了上海的經濟增長。世博會舉辦期間,超歷史的人流量,也為上海及周邊城市帶來了極大的經濟附加效應。
然而,世博之於上海,意義終究不止於此。在諸多觀察人士看來,這場世界經濟、科技和文化領域的“奧林匹克”盛宴,對於當前的上海,更多的是一次城市發展轉型的契機,世博後的上海,經濟結構,以及與之相應的城市空間規劃、城市治理、政府行為都將進入調整期。接下來的問題是,上海能不能把握這個機會,利用“世博遺産”完成自身的飛躍?
本報記者 王玨磊 實習生 趙淑菊 發自上海
隨著世博步入尾聲,對後世博的思索與討論日趨熱烈與成熟。在上海社會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躬逢世博之盛,一如注入了一劑有力的催化劑。世博不僅讓上海嘗到了“軟經濟”的甜頭,甚至可視為城市發展的一個轉捩點。
世博是一個轉捩點
“上海到了一個新的轉型期。”不久前,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上海市長韓正開門見山。
在高速發展了20年後,在6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將近2200萬人的上海,傳統的增長模式,即高速城市化、工業化、要素集聚化的發展道路已難以為繼,上海面臨迫切的轉型需求。
在此過程中,世博被上海寄予厚望,被視為上海進行産業轉型的一次重要契機,在城市功能、定位以及發展理念的轉變過程中,世博也被認為提供了不小的借鑒空間,“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題語顯得內涵深遠。
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眼裏,世博就是一個轉捩點,“世博之後,上海的投資速度應該是會明顯地緩慢下來,發展的重點可能要從靈感中去尋找,而不是從汗水中去尋找。”
“現在到了對世博作進一步沉澱、消化的時候了。”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專家、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建文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原來在世博會前期準備時,對世博會可能對上海産生的影響,我們寄予的希望比較大。比如各國都把它最先進的東西拿來展示,這能否轉變為我們自己的東西。但到目前為止,能夠落地的東西不多,跟原來的期望還是有差距的。因此,在世博結束後,怎樣消化人家的東西,同時結合我們自身的情況,作進一步的思路、技術和工業層面的創新,還要補課。”
世博會的超大客流,對上海服務業的助力也毋庸置疑。據上海財經大學世博經濟研究院分析,上海零售業是世博最大的受益者,世博“貢獻”達175億元。此外,餐飲業、娛樂業、酒店業分列受世博輻射行業的2-4位。
“從整體的産業發展和經濟發展角度來講,怎樣把世博對服務業的促進效益進一步放大,落實,要認真考慮。”楊建文説。
體制的變化,可能是世博不那麼顯眼的“軟效應”。復旦大學企業研究所所長張暉明説:“世博在提升産業發展之外,從體制上、管理水準、服務水準、做事的標準上也有推動。值得思考的是,世博會很多事情都是開綠燈的。這個綠燈能不能一直開下去呢?”
轉型是“十二五”關鍵詞
上海轉型的課題,討論並非一朝一夕,嘗試也並非始自今日。但在實際操作中,用張軍的話來説,“這麼多年來,也一直在痛苦地掙扎,一直在想怎麼樣能夠實現轉型。”
楊建文認為,“轉型”兩個字,將是貫穿于上海十二五規劃,乃至十三五規劃部分時期的重要關鍵詞。在他的理解中,上海未來的轉型,應堅持科技導向型、消費導向型、服務導向型和低碳導向型的方向。“四個導向互有聯繫,也要分輕重緩急,對這一點,現在還沒有形成思路清晰、部署完整的一整套考慮。”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讓經濟發展減速的背景下,“要抓緊把轉型的基本的東西做出來。”
所謂基本的東西,在楊建文看來,首先要有效地、整體地推進城市化進程,此外,便是要把準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方向。“戰略性新興産業關係到我們能不能在下一輪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但這並不意味著把所有新的東西都放進這個框裏,不要以為高新技術産業就是戰略性産業。”
10月10日,韓正在第22次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上指出,上海在未來3年預計將有1000多億元資金投入重點産業發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聚焦突破,重點發展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導産業,積極培育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先導産業,預計到2015年,上海戰略性新興産業産值規模實現翻番。據了解,戰略性新興産業産值規模實現翻一番,也是正在編制中的上海“十二五規劃”的內容之一。
大力推進高新技術産業化,也被認為是上海的經濟動力機制由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主要路徑。
“對於2015年戰略性新興産業産值規模翻一番這個目標,我們還是應該持樂觀的態度的。不過,我看最近有個機構搞了一個最具活力城市排名,上海還不是第一名。上海應當創造更好的環境來吸引人才。”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副會長奚潔人認為。
“由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這是規律,總體上是樂觀的。關鍵是對具體産業要作具體分析。比如説太陽能汽車,城區裏已經有多少輛在走了,車子的安全性、保養維護費用、運營中的成本回收等等問題,都要作具體分析。如果要達到一萬輛的規模才能活下去,那就想辦法達到一萬輛,政府應該做這個事情。”張暉明則建議。
借兩個中心建設提振服務業
産業結構的升級,無疑是轉型的首要含義。繼17年前上海實現産業結構由“輕”變“重”,由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産業為主導轉向以IT、汽車、裝備製造等高新技術産業、重化工業為主導以來,上海産業結構將實現再次升級,在更高層次上由“重”向“輕”回歸,發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
“立足上海實際,要把經濟轉型放在突出位置,以調結構、促轉型推動經濟發展。以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為依託,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以推進高新技術産業化為突破口,整體提高先進製造業能級和水準。”韓正市長曾表示。
所謂“現代服務業”,在楊建文的理解中,更多地與消費型服務業聯繫在一起。他解釋説,在之前二三十年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上海定位於發揮生産型服務功能,主要為企業、廠商提供服務。而在今後的中國經濟體系格局中,上海的生産型服務業還是要繼續發展,但服務業的主體應變為消費型服務業,這是上海現在應該抓緊做的事情,在全國要起到引領作用。
與提高製造業的能級與水準相比,服務業的提升堪為難點。事實上,上海向服務業轉型已作過多年嘗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即已致力於“退二進三”,然而,服務業的比重卻一直提振乏力,自2000年首次超過50%,達到50.2%之後,便連續多年在50%上下徘徊,2009年佔比為59.7%,而服務業佔比達到60%是邁入國際大都市行列的達標線。對此,張暉明認為:“發展服務業,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在市場結構、組織安排、需求培育等方面都要作出努力。”
上海國際航運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真虹則告訴記者:“服務業本身發展有規律性,營造服務業需要時間,需要環境的逐步積澱。”
不過上海在發展服務業方面的努力正在逐步顯現。自9月1日起,上海開始實行在負有營業稅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按差額方式確定計稅營業額,此舉大大減輕了服務業的稅負,破解了服務業發展的稅制約束。
兩個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無疑是上海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重要依託。“拿航運中心建設來説,在去年國務院19號文件和航運中心建設十二五規劃中,都把下一階段的重點任務放在航運服務業上,建立起航運服務的完整體系。這方面有大量的需求,有非常好的發展前景。”真虹説。
專家訪談:讓上海的經濟更“軟”一些
“上海應該從工業化的階段,轉向更軟的經濟,經濟越軟,生産力越高。”對於上海轉型的話題,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的觀點很鮮明。在他看來,借助世博契機,上海應該放下製造業的包袱,致力於服務業的發展,兩者並行不悖顯然不利於轉型的實現。
時代週報:世博會對上海的轉型有哪些促進作用?
張軍:從後世博這個角度講的話,這是一個服務的平臺,所以我覺得可以把“世博”理解為一個轉捩點,也許從此上海就告別了這種以製造業和大規模的投入建設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對服務業的發展是一個拉動。因為世博之後,上海的投資速度應該是會明顯地緩慢下來,發展的重點可能要從靈感中去尋找,而不是從汗水中去尋找。
我想普通老百姓對世博印象最深的可能不是各個場館,而是上海的天更藍了,空氣更好了,這其實對上海經濟的發展構成了一個挑戰。上海需要更藍的天,也就是説基建在經濟中的含量要大幅度地降低。基建降低之後,經濟從哪兒發展呢?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從靈感裏面找思路,利潤、附加值這些東西都是從靈感裏面來的。所以對上海來説,將來應該吸引更多的人才,這就需要創造更藍的天,更好的環境。有了人才,財富才能增加。
時代週報:您覺得上海今後的轉型還面臨哪些難題?
張軍:對上海來講,這麼多年來,其實一直在痛苦地掙扎,一直在想怎麼樣能夠實現轉型。我覺得世博之後,上海應該更輕鬆了,應該看到了轉型的甜頭,應該是更大膽地放下製造業的包袱,創造吸引人才的環境,人才來了,轉型自然就會完成。上海最大的挑戰是關於人才的挑戰,難題在於創造吸引人才的環境。
對上海來説,應該從工業化的階段轉向更軟的經濟,經濟越軟,生産力越高。
時代週報:服務業在上海的經濟結構中所佔的比重一直不是很高,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張軍:服務業不發達有很多原因,一方面跟我們的觀唸有關,認為價值是生産部門創造的,服務部門是消費的,不創造價值。城市也總認為要辦很多製造業,經濟才能發展,辦理髮、餐飲、洗浴這些東西就不創造價值。這種觀念現在有所改變了。另外,服務業不發達,和自身的稅負也有關係。很多高端的服務業,比如銀行、金融、保險、航運、物流等,如果稅負比較重的話,其中的中小企業就很難生存。上海有很多很小的物流公司,生存空間就很惡劣,主要就是營業稅太重。
時代週報: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是不是發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重要途徑?
張軍:我認為上海壓根就不應該繼續發展製造業,應該發展航運和金融。比如説汽車産業是先進製造業,發展航運和貿易是服務業,這兩個産業如果在一個城市並行發展,當然也可以,但既然提出經濟轉型,如果這兩者並行發展,怎麼實現轉型呢?不要説製造業是一個大的産業,捨不得丟棄,其實上海的汽車製造業並不掙錢,這是一個很大的包袱。一直背著這個包袱不放,還不如把它放下,去搞金融、航運這些東西。
世博叩響上海經濟轉型之門 服務經濟將唱主角
上海過去20年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基礎上的粗放型增長,是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出口帶動的外延式增長,是高增長低效益、高GDP增速低居民收入增速的不可持續增長。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暴露了這種增長模式的缺陷及對上海發展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