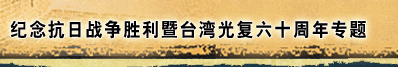我的朋友陳慶港在2004年的夏天和秋天,汗水淋漓風塵僕僕地奔走在中國的大地上,大海撈針般的一個個尋找倖存的慰安婦,竭力勸服她們説出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並鼓起勇氣面對他舉起的鏡頭。 我想我必須公開對他的工作表達足夠的尊敬,因為這些充滿震撼人心的力量的照片,不僅展示了一位優秀攝影師令人吃驚的才華,更重要的是它們記錄了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永遠不能忘卻的記憶。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那些曾經親身經歷戰爭的苦難和傷痛的人,在60多年的時光中,許多都已經悄然逝去。照片中這些歷史的見證者,也已經成為風燭殘年的老人,到了她們生命的最後時刻。就在這些照片刊登前,她們中已經有人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隨著時間的繼續流逝,她們一個個都將先後默默地離去,幸而有一個充滿良知和責任感的新聞攝影人,用自己的鏡頭和文字永遠留住了她們。
時間也許會消失,但是歷史不會消失。我無法想像,老人們在回憶那些夢魘般的往事時,攝影師陳慶港在尋訪和面對她們時,親歷者和記錄者,講述者和傾聽者,年長者與年輕者,內心究竟都翻滾過怎樣的激烈與掙扎、顫抖與疼痛、悲慟與憤怒。老人們在講述中與60多年前的歷史相遇,攝影師在記錄中與60多年前的歷史相遇,而我們在閱讀中與60多年前的歷史相遇。這不僅僅是這些老人們的歷史,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這不僅僅是這些老人曾經經歷的苦難和血淚,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曾經經歷的苦難和血淚。
這裡選用的照片,只是作者關於慰安婦調查拍攝的上千張照片中的一部分。這裡刊登的文字,只是作者關於慰安婦調查十數萬字採訪筆記中的一部分。這裡記錄的慰安婦倖存者,也只是當年所有飽受日軍摧殘的慰安婦中的極少一部分。而慰安婦們遭受的苦難和屈辱,更只是當年我們這個民族遭受的苦難和屈辱的極小一部分。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從一個民族對待歷史的態度中,可以看出這個民族的未來。我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不僅是紀念偉大的中華民族面對外來侵略者時不屈不撓的奮鬥與抗爭,同時還要牢記那些永遠不能忘卻的記憶,那些飽含血淚的記憶,那些充滿痛楚的記憶,那些歷經苦難的記憶,那些浸透屈辱和悲傷的記憶。
昨天是“七七事變”68週年,從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日軍隊在盧溝橋打響了全面抗戰第一槍,中國人民開始了8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編完這一期專題後,我不知不覺間已經淚水潸潸。
尋找
在當年橫遭日軍鐵蹄踐踏的城市,或者偏僻鄉村,尋找。直到今天,我依然無法説出這是怎樣的一次尋找,是對已然遠逝的歷史的某個鮮為人知的細節的擦拭?還是對正在行進的仍然無法終結的一份現實苦難的注目?在這綿長的尋找中,心裏一直揣著一份無法言説的巨大苦痛。從陽光明媚的海南,到山重水疊的雲南,再從黃天厚土的山西、河北,再到風輕雲淡的江蘇、浙江、上海……當我站在陰暗而又破敗的慰安所遺址裏,當我一步步邁進當年日軍精心營造的堅固而又陰森的炮樓裏,我似乎仍然能聽得到“慰安婦”當年悽慘的哭喊……一次又一次撩開被掩藏在內心最最深處的黑暗記憶,一次又一次將那些生動的名字去對應一撮撮冰涼的黃土……我努力將自己所能尋找到的歷史碎片慢慢拼合,60多年的歲月雖然沒能抹去那場劫難所有的印痕,但時間卻也削弱了那場劫難所應有的太多殘酷的色彩。
在三亞椰樹掩映的海濱大道旁,當年日軍的碉堡仍趴在白色的沙灘上。不時有遊人站到碉堡前留影,灰色的碉堡後面是高樓鱗次櫛比的三亞新城。就在三亞,還有海口,還有崖城,當年日軍“慰安所”的遺址,正一處處悄然消失在鱗次櫛比的樓群背影中。碉堡上黑洞洞的槍孔沉默地盯著陽光下的每一個人,耳邊只有海風吹拂椰林時的輕嘆,還有海浪撫摩沙灘時的低吟。
沒有太多炎熱和灼痛的感覺,那個漫長的夏季,給我的只有沉重而又陰晦的潮濕,濕漉漉的潮濕。渾身內外,晴天被汗水濕透,陰天則被汗水和雨水一起濕透。而在不停地奔走中,無論天的陰晴,我的心則總是浸透在一場巨大的潮濕中,一種苦澀的淚水般的潮濕中。這種濕漉漉的感受一直延續到秋天,甚至一直延續到冬季,還有這個春天。
其實從前一年的春天開始,我就在籌劃著這次採訪,對這次採訪的難度自認為有充分的準備,但一直到實施時,我才知道,這次採訪的難度和內容遠遠超過了我的想像。
在我沒有進行採訪之前,我一直以為自己對那段歷史了解得異常清楚,因為課本上我認真學過,影視片中我也都看過。而現在,我總是不停地在問自己,在我了解得異常清楚的關於那段歷史的年表和諸多名詞的背後,到底還隱藏了些什麼?除了熟知的那幾部影視片中煽情而又蒼白的一些場景外,對於那段歷史,我到底又知道了多少?
在日軍侵華期間,被逼迫成為日軍性奴隸的中國婦女達20萬。大部分慰安婦,在戰爭結束前就已遭日軍殺戮,或者被迫害而亡。而少數帶著羞辱和痛苦含恨活著的,在經過漫長而又動蕩的60多年的時光流逝後,其中又有大部分離世,今天仍然活著的已寥若晨星。而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受害人至死都恥于向人説出自己的那段悲慘經歷,那段歷史究竟還能有多少細節為我們留下來?有人説,對於痛苦的記憶,回顧一次,就等於重新經歷一次。這些背負著沉重悽愴的記憶活到今天的老人,都已是八十歲左右的高齡,面對她們,我常常不知道該怎樣開口,不知道該怎樣開口去問,去問那些總能讓她們肝腸寸斷的事情。真的,如果有可能,我願永遠不去叩碰那扇讓她們疼痛了一輩子的記憶之門……可我,不得不去叩碰……
“追思歷史,不是要讓人們永遠活在仇恨的邊緣。一個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終都不應成為人們思維的中心。”50多年前,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大法官梅汝敖先生説:“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導致未來的災禍。”
“慰安婦”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我用鏡頭記錄了數十位“慰安婦”的悲慘經歷,以及她們因為那段經歷而被改變了的現在的生活。這數十位老人的悲慘經歷,其實只是日軍侵華期間所有“慰安婦”的一個縮影,她們的苦難,實際上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苦難。而“慰安婦”代表的正是我們這個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難、最最血淚的那一頁。
那段歷史,是留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的一道傷痕。
“他們(日本政府)什麼時候能向我道歉?我還能等到那一天嗎?”在講述自己的苦難後,在用乾枯的雙手擦拭完眼角的淚水後,幾乎所有的老人都會拉著我的手這樣問。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她們,我也無法知道她們能否等到那一天,但我相信一定會有那一天!
在我寫這短文時,又來電話説有一位老人永遠離開了我們。我拿著話筒好長時間,不知該如何是好。
侯二毛
13歲的侯二毛是什麼樣子?那些從我身旁忽閃而過的女孩子的笑臉,總讓我忍不住要去想這個問題。走在山路上,總覺得她就剛剛挎著籃子,低著頭,從我的身邊羞怯地跑過;恍惚中也總能看到她坐在溪邊,洗衣,洗自己那一頭烏黑的長髮;而抬頭遠望時,又看見她正在對面的山坡上,放羊,唱著那支最最悽婉的歌……就這樣,她的影子時時在我的眼前,揮之不去,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娃那樣,她穿著土布紅襖,扎著又長又粗的辮子,辮梢上插著花,一朵剛剛綻放的鮮艷欲滴的山花,她愛花,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孩一樣,愛花,而她自己似乎就是另一朵剛剛含苞的山花。
又是開花的季節,此時,山路兩邊的草叢裏、峭崖上開滿了花,我已遙望不見60年前的那個開花季節裏,13歲的侯二毛那粗黑的辮子上插著的是哪種花,如今我只知道60多年前,在那個同樣也是開花的季節裏,13歲的侯二毛,辮子上插著花的侯二毛,就是從這條山路上,從這條兩旁開滿花的山路上,和許多少女一起被日本兵著,進了據點的。當年,那朵跌落在山路旁的小花,是侯二毛辮梢上插過的最後一朵花。
在據點裏,13歲的侯二毛每天都要遭受日本兵的種種折磨和侮辱。
4個月後,13歲的侯二毛就被日本兵糟蹋得成一朵枯焉了的花,父親便賣了家裏的所有財産,還借了債,才把快咽氣的女兒從日本兵的手裏贖了回來。
這時,13歲的侯二毛,肚子裏懷上了日本兵的孩子。
為了趕走女兒肚裏的孩子,家人用木杠在她的肚子上搟,趕驢拽著她在山路上顛……家人想盡了各種辦法,侯二毛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可孩子就是沒有下來。母親不想看著女兒被折磨死,就找來了村裏的幾位鄉親,問能不能等孩子先生出來,然後再……鄉親們説怎能讓這孽種見天日?最後,人們請了老醫生,老醫生的一劑烈藥灌進了侯二毛的肚子裏。據説,孩子在侯二毛的肚子裏掙扎了兩天兩夜,侯二毛也掙扎了兩天兩夜,第三天,肚子裏的孩子終於不再掙扎了,侯二毛也終於不再掙扎了,孩子終於死在了侯二毛的肚子裏,侯二毛也終於死在了被她擂塌的土炕裏。
村裏人又請了鐵匠,鐵匠用一天的時間,打了三根鐵釘,三根七寸長的鐵釘,鐵釘被一根一根釘進了侯二毛的肚裏,人們一邊釘著,一邊念叨著,説:不能讓小鬼子的孽種出來害人,小鬼子永世不得翻身。
這是一個真實的事情。我打聽過許多位老人,想找到侯二毛的墳,村裏也還有她的親人,他們帶著我,尋遍了村邊的溝溝壑壑,60多年過去了,誰都已經説不清究竟哪一撮土裏埋葬著侯二毛13歲的冤魂。那些個日日夜夜裏,我總是在睡夢中,被砸向侯二毛身體的錘聲驚醒,於是常常望著漆黑的夜空,整夜整夜無法入眠,就想:她還是個孩子,家裏不多的粗谷雜糧應該還沒來得及把她餵養成熟,她的身子一定還很單薄,皮膚很薄嫩,骨頭也不堅硬,尖銳的鐵釘輕易就能穿透她的腹部,還有她腹中的嬰兒,可為什麼那錘聲仍然那麼沉重,經過了60多年的隔音仍然那麼擾人?每當耳邊響起這錘聲時,都好像有一根鐵釘正在一點點穿透我的心,劇烈的疼。
當年關過侯二毛的窯洞還在,一把銹跡斑斑的鎖,鎖著洞門,也鎖著那段黑暗的歷史,鎖著那段黑暗歷史裏太多不為人知的秘密和那段黑暗歷史裏太多已為人知的恐懼。院子里長滿了荒草,也蓄滿了陽光,不知這些陽光當年是不是也曾灑在過侯二毛的身上?如果60多年前這裡也曾有過陽光,那麼灑在侯二毛身體上的陽光,一定是讓她感到刀割般的疼,冰霜一樣的冷。院子裏的棗樹挂滿了棗,鮮紅鮮紅的棗無人採摘,落在樹下的荒草間;院子裏的棗樹挂滿了棗,鮮紅鮮紅的棗當年13歲的侯二毛可曾採摘?這滿地鮮紅鮮紅的棗,讓人感覺那段歷史並沒走遠,就在眼前。
那些施暴的日本兵,那些還活著的當年施暴的日本兵,如今他們也該都是滿頭白髮的老人,也該有了自己的兒孫,在他們的生命同樣行將走向終點的今天,在他們每每和兒孫盡享天倫的時分,他們是否會偶爾想起這個樹上結滿了鮮紅鮮紅的棗的小院子,還有院子裏的那個13歲的中國女孩?
釘入侯二毛身體的鐵釘,辛酸而又無奈地表達了鄉親們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可侯二毛的屈辱和仇恨的長釘該怎麼釘?!其實每一個和侯二毛有著相似命運的“慰安婦”,死去的或活著的,她們的身體裏都被釘入過長長的“鐵釘”,死去的或許已不再疼,而活著的仍每時每刻疼得難忍。
林石姑
生於1920年,海南省陵水縣光坡鎮港坡村人。19歲那年被日軍抓走,關在軍部,關期間胳臂被打斷。因不堪日軍侮辱,曾幾次自殺。林石姑説因為被日本人抓去過,就覺得自己被人看不起,也因為這,自己這輩子受了太多的苦。
楊阿布
生於1920年,海南省保亭縣保城人。1940年春起屢遭日軍強姦並懷孕,1941年10月生下一男嬰,不久夭折。1942年被迫當勞工其間,遭日軍扣留,成為日軍長期發泄獸欲的工具,直至1945年秋,日軍投降後才得以回家。由於被日本兵糟蹋,楊阿布喪失了生育能力。她雙手做出抓人的樣子,她説她每天都在夢裏夢到日本兵來抓她。
就在侯二毛的身體被釘入鐵釘的那個秋天,在與她相隔數千公里之外的南中國,另一位名叫楊阿布的姑娘正經歷著與她相同的苦難:在遭受日軍的多次淩辱後,楊阿布懷孕了,懷著身孕的楊阿布東跑西躲,最後不得不躲進深山裏。在原始的山林裏楊阿布把孩子生了出來,但不久就夭折了。為了繼續逃避日軍的淩辱,楊阿布就藏在深山裏一個人偷偷活著。楊阿布是當地最漂亮的姑娘,日軍找不到她,就對甲長説:如果不把楊阿布送到據點,就要殺了村裏的所有人。為了保住全村人的性命,甲長只好帶著村裏人到山裏將楊阿布找了回來,全村人哭著把她交給了日本兵。從此楊阿布淪為了日本兵長期發泄獸欲的工具。
但她活了下來。活了下來,不知這是她的幸運還是更大的不幸:從此,一場噩夢開始兇殘地吞噬她的漫漫余生。
60多年後的一個夏日,在一場無邊無際的風雨中,在距離埋葬侯二毛的那片黃土數千公里之外的一個僻靜小村裏,我找到了楊阿布。她就活在那個處處留著她痛苦記憶的潮濕的村莊裏,活在那間壁上挂著發黴的雨跡的昏暗的小屋裏,活在小屋裏的那張鋪著椰樹葉同時也鋪滿了屈辱的老床上,活在60多年前的某一天裏……已經癱瘓在床的楊阿布,手中握著一把刀,刀很鋒利,但她仍在不停地磨著,吃飯的時候她握著這把刀,睡著的時候她握著這把刀,這些年來她永遠都握著刀,誰也不能拿開,她説她夜夜都夢到日本兵來抓她,沒有刀,她怕……説這話時,她的眼睛裏充滿了恐懼,手中的刀在身前來回地晃……
椰林仍是那片椰林,小路仍是那條小路,茂密的椰樹掩映著崎嶇的小路,60年,時光從這裡走遠,時光又從未從這裡走遠,對於楊阿布來説,一切就是昨天,或者就是今天。
陳亞扁
生於1927年12月,海南陵水縣鳥牙峒人。1942年春被日軍抓至砧板營軍營長期姦污,3個月後被往崖縣藤橋慰安所成為慰安婦,1年後又從藤橋慰安所送回砧板營軍營,直至1945年8月日軍投降。老人常常這樣一個人坐在房間裏發呆。
老人在往可樂瓶做成的水煙筒上裝著煙絲,裝好後,她抬起頭,望著我説:“問吧,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個慰安婦。”
坐在老人的面前,很久很久了,我不知道該怎樣對老人開口。如果有可能,我願永遠不向她提問,不問60多年前在她身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老人將嘴抵在水煙筒上,她深吸了一口,接著又嘆息般的呼出剛剛吸進嘴裏的煙,然後説:“那年春天,我還不到15歲……”老人沒有等我提問,她便開始講起當年自己被日軍強擄進慰安所的悲慘經歷。
1942年春天的一個中午,未滿15歲的陳亞扁正在家中的堂屋裏織著桶裙,嫂子和姐姐則在一旁舂米。突然,幾個端著槍的日本兵闖進屋來。日本兵的出現,讓姑嫂三人嚇得扔下了手中的活,她們驚慌失措地呆在那,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如虎似狼的日本兵嘰裏咕嚕地一陣亂嚷,他們堵住門,眼睛在我們姑嫂3人的身上掃了一遍又一遍,最後停留在我的身上。日本兵把姐姐和嫂子趕出了家門,他們先用匕首割斷了我身上係著的連著紡車的纏帶,然後就把被嚇得渾身發抖的我拉起來,獸性大發地進行調戲,一個個迫不及待地用手在我身上亂抓亂捏,並粗野地剝光了我的衣裙,然後把我按倒在地上,進行輪姦……不管我怎樣撕心裂肺地痛苦哀叫、拼命掙扎,他們都不停下來,還邊施暴邊興奮地狂叫……直到我大出血,昏死過去才罷休。”
從那以後,日本兵就經常來找陳亞扁泄欲。有時抓到軍營中留宿姦淫,有時在馬背上,或者在村寨外強行施暴,稍有不從陳亞扁就會遭到毒打。“後來,日兵就索性把我抓到砧板營的軍營裏,一同被抓去的還有同村的其他漂亮姑娘,我們被關在兩間簡易的木屋內,成了固定的‘慰安婦’,由日軍士兵日夜輪班看守。每天晚上我們都要遭受日本官兵姦淫,遇到輪姦時至少是兩三個,多時有四五個不等。”
在軍營中,陳亞扁白天在給日軍做飯用的大米中找出砂子,在院子中收拾房子,夜裏供日本官兵發泄性慾,有時白天也會遭到日軍官兵的性強暴。“3個月後,砧板營日軍奉命把我送到百里之遙的崖縣藤橋慰安所。在藤橋慰安所裏,我被關在一個盒子式的木樓上,樓下還關著其他姊妹。由於當時我年紀小,不來月經,晚上來姦淫我的日軍官兵人來人往整夜不斷,我常常渾身麻木,失去知覺……日本兵不把我當人看待,在我身體上為所欲為,用各種方法和動作對我進行性折磨,每天夜裏我幾乎都是死去活來,稍不順從,還遭毒打。每天每夜我也都能聽到姊妹們撕心裂肺的呼救聲和啼哭聲,也聽到日本官兵嚎叫狂笑聲。我在藤橋慰安所的日子,整天以淚洗臉。”
一年後,陳亞扁從藤橋慰安所又被送回到砧板營軍營。在砧板營軍營,陳亞扁被關在一間房子裏,相連的房子裏還關著同村的其他姑娘。白天,日軍叫她們幹各種雜活,夜裏又成為日軍官兵發泄性慾的工具。日軍砧板營軍營離陳亞扁家所在的村莊僅一里之遙,能聽到村裏的雞啼牛哞聲,可是陳亞扁卻無法見到家人的面,春去冬來,家人送來衣裙添換,也只能通過看守遞進來。“我在日軍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性折磨近4年之久,從未滿15歲的少女到渾身傷痛的18歲大姑娘,其間遭受到數以千計的日軍官兵肉體和精神上的蹂躪,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才得以逃離魔窟與親人團聚。”
由於遭受日軍長時間的羞辱摧殘,陳亞扁雖然逃脫了魔窟,但卻已無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走出日軍的慰安所後,她就一個人躲避到了深山裏,過起了與世隔絕的野人般的生活。直至解放後,人民政府把她從山裏請回來,分給了她土地,給了她自由生活的權利。1957年12月,30歲的陳亞扁嫁給了同村的一位鰥夫,然而婚後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3年後,陳亞扁再次嫁人,並生有一女。陳亞扁老人的第二任丈夫也已在多年前去世,現在老人和女兒一起生活。“我活不了多久了,現在我什麼也不怕了。我是慰安婦!我要把我的經歷告訴所有的人!”説這話時老人緊緊抓著我的手。
60多年前,當時僅4000余人口的陳亞扁家所在的鳥牙峒村,就有20多名少女被日軍抓去充當“慰安婦”,年齡最小的僅14歲,最大的不超過19歲。而據有關專家考證,在日軍侵華期間,至少有20萬中國婦女先後被逼迫為日軍的性奴隸,日軍慰安所遍及我國20多個省,中國是日本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國,陳亞扁老人的經歷是日軍侵華期間所有“慰安婦”的一個縮影。因為種種原因,大多日本慰安婦制度的受害人至死都沒有説出自己的那段悲慘經歷;然而也有越來越多的受害人正在像陳亞扁老人一樣,她們站了起來,把自己的那段經歷告訴所有的人,把那段歷史告訴所有的人。
尹玉林
生於1920年,山西省盂縣西煙鎮後河東村人。1941年春,尹玉林和姐姐尹春林一起被駐河東炮臺日軍抓走,姐妹倆在日軍炮臺上遭性摧殘達兩年多時間。
在村裏,我告訴村裏人我要尋找的那些老人的名字時,所有人往往都説村裏沒有這個人,最後常常是我不得已要告訴他們:這位老人曾被日本人抓到炮臺上,這時大家便都會不約而同地“哦”一聲,然後就會用手一指説:喏,那就是進過日本窯子的人的家。人們説這話時,臉上的表情令人捉摸不透。
在“進過日本窯子”的老人中,有些人一直隱姓埋名,也有一些是人們不再叫她們本來的名字,因為她們有了一個更讓人容易記住的“進過日本窯子”的名字,這個名字,就像一把銹澀的刀,時時為她們割扯開那道傷口。因為“進過日本窯子”,這一經歷改變了她們的一生,因為“進過日本窯子”,她們就不能再像正常人那樣生活,她們在村裏抬不起頭來,甚至有老人不敢出門,至今不敢與人説話。
在這幾十年裏,尹玉林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村裏生活著,就在幾年前,村裏人甚至家裏人都不知道她“進過日本窯子”的這一經歷。那時她深深地埋藏著自己的這段秘密,不和人説話,不敢太多地出門。現在,尹玉林説這個秘密讓自己痛苦了一生,她不想再繼續埋藏它,“進過日本窯子”那不是自己的罪過,製造這一罪過的人才更應該去痛苦一生。
1941年春的一天,駐在河東炮臺上的日本鬼子到村裏掃蕩,尹玉林家裏的人沒有來得及跑,就都被日本鬼子抓住了。他們一家人緊緊挨在一起,日本鬼子用刺刀把尹玉林、她姐姐和家人分開,然後拉到一邊,當著家裏人的面,就把尹玉林和姐姐強姦了。
日本人用刺刀逼著尹玉林和姐姐到了他們駐紮的炮臺。到炮臺後,她們姐妹倆就又被更多的日本鬼子強姦了一遍。
接下來,每天都是如此。
和她們關在一起的還有其他村被抓來的姑娘。有一個才13歲的鄰村小姑娘也被抓到這裡,小姑娘的身子很瘦小,每天晚上小姑娘都害怕得要命。她們裏面有結過婚的婦女,一到晚上就把這個小姑娘抱在懷裏,躲到大炕的角落裏邊藏起來,讓其他婦女躺到炕的邊沿上。但是每天晚上日本鬼子還是照樣要把那個小姑娘拉出來,一個接一個地糟蹋她。有時候白天日本鬼子也會把她拉到院子裏,逼她給他們跳舞,她不會跳舞,就又逼她做各種難看的動作來取樂,小姑娘年紀小,又羞又怕,什麼都不敢,日本鬼子就把她推到人群中推過來抱過去的。不到一個月,這個小姑娘就被折磨得全身浮腫,不能站起來了,連上廁所都只能爬著去,後來就連爬都不能爬了……
尹玉林和姐姐也很快就被折磨得受不了了,她們想回家,不想被日本人弄死在這裡,姐妹倆跑了好多次,但都被抓了回來,每次抓回來都要被毒打,連她們的父母都要受到牽連,被毒打。沒有辦法,最後只好任鬼子欺負。
在炮臺上兩年多時間,尹玉林和姐姐都患上了婦科病,很嚴重,下身疼痛,不能走路。後來日本鬼子看她們實在是不中用了,就讓家人把她們抬回家了。
姐姐尹春林,被日本人折磨得不能生孩子,後來丈夫就不要她了。尹玉林説姐姐的命比她苦,改嫁了兩次。
尹玉林後來和村裏楊二全結了婚,還生了孩子。楊二全在十幾年前去世了,尹玉林説,她過去的這段事情一直都沒有告訴過他,也沒法告訴他。
陳金玉
生於1925年,海南省保亭縣南茂場北懶下村人。1941年被日軍抓去當勞工,之後被編入“戰地後勤服務隊”,成為日軍性奴隸。1945年6月逃出日軍營地,一直藏身於荒野中,直到日軍投降。陳金玉老人的身體上,至今還留有當年被日本兵棍棒打傷的痕跡。臉上,頭上,甚至口腔,也都有至今仍在痛的傷。
譚玉蓮
生於1925年,海南省保亭縣南林峒人,1942年日軍侵佔南林峒時,她和同村的其他幾位姑娘一起被日軍送到據點,成為“戰地後勤服務隊員”,受到難以忍受的淩辱,直到日軍投降。“文革”時,因曾經當過“日本娼”,譚玉蓮被批鬥。有位當年和她一起被日軍抓去經受屈辱的譚亞細,在被掛牌、遊村、批鬥後死去。
王改荷
生於1920年,山西省盂縣南社鄉侯黨村人。24歲時,日本侵略軍闖進了她的家,槍殺了她的丈夫,並強姦了她。後又被關在炮臺上,成了日軍性工具。
蒲阿白
生於1915年,海南省三亞市鳳凰鎮人。1941年被日軍抓去,當日即遭多名日軍強姦,並被關。一年後被轉移至司令部,直到日軍投降。在被關期間懷孕,生下一女孩,女孩15歲時受傷致病,後在井旁打水時病發,落井死亡。90歲的蒲阿白仍然每天都在為自己的生計而奔走。
符美菊
生於1928年,海南省澄邁縣中興鎮東嶺村人。16歲時被日軍抓去加入“戰地後勤服務隊”,成為日軍的性奴隸。符美菊的丈夫王和安在6年前去世,兩個兒子也已相繼去世,媳婦也都改了嫁。符美菊的身邊如今只有孫子王才強跟著她生活,王才強今年14歲。
張仙兔
生於1925年,山西省盂縣西煙鎮西村人。15歲那年的大年初三,日本侵略軍衝進她家把她搶走。在日軍的炮臺上張仙兔受盡淩辱,後被家人以700大洋贖回。
(作者:陳慶港 資深新聞攝影人,某週刊視覺總監。作品刊于《南方週末》、《新週刊》等國內主流媒體,併為國外多家通訊社選用。作品《慰安婦》獲首屆“華賽”(中國國際新聞攝影比賽)金獎,《細菌戰》獲人民攝影全國新聞攝影比賽金獎。)
來源:杭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