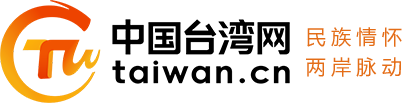鄧麗君誕辰70年,全球華人不斷紀念是在紀念什麼?
中新社北京5月7日電 題:鄧麗君誕辰70年,全球華人不斷紀念是在紀念什麼?
——專訪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白惠元
中新社記者 楊程晨
5月8日是鄧麗君逝世28週年的日子,來自全球的鄧麗君歌迷陸續前往她的長眠地——位於臺灣新北市金寶山筠園悼念。
近30年來,包括兩岸及港澳中國人在內的全球華人每年定時紀念鄧麗君,這位傳奇歌者好似從未走遠。今年也是鄧麗君誕辰70週年,一些過去不常見的影像被發掘併發布在社交平臺,展現著熟悉面孔下的另一面,關於她的記憶愈發清晰。鄧麗君承載著跨越流行時代的哪些文化符號?人們不斷地紀念,是在紀念什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白惠元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除了是華語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指標人物,鄧麗君對於包括兩岸及港澳中國人在內的全球華人來説,意味著什麼?
白惠元:鄧麗君最重要的就是讓全球華人都聽見了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中華文化已超越了國界。鄧麗君現象有助於我們尋找中華文化內部的一種通約性,實現跨地域的共情。
我認為,鄧麗君是港臺華語流行音樂史上重要的指標性人物之一。但鄧麗君又很特別,因為她主要是翻唱歌手,很多歌都是經過她的演繹才成為廣為流傳的代表性作品。
鄧麗君的演唱能讓全球華人聽見,基於四個特性。首先是古典性,鄧麗君學過黃梅調,1982年推出過一張根據中國古典詩詞譜曲的專輯《淡淡幽情》,我們熟悉的《獨上西樓》就來自其中,她很早就嘗試把中國古典文化進行當代轉化。其次是民間性,她翻唱過《鳳陽花鼓》《晚風花香》《望春風》等中國民歌,通過歌聲展現中國不同地域的人文地理風貌。第三是都市性,她還有部分作品是翻唱反映20世紀30、40年代上海的時代曲,如《天涯歌女》《四季歌》,她的演唱方式和周璇等大上海女歌星之間有一種互文、傳承的關係。第四是亞洲性,聽眾比較熟悉的《甜蜜蜜》原是印尼民歌,像《再見我的愛人》《我只在乎你》等則源於日本流行音樂。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國性。鄧麗君在眷村長大,父親是河北人、母親是山東人,她也一直強調自己對於祖國、對於民族的認同。
中新社記者:在20世紀的70、80年代,鄧麗君的音樂是如何輻射香港及東南亞社會的?
白惠元:鄧麗君首先是在臺灣成長,她的音樂流傳到香港,後來她又去了日本,這本身就呈現出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流動性。在中華文化內部,鄧麗君的表演能喚起跨地域聽眾的集體記憶,就像她歌中反覆演唱的“月亮”一樣,具有情感的豐富性和強大的召喚力。當然,在不同地域流傳時,鄧麗君對人們的意味也有些許不同,凝聚著人們不同的想像。
對於大陸來説,鄧麗君是改革開放的時代標記。她柔軟的聲音,進入到那一代年輕人的“情感結構”之中。香港電影《甜蜜蜜》《千言萬語》以鄧麗君歌曲為名字,勾連時代變遷,召喚著香港民眾關於民族和國家的身份認同,以及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在臺灣,比較典型的是著名導演李行拍攝的電影《小城故事》和《原鄉人》,都是請鄧麗君演唱主題曲,所強調的也都是中華文化傳統。不止如此,鄧麗君在日本發展,她的歌曲在後來的日本電影中也留下了時代記憶,比如岩井俊二《燕尾蝶》、是枝裕和《比海更深》等。可以看出,鄧麗君不只是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亞洲。
中新社記者:在20世紀70、80、90年代,為什麼大陸會那麼風靡鄧麗君的歌曲?她對於那個年代的大陸年輕人來説意味著什麼?
白惠元:那個年代,很多人説鄧麗君的演唱是“靡靡之音”,這和她的演唱方式有關。她是一種氣聲唱法,把説話的聲音帶到了演唱裏,把日常生活帶到了音樂中。不同於傳統意義上歌唱的宏大敘事和嚴肅表達,她尤其熱愛歌唱愛情,這與20世紀80年代初的新啟蒙話語形成了呼應,也起到了思想解放的效果。在時代語境中,這種現象不是孤立的,文學界則表現為劉心武《愛情的位置》、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小説。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唱法出現了很多模倣者,比如大陸的楊鈺瑩等。1995年,王菲出了一張翻唱專輯去致敬偶像鄧麗君,就叫《菲靡靡之音》。
不能回避的是,鄧麗君在大陸開始流行時,很多年輕人是“偷聽”到她的音樂。從海峽對岸飄來“靡靡之音”,某種程度上預告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兩岸從對峙走向交流,構成了一種跨越政治界限的共同情感記憶。這些歌曲成了那一代人在那一時期的私人回憶,在這個意義上,鄧麗君和許多人的人生烙印緊密結合。
她的歌曲內容是無關現實政治的,恰恰是這種風格,能在當下語境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實現“軟著陸”,起到春風化雨的美學效果。兩岸青年之間共同文化記憶的塑造,是很多文化機構、媒體在一直嘗試的事。最近湖南衛視的節目《聲生不息�寶島季》也通過臺灣綜藝節目常出現的街訪環節,尋找著兩岸青年的共同音樂記憶。而故事的另一面是,“鄧麗君唱法”的後繼者們開始嘗試“柔軟”地唱出共同體想像,從李谷一《鄉戀》、蘇小明《軍港之夜》,到楊鈺瑩《十送紅軍》、王菲《我和我的祖國》,這種聲音形象拓展了我們對“主旋律”的理解空間。
總之,鄧麗君是一個開始,但肯定不是終結。
中新社記者:實際上,鄧麗君這一批明星當紅的歲月,現在的許多年輕人都還沒有出生。但卻並不妨礙今天的“00後”們懷舊。這是為什麼?
白惠元:從歌聲角度看,鄧麗君的聲音給“00後”帶來了一種“治愈係”的美好感覺,她溫潤、舒緩、鬆弛、輕柔的歌聲,有效療愈了現代生活的速度焦慮。無論何時何地,只要鄧麗君的歌聲響起,它都會觸發一種強烈的、具身的情動效果,將網路碎片迅速整合為一種共情力。
歌聲之外,鄧麗君幽默機智的現場對答也在當下短視頻平臺獲得了較高熱度。在這些近乎脫口秀的語言場景中,鄧麗君展現了現代女性的自信、爽朗、親和、獨立。比如,在著名的“鄧麗君説山東話”短視頻中,她流暢的山東方言就贏得了“00後”的彈幕狂歡。我想,在這“對答如流”的背後,正是鄧麗君真實流淌的故土情結與身份認同。
在“00後”對鄧麗君的評價中,最常出現的詞是“優雅”。這是近年我比較關注的一個現象:“00後”越來越喜歡從中國古典文化內部發掘一種“原生的優雅”,包括關於故宮的、中國文物的“出圈”紀錄片,也包括舞蹈《只此青綠》等。青年人在這裡找到了一種認同,他們成長于“中國崛起”的年代,從帶有中國古典氣質的“優雅”中可以感受到中國的文化自信。
在這樣一個維度上,他們再次發現了鄧麗君的“優雅”,這是當下追求流行的年輕世代和鄧麗君産生的微妙碰撞。(完)
受訪者簡介:
白惠元,文化研究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電影與大眾文化。著有《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代中國的自我超越》,曾獲第五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作品獎。在《文藝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電影藝術》等期刊發表論文三十余篇,部分論文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