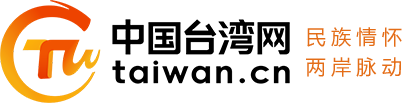文明的細節:來自陶寺的調研報告
來源:3月30日《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趙東輝 劉翔霄
初春的暖陽,如同輕紗般灑落在晉南的黃土地上。遠遠望去,襄汾縣陶寺鄉一片層層疊疊的農田裏,一座規模空前的城郭遺址若隱若現。
這裡是陶寺遺址。它與浙江良渚、陜西石峁和河南二里頭一起,並列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處都邑性遺址。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考古發現之一,陶寺遺址為延伸中華文明史提供了重要實證。
它的存在表明,早在4300年前,華夏大地上已孕育出繁盛而且較為成熟的早期文明形態。從氣勢恢宏的土木工程技術到觀天授時的“國家工程”,從神秘未解的朱書文字到井然有序的禮制體系,陶寺猶如一處塵封的時光印記,映照著中華文明起源的時空版圖。
開時間和空間之混沌
天光朦朧,在觀象臺的一根根夯土柱間投下暗影重重。當清晨第一縷陽光越過遠處的崇山,幾位早已等候多時的陶寺先民站在特定的觀測點,觀察日出、記錄位置、加以標記,迎接一個時節的到來。
在陶寺遺址博物館,現代科技模倣復原出陶寺先民觀天測象的一幕。
位於遺址東南部的“古觀象臺”被發掘時,只剩下13塊呈半圓形排列的夯土基址遺跡。它們“墻不像墻,路不是路”,引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員、時任考古領隊何努的注意。經過兩年多的反覆求證、模擬觀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專家和中國科學院天文學家初步證實,陶寺遺址“古觀象臺”由13根夯土柱、特定的觀測點和三層夯土臺基三部分組成,總面積1740平方米。
“通過夯土柱間12道縫隙觀測日出方位、捕捉星辰軌跡,陶寺先民可精準劃分20個節令,是傳統二十四節氣的主要源頭。”何努説,陶寺古觀象臺的發現,表明當時的陶寺君王已經能夠制定曆法、安排農耕、頒行天下。
陶寺遺址原址處復原重構的“古觀象臺”,陶寺先民據此精準劃分20個節令,是傳統二十四節氣的主要源頭(高江濤供圖)
晉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是堯都平陽、禹都安邑和叔虞封唐等古史傳説的發生地。已有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陶寺遺址就是文獻記載中的“堯都平陽”。而古觀象臺的發現,也使《尚書�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説法得到了印證。
出於狩獵、採摘和農作的生存需要,遠古人類很重視對太陽的觀測。天文觀測設施在古代建築和城市遺存中比較普遍,埃及的阿布�辛拜勒神廟、故宮的太和殿等都有類似設計。“陶寺古觀象臺並非隨意建造,而是建立在精心的選址和朝向測量基礎之上的。”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副研究員黎耕説,這正是陶寺先民“逐日而居”的寫照。
人們在原址處復建了這個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經常有天南海北的天文愛好者尋訪至此,搭起帳篷、觀察拍攝,沉浸式體驗先民們追光逐影的創舉,感受經天緯地的文明初象。
如果説,陶寺遺址觀象臺説明先民們在那時已經有了“大時間”的概念。那麼,陶寺中期王墓中“沙漏”的出土,則説明先民們也已經有了“小時間”的概念。
考古人員進行復原實驗後發現,形似沙漏的陶寺文物與我們今天的一天24小時計時相差很小。這一發現補全了陶寺的計時體系,形成了一套年、月、日、時的完整計時系統。
在陶寺,還初步形成了流傳後世的度量空間、長度的標準。
陶寺大墓中出土了黑、綠、紅三色相間的“圭尺”,出土時已有殘損,考古專家和天文學者推測其全長應在1.7至1.8米之間。在夏至、春分和秋分,日影長度會顯示在圭尺上不同的顏色條帶。對陶寺圭尺的考古研究表明,當時的陶寺先民已經有了“地中”觀念,認為自己所在就是天下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認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之“中”始自陶寺,這正是“何以中國”的關鍵實證。
“精準管理時空並服務於王權與社會,是陶寺作為早期國家科技與制度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標誌著中華文明經天緯地的肇端。”何努説,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共識意義上的“地中觀念”,亦被後世歷代王朝繼承完善。
考古還發現,陶寺社會已使用“肘尺”的測量方法,三肘的長度加起來約等於今天的0.75米。學者們推斷,流傳後世的“寸”可能與“肘尺”存有淵源關係。
如果盤古開天闢地只是一個神話傳説,那麼在陶寺遺址,我們則看到了先民劃時間、定長度、劈空間的具體操作。
農耕文明的孕育
穀雨時節,空氣中瀰漫著泥土的清香,霧氣在大地上升騰。腰間捆紮著秧苗的陶寺先民,熟練地播下一年的希望。“呦呦鹿鳴,食野之蘋”——也許,我們的先民從那個時期就創造了口口相傳的《詩經》,一直流傳到現在。
作物的種植與節氣密切相關。可以想見,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觀象臺,早期的農耕文明便在這裡日漸孕育成長。
“觀象臺反映的是當時先進的‘科技文明’,是最早的‘天地人合一’,也是最早的‘問天系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遺址第五任考古領隊高江濤説。某種程度上,它也是農業生産的“剛需”,依據觀象而誕生的農時劃分,可以很好地指導陶寺先民應時而作,開展集中種植。
陶寺出土的稻穀、倉儲區表明,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作物馴化”。人們能夠從大自然中選擇作物,並摸索出一套基本節令,據此對集中種植作物進行安排,也能夠形成一定的糧食儲備。而剩餘糧食的産生,促進了進一步的社會分工和手工業的發展,從而為當時的文化發展創造了條件。
一個可以印證農耕文明的細節,從遠古的晉南大地浮出:在陶寺,考古發現了截葉鐵掃帚、蒼耳、草木樨、黍、粟、稻、豆,以及桑樹、樺樹和柏樹等多種植物集中起來的種子化石,説明當時陶寺一帶作物多樣、生態良好。這裡土壤肥沃、四季分明、五穀豐登,有利於人類生存和人口繁衍。
這一細節也説明,4000多年前的晉南大地,也許能夠看到“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美景。
陶寺遺址出土龍盤(陶寺遺址博物館供圖)
在距陶寺遺址7公里以外的汾河中,考古還發現了陶寺時期的鱷魚骨板以及竹鼠化石,兩者都是今天常見於長江流域的動物種類。這些跡象表明,當時的陶寺曾有大片的水域和茂林,環境氣候比今天更加溫暖濕潤。
細緻的考古發掘進一步證實,陶寺早中晚三期均有氣候波動,部分植被已經消失。今天在陶寺一帶廣泛種植的柳樹、楊樹等在當時並未出現,説明陶寺歷史上出現了氣候變化並漸趨幹冷,直至今天成為典型的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
掩映的國家雛形
經過綿延數千年的風雨侵蝕和人類生産生活的破壞,陶寺遺址的地貌已經發生了改變,廢棄的城墻、宮城等早已面目全非。要想從一片荒垣斷壁和支離破碎的遺物遺跡中讓歷史“重現”,談何容易。
古城墻和宮殿遺址的相繼發現,讓這一切有了眉目。
“尋找城墻的工作持續了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特級技師馮九生回憶。在遺址北部,考古人員循著破碎的夯土遺跡,終於發現了古城墻的蹤影。城墻由夯土夯砸而成,部分地段已遭毀壞,但連接起來能夠圍成一個“圈”,形成了一個圓角長方的形狀。
古城墻的發現,使古城規模進一步得到了確認:這是一座巨無霸式的城池,被城墻合圍的區域面積超過了280萬平方米,興建與使用的主體年代距今約4100年至4000年。考古人員根據夯土遺跡推算得出,城墻底寬最寬處約10米,高約8米,曾歷經數次大規模擴建。
這座大城清晰呈現出“宮城—郭城”的分野,城址分為內、外兩城,功能分區、等級秩序和空間格局分明有序:從1978年首次發掘至今,陶寺遺址陸續發掘出城墻、宮殿區、宮室類夯土建築、大型墓地、統一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大型倉儲區和平民區等,功能十分完備。
“一系列考古地點的發現,為今人勾勒出陶寺先民充滿智慧和理想的營建,成為文明早期都城制度初創時的空間樣本。”陶寺考古遺址公園規劃師、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文物保護科技研究院副院長王璐説。
在這座大城內,又發現了一座面積近13萬平方米的宮城。宮城由寬度大於大城城墻的城墻圍繞著,且有形制特殊、結構複雜、防禦色彩濃厚、史前罕見的城門址。“陶寺宮城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明確帶有圍垣的最早宮城,並使陶寺‘城郭之制’完備,成為中國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內涵的重要源頭。”高江濤説,宮城內有大量殘留的宮殿建築基址,其中一處宮殿建築僅柱網結構就有540平方米。
這些細節證明,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理念在陶寺時期已具雛形。
陶寺遺址平面圖。在這座大城內,考古發現了一座面積近13萬平方米的宮城,陶寺宮城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明確帶有圍垣的最早宮城(高江濤供圖)
陶寺大城的發現,在考古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4000多年前,能夠修建這麼大一座城池,意味著陶寺聚集著數量眾多的人群,也已經擁有了強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陶寺文化的實力可窺一斑。”高江濤説。
王巍則認為,這是首次在中原地區發現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城址,考古學上把它稱為王權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
生死之所的差異,也表明陶寺社會已然出現嚴格的等級分化。
陶寺君王居住在高大恢弘的宮殿,普通貴族住在20平方米到40平方米的雙開間,平民住處則為半地穴式。早期和中期墓地都有大墓、中型墓和小墓,呈現出嚴格的階級分化。大墓有序分佈在墓葬區的特定區域,隨葬品中不僅發現了傳説中上古時期最高等級場合使用的禮制樂器組合土鼓、鼉鼓和石磬等,還有後世王者的象徵——龍盤。與此對比鮮明的是,有的小墓簡陋到僅能容下一人,隨葬品很少,甚至沒有。
陶寺遺址出土鼉鼓(陶寺遺址博物館供圖)
“地位凸顯的宮殿區、等級分化明顯的墓葬、標誌身份的禮器群、具有觀象授時功能的大型建築等,都表明陶寺文化已達到早期國家的標準。”高江濤説,它提供了一個以政治文明為中心的國家都城遺址範例。
陶寺遺址是迄今黃河流域發現的最大史前遺址之一,現存面積約400萬平方米。陶寺遺址博物館展陳顯示,遺址坐落于崇山向汾河谷地過渡的黃土垣上,地勢較高,呈大緩坡平面。城址面向西南,整體上正合春秋時期軍事家管仲所著《管子�乘馬》“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之説,呈現大山懷抱、依山傍水的獨特地貌。
已故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對於陶寺的歷史定位是這樣表述的:“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進的歷史舞臺轉移到了晉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區文化以及東方、東南方古文化的交匯撞擊之下,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這時的‘中國概念’也可以説是‘共識中的中國’。”
中華文明的“華燈初上”
4000多年前,中華文明的圖景發生著巨變。
盛極一時的長江中下游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等相繼衰落,中原崛起,興盛于黃河中游晉南盆地的陶寺文明脫穎而出。海岱地區的陶器、石家河文化的玉獸面、良渚文化的玉琮……各地的文明因素匯聚而來,使陶寺成為一處史前文明因素的“集大成者”。
“陶寺遺址匯聚融合四方文化因素與精華,有相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文化品質和特點。”高江濤説,這是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重要開端。
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誕生了一脈相承、流光溢彩的早期中華文明,奠定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基礎。陶寺遺址考古發現了我國史前時期的早期文字或符號,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發現。
“用硃砂寫就的兩個字,同時出現在了大墓出土的一個扁壺上。”何努説,其中一個字,學界普遍認為是“文”字。它與後世安陽殷墟出土甲骨文的“文”寫法幾乎完全一致,卻早了足足700餘年。
另外一個字,有學者認為,它像是甲骨文中的“昜”(讀“陽”)字,“文昜”二字表明古代帝王的盛德高光。也有學者認為是“文邑”,代表“夏邑”,即夏代王庭。何努則認為,字體上端的城圈、土塊代表夯土大城,而在中國古代文字中,壘土為“堯”,因此是“堯”字。雖然説法不一,但指向了傳説中堯舜所在的那個時代。
陶寺遺址考古發現了我國史前時期的早期文字或符號。(高江濤供圖)
此時,文明社會的另一要素——冶金術,也在陶寺出現。
在銅器遠沒有普及的史前時代,陶寺卻發現了銅環、銅鈴、銅蟾蜍等7件銅器,數量明顯多於其他同時期遺址,是迄今我國發現最早的銅器群。它們已經採用範鑄技術——後世青銅時代的核心技術,為即將到來的夏商周時期青銅禮樂文明奏響先聲。
2024年11月12日,陶寺遺址博物館開館儀式上,沉浸式演出的古裝舞者在聚光燈下一舞驚鴻。
翩翩舞姿,仿佛帶人們穿越回那個禮樂文明的發啟時代。
陶寺大墓中出土有7大類29件古樂器,其中,石磬以及用鱷魚皮蒙做鼓面的鼉鼓,是迄今所知同類樂器中發現年代最早的。在後來的甲骨文中,“鼉”字正是揚子鱷的形狀。高江濤認為,陶寺出土的成組樂器,説明禮樂制度已經在陶寺大地上萌芽,象徵王權的禮樂器組合在這裡誕生,逐漸演變為夏商周時期的禮樂器。這些禮樂器的發現,也使得《尚書》“擊石拊石”、《禮記》“土鼓”、《詩經》“鼉鼓逢逢”等古老的記載在陶寺找到了實物印證。
在陶寺,還出現了一個特殊現象:6000年來,各地常作為武器而存在的斧鉞,在陶寺大墓中出現時尖刃向下、鏤空雕漆,作為一種儀仗用具成排地沿墻擺放。大墓中還出土了拔掉獠牙的野豬下頜骨,以及兩張折斷的弓,昭示統治者“休兵不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念,體現當時社會繁盛而不黷武擴張的“和合”思想。從這些墓葬細節,不難看出陶氏先民以禮治國、協和萬邦的大政之道。
沿襲數千年的中國古代建築特點,在陶寺已經初見端倪。
考古發掘和研究表明,陶寺宮殿的建築佈局與後世都城制度有一定的傳承關係。遺址的主體建築居於核心區域,這種建築理念一直延續到明清故宮。類似“東廚”的房址位於宮城主殿東側,後世“東廚”的宮室制度疑由此開創而來。宮城外的倉儲區發現了大量的大型灰坑,採用環形坡道上下,這與2500年之後隋唐時期的窖穴十分相似。陶寺宮城南墻上的“闕樓”式建築,也與隋唐時期洛陽城應天門闕樓大體相近。
《新唐書》記載:“古者祭天于圓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遺址,已經有了與之對應的“祭祀區”,如“觀象臺”遺跡和墓葬區等。考古發現,陶寺墓葬區疊壓存在著多個時期的墓葬,疊壓墓葬達100多處。直到現在,周邊村落的女性仍心存恐懼,不敢獨自前來這一帶。有民俗學家認為,這種心理可能與世代的口口相傳有關。
一個細節引人注目:陶寺宮殿區規劃在城池的東北部,而容易産生大氣、土壤和水污染的手工業作坊區則位於距宮殿最偏遠的西南部,在這裡很可能出現了早期的“環保規劃理念”。
位於手工業作坊區的回字形夯土建築面積有1000多平方米,在周圍十幾平方米的眾多“小房子”中顯得特別“高大上”。考古人員推測,這可能是管理手工業生産的機構,同時能説明官營手工業作坊已出現,相當於現代城市裏的“工業園區”。
“陶寺已經有了早期王權國家和禮制制度的出現,這些因素都被夏商周和後世所繼承發揚,也是人們普遍認可的中華文明的顯著特徵之一。”高江濤説。
作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中華文明,諸多流傳後世的文明特徵,能在陶寺找到相應的發端和細節。
最早的“生活藝術”
種種細節表明,陶寺已經誕生了那個時代最高級的生活文明和起居文明。
在宮城內,考古發現了明確的宮殿建築基址及其附屬建築。隨著考古發掘的全面展開,陶寺宮室制度的大體樣態逐漸呈現:在大型夯土基址上,建造有前後兩座宮室類建築,這些應該是處理政務或者廟堂之類的主殿。這一區域的柱洞直徑均在30釐米到50釐米之間,呈有序排列狀,可見宮殿主人的身份和地位非同一般。宮殿內外墻皆用石灰制的墻皮加以裝飾,外墻上繪有精美的幾何紋,內墻墻面則採用了白藍雙色的經典配搭。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宮殿區罕見地出現了一間形制獨特的“大房子”,面積有40多平方米,為淺地穴建築。這一區域的地面上出現了白灰皮室內地面的刻劃裝飾,刻劃出一排排長方形格子,並在格子中間戳印出紋路清晰、凹下去的三角花紋,美觀且防滑。地面塗抹的白灰皮厚度一釐米有餘,質地堅硬,有防水、防潮之效。考古人員懷疑,這座大房子與宮室日常生活的“洗浴”有關。
“陶寺考古長達47年,唯獨在這裡發現了這種刻劃修飾類似‘地板格’的地面,特別珍貴。”馮九生説,北方地區偏冷偏乾燥,專有的這種用途的房子在當時應不常見,或許反映了高等貴族擁有有別於平民的華麗生活,這些應該是很重要的物證。
宮殿區的附屬建築中還出現了淩陰和烤爐。
淩陰的功能等同於現代冰箱,在地下約8米深處。建造者有意將坡道打成了臺階狀,以防止垮塌。在這裡,甚至發現了因長期存放冰塊而形成的淤土痕跡。
在大型宮殿建築外的東南角處,發現了一種小型直立的“窯爐”。窯爐有上下室之分,中間是鏤空的窯篦,窯內有明顯被燒過的石頭,旁邊有橢圓形的“操作坑”。有學者研究認為,這種飲食方式並非中原傳統,而是充滿了“異域風味”。“它僅限于宮城內部製作和享用,可見陶寺政權視之為一種高級的生活方式。”何努説,它除服務於宮廷日常生活之外,還為陶寺宮廷的君臣禮聚、邦交設宴等“美食政治”服務。
隨葬的石廚刀在陶寺大墓中比較常見。大中型墓葬中還發現了石鏟、木勺以及陶盆、灶等炊事物品,以及木案、木觚、木豆、骨匕等飲食器具組合。考古人員表示,這類器具佈置陳列體現社會等級地位,反映當時社會的飲食之禮。
水井的“技術革新”也在陶寺問世。考古發現,陶寺遺址的多處井址內壁上加築有木質“井框”,以防止坍塌現象的發生。
遠古人類嫺熟的制陶技藝,在陶寺時期已經嶄露頭角。經過拼接修復,大量看似平淡無奇的灰色陶片恢復了它們的原本樣貌。其中,有先民打水的扁壺、煮飯的鬲、存放糧食的陶罐、加熱液體的陶斝等生産和生活用品。
今天,人們可以想像先民燒制陶器的盛景:能工巧匠們在制陶房內忙碌著,柔軟的黏土在他們的手中熟練地塑形,壺、罐、盤等各類陶器逐漸展現,嫋嫋升起的煙霧中夾雜著泥土與火焰的氣息。窯爐外,一排排尚未燒制的陶器整齊堆放,等待著一場爐火純青的淬煉。在整個燒制過程中,先民們需要精確控制火候,並根據火焰的顏色和陶器的顏色來判斷溫度,這需要豐富的實踐經驗和高超的技術,才能確保陶器在燒制過程中不變形、不開裂。
這一過程寫滿了未知數,直到開窯一刻的到來。
陶寺遺址出土土鼓(陶寺遺址博物館供圖)
遠古的“文明危機”
陶寺社會是怎樣由盛轉衰的?關於這一點,並無確鑿的歷史記載。但從考古遺跡可以推斷出,這裡曾經發生過血腥的暴力衝突。
根據考古發掘推測,陶寺城內出現了慘烈的毀墓和殺戮現象。陶寺晚期的大墓均被搗毀,破壞行為從墓口一直持續到墓地,出現了甲墓葬人頭被扔到乙墓葬當中的現象。宮殿區也發現了很多頭骨以及大量被肢解的人骨,宮殿有被夷為平地的跡象。
“宮城和城墻都有修復跡象,但沒能完成修復,可見當時或許出現了一個政權再興的過程。”高江濤説。
在古觀象臺遺跡旁的圍溝裏,考古發現了大量石材。考古人員推測,這可能是觀象臺被強行推倒後,攻擊者擔心石材會被作為戰略物資再次使用,而選擇將其傾倒於此。
何努先生還認為,陶寺晚期的衰落與石峁的南下衝擊有關。
浪濤奔涌的黃河行至晉陜大峽谷附近,出現了“幾字形”大拐彎。峽谷兩岸的山西陶寺與陜西石峁橫空出世,並稱為“黃河雙雄”。考古證實陶寺以農業為主,陶寺與石峁兩地有農業、資源等文化往來,還有風格類似的“甕城”類建築。
龍山時代末期,風雲際會。從文化互動、關係密切到衝突升級,這或許是歷史上第一個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發生的“最早戰爭”。
到了漢代,陶寺還有零星的居民定居,此後便無人問津。今天的人們只能猜測,或許是戰爭,又或者是族群衝突,讓盛極一時的陶寺走向了衰亡。
煌煌都邑最終廢棄,陶寺文明自此“遠去”。
在距此200多公里外的二里頭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陶寺遺址既有的綠松石鑲嵌的器物、範鑄青銅器、漆木器等。而且,二里頭遺址也出現了與陶寺似曾相識的宮城、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等功能分區。可見,陶寺文明仍在延續中。
陶寺遺址出土銅蟾蜍(陶寺遺址博物館供圖)
文明的迴響
河流穿城而過,城內小橋流水人家。闕樓高立,樓間張燈結綵,禮迎八方來客。
考古發掘的細節表明,數千年前的陶寺,物阜民豐、百工興盛,四方聚落主動交流,往來友好,互動頻繁。彼時的陶寺,如同《尚書�堯典》中描述的那般文明氣度:“光被四表、協和萬邦。”
浩瀚星空,見證著“堯”的豐功偉績。可見“堯”的存在,是有跡可證的。“堯”時期的中華文明在那個時代的地球上,已然燦若熾陽。
幾代考古人證實,陶寺社會至少歷經400多年的歷程,它所呈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文明標識與“堯都”有著密切的印證關係。“堯”,也隨之走出迷霧重重的“傳説時代”,走向考古實證充分且清晰的“信史時代”。
“堯可能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更多是指一個時代。”持有這一觀點的高江濤認為,陶寺遺址應是以“堯或堯舜為代表”的那個時代的都城。
從時間節點看,陶寺遺址距今年代與古史記載的堯時期一致。文獻記載,夏代之前,存在著一個中華文明早期歷史階段。“百年中國考古學實踐證明,那個時代確實存在,並且已經進入文明社會。”高江濤説,其大體相當於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恰是中華早期文明和國家形成的關鍵時期。
從地理位置看,陶寺所處地帶,正是古史記載的“唐地”“堯墟”所在。臨汾市存有“堯廟”“堯陵”等文物古跡,也一同佐證著“堯”的傳説。
王巍等人認為,從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遺址性質、等級和內涵上判斷,陶寺遺址是“堯都”所在。
長期研究陶寺考古、已故考古學泰斗嚴文明先生曾説:“最早的中國是在什麼時候呢?是在傳説中的堯舜時代。現在從考古來看,可能堯都就在山西的陶寺。”
時至今日,陶寺遺址留給人們的思考題還有許多。比如,陶寺之前,先民怎樣觀測日出?之後又是如何演變出二十四節氣、二十八星宿?文字的載體怎樣從陶罐走向甲骨?陶寺文字與寫在玉石片上的“侯馬盟書”有無關聯?……
未來,還有很多謎團等待揭開。
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廣泛地聯合和團結天下,以一種開放包容的胸懷,向世界展示著不同區域文明之間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盛況。
4000多年後的今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廣泛地被世界各國所接受,被世界人民所認同。在世界文明版圖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正展示著見證時代之變的文明力量。
跨過山海,穿越時空。
文明的迴響與時代的召喚在這裡匯合。
陶寺遺址,一處文明探源的新坐標,見證著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生生不息、奔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