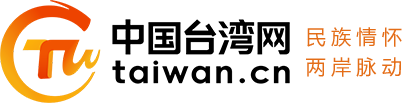向世界生動展示新中國形象
向世界生動展示新中國形象
《白毛女》歌劇劇本在1945年由賀敬之、丁毅等人執筆,根據20世紀40年代流傳在晉察冀邊區的“白毛仙姑”故事創作而成,同年4月作為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獻禮作品在延安首次演出。演出非常成功,《白毛女》很快傳播到全國各地,成為風靡大江南北的經典之作。在新中國成立後,《白毛女》除了被改編成京劇、電影、連環畫、四扇屏、幻燈片、皮影戲、芭蕾舞劇等多種形式,還走出國門,並在海外得到廣泛傳播與接受:劇本于1951年獲史達林文學獎二等獎,由東北電影製片廠在1950年拍攝的電影《白毛女》于1951年7月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辦的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中獲得第一個特別榮譽獎。它作為一部充分體現出新中國人民取得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精神的紅色經典,不但被譯成日語、英語、俄語、印尼語、西班牙語、羅馬尼亞語、僧伽羅語、捷克語等多種語言在多個國家發行,而且以歌舞劇、話劇、芭蕾舞劇、電影等多種表演形式,首先是在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及法國、日本等得到廣泛歡迎與傳播,然後以這些國家為輻射中心,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逐漸擴散到以英語國家為主的西方社會,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影響。這也使它成為迄今為止世界影響最大的一部中國紅色經典,在70餘年間的歷史進程中持續不斷地把新中國形象傳播到世界各地。
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説:“我在解放區所觀看過的戲劇中,這是最好的,大概也是最負盛名的”
中國戲劇團于1955年在訪問法國時演出歌舞劇《白毛女》,當時觀看過此劇的法國作家韋科爾驚嘆它所具有的高超藝術水準,在發表于1955年10月號《北斗》中的文章中指出:“這部歌劇用一種呼籲中國民眾的覺醒的方式表達農民的疾苦。這種方式包括,中國民眾本來很喜愛舊劇,但這部作品不僅僅是舊劇裏所包含的愛情故事,還具有現實主義的內容,兼備柔情和激情,同時還有豐富的內容結構、鮮明的人物形象等。”
這並非《白毛女》首次受到海外人士的高度評價,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曾在1970年出版的英文書《中國震撼世界》中提到,自己曾于1947年三八婦女節時,在華北彭城夜晚觀看露天演出的歌劇《白毛女》,儘管當時劇中還存在一些插科打諢的因素,但是在文學成就與總體演出效果上卻已與1954年出版的修訂版劇本相差無幾:“其實這個劇本已很成熟,無須多加修改。它是由許多作家集體創作的,並廣泛地吸收了農民群眾的意見,進行過多次修改。我在解放區所觀看過的戲劇中,這是最好的,大概也是最負盛名的。”
無獨有偶,同為美國記者的雷德曼夫婦在1951年出版的英文書《紅色中國剪影》中,同樣談到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後上海的一個劇院觀看歌劇《白毛女》時,觀眾們都身臨其境的、感同身受的情景:“當演到年長的佃農談起悲傷來時,觀眾也一起哭了。地主婆説喜兒給自己做的湯不合自己的口味,往喜兒的舌頭刺進去時觀眾也同樣地發出痛苦的叫聲。對地主的好色,觀眾也咒罵了。”
而這種與劇中人物同哭同笑的情感共鳴情況也出現在觀看《白毛女》的眾多海外觀眾身上。如中國政府曾于1951年7月派遣中國青年文工團到世界各地(主要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維也納等地)進行巡演,歷時一年有餘。其中歌舞劇《白毛女》同樣感動了各國廣大觀眾,劇團所到之處均受到熱烈歡迎。正是因為《白毛女》具有令人沉浸其中的藝術魅力,因此扮演喜兒、楊白勞、大春等劇團演員在各國都受到當地觀眾的崇敬與喜愛,他們每次演出結束後都會收到觀眾的鮮花與掌聲。而扮演黃世仁、黃母等反面人物的演員卻始終收不到獻花。甚至有一次有人在劇場要獻鮮花給他們時,觀眾中有一位老太太站起來反對,還激憤地高喊著:“不要把鮮花送給壞人!”這也從側面説明《白毛女》的故事深入人心,具有感人至深的審美力量。而這種感人力量自《白毛女》劇本在1945年被創作及不斷改編之後就始終存在,並成為它的一個基本藝術特徵,更是其穿越70餘年歷史風雲變幻,在海內外得以傳播至今的藝術生命力與靈魂所在。
蘇聯、東歐各國與日本等國家都還把《白毛女》劇本翻譯成本國語言並根據本國習俗加以改編與排演,由此引發出一些有趣的軼事。像在1951年捷克文版的話劇《白毛女》中,曾出現楊白勞到地主黃世仁家後脫下大衣挂到衣架、喜兒與大春這對未婚夫妻見面親嘴的“捷克式”場景,原因在於捷克人民的生活習慣、生活細節等與舊中國的迥然不同。然而,一個受盡地主壓迫與侮辱的女子最終得到解救的精彩故事,所産生的情感震撼與審美力量卻依然在劇中存在,並不影響本國觀眾對弱勢人群的同情與對反抗壓迫剝削精神的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與50年代初在華的一些日本藝術家也曾參與到《白毛女》歌舞劇與電影等的製作中,可以説它又是一部匯聚海內外力量的佳作。除了日本士兵武村泰太郎(中國名“武軍”)曾為東北民主聯軍二縱隊第四師文工團在1947年演出《白毛女》時演奏音樂,小野澤亙(中國名“肖野”)、森茂于1945年在抗敵劇社為張家口演出歌舞劇《白毛女》做舞美設計和宣傳工作,以及剪輯師岸富美子(中國名“安芙梅”)、錄音師山本三彌(中國名“沙原”)參加了電影《白毛女》的攝製工作之外,二戰後留在東北的日本工人還曾組成鶴崗劇團,在1952年用日語演出歌劇《白毛女》並獲得主管部門的認可。這些日本工人返回日本後,就成為傳播《白毛女》的一股重要力量。
而歌劇劇本《白毛女》最早被海外國家譯介發行的版本正是由稻田正雄翻譯的、在1952年由東京未來社出版的日語版。電影《白毛女》同年被帶到日本並在很多地方陸續放映,這部被認為“真的很中國”的電影如同歌劇《白毛女》一樣,亦對許多日本觀眾産生很大觸動。魯迅的日本好友內山完造在1952年10月曾寫過一篇文章《從〈白毛女〉想起魯迅》,直接把“白毛女精神”等同於“魯迅精神”:“我為喜兒(白毛女)戰勝一切痛苦和災難活下來那種人的活力的堅韌而驚嘆。我越想到白毛女為生存而進行的苦鬥,對於黃世仁等的兇惡殘暴日益強烈的憤怒,便越情不自禁地燃燒為火焰。……我認為作品裏極其鮮明地表現了魯迅精神。不,僅僅這樣説還不明晰,據我看,甚至可以説‘白毛女便是魯迅先生’。”
演集劇團在1954年首次排演歌舞劇《白毛女》並把它搬上日本舞臺,尤其是松山芭蕾舞劇團把經過改編創作出的芭蕾舞劇《白毛女》在日本進行公開演出的劇目,為多年來中國紅色經典《白毛女》在日本,甚至是世界各國的廣泛傳播、接受作出無法磨滅的重要貢獻。
“三個喜兒傳佳話,異國姐妹同臺人”
1955年松山芭蕾舞團把根據電影《白毛女》與歌劇劇本《白毛女》進行改編的芭蕾舞劇《白毛女》搬上舞臺。電影《白毛女》最早觸發了清水正夫與松山樹子等日本藝術家的改編靈感,他們認可受盡壓迫剝削的中國農民的反抗精神,並對他們的悲劇命運産生同情,正如前者多年後回憶他在1952年東京江東區的一個小禮堂觀看電影后所産生的心理震撼:“打動我們的心弦並使我們難以忘懷的是受壓迫的農民們如何去求得自己國家的解放這一主題……我們對於受壓迫的人們求得解放,感到了強烈的共鳴,對這個戲的主人公喜兒也懷有深切的同情。”
這部電影也恰好契合當時日本在抗美援朝背景下,廣大民眾反抗美國依據《日美安保條約》而沒收他們的土地當作遠東戰略基地的很多舉措,由此在日本社會掀起追求真正獨立、和平運動高潮的社會反抗情緒;而且喜兒翻身得解放的境況顯然也與當時日本婦女社會地位極其低下還經受性別歧視的現狀形成鮮明對比,因此把《白毛女》改編成一部謳歌婦女解放的日本人作品就成為他們要實現的主要藝術目的。而《白毛女》中一個一頭黑髮的青春女孩變為可憐的“白毛女”的跌宕起伏構思與曲折精彩的故事情節,均使它非常適合被改編成芭蕾舞劇,所以當排演完芭蕾舞《夢殿》,正在為尋找新劇目而苦惱的松山樹子看完電影《白毛女》後,眼前立即一亮,産生了找到目標的喜悅:“我們正到處搜尋具有日本人情味的芭蕾舞素材,所以當《白毛女》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感到:‘啊,這不正是我們要找的嗎?’”
他們在給中國戲劇家協會寫信並在收到對方郵寄來的《白毛女》劇本等資料後,開始進行翻譯、改編等多項工作。在經過長達一年多時間的準備與克服當時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障礙之後,三幕芭蕾舞劇《白毛女》于1955年2月在東京日比谷會堂進行首演。當松山扮演的穿著銀灰顏色的、袖口下襬被剪成鋸齒形服裝的“白毛女”出現在舞臺上,並伴隨由日本著名作曲家林光改編的芭蕾舞音樂翩翩起舞、表達出內心的悲傷與仇恨時,擠滿禮堂的觀眾都追隨著她的一舉手一抬足,深深地沉浸其中,還跟隨故事的展開而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動的淚水。尤其是在演出結束後,臺下觀眾眼中所含的熱淚、響起的雷鳴般掌聲與此起彼伏的“再來一個”的歡呼聲,都説明他們的演出取得巨大成功。此後,不但日本的一些報紙登載照片並報道演出情況,而且時任中國中央戲劇學院院長的歐陽予倩曾致電祝賀,指出改編後的芭蕾舞《白毛女》可以促進中日兩國的交流。的確如此,歷史已經證明,芭蕾舞劇《白毛女》多年來成為中日兩國友好往來與交流的一個重要橋梁。
松山芭蕾舞團的《白毛女》在日本演出近40場後,于1958年3月到中國進行首次訪華演出,這也是對周恩來總理此前殷殷期望的一個回應。早在1955年6月,松山樹子參加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會間曾與大會理事會副主席郭沫若交談並收到訪問中國的邀請。她在參訪北京後,到蘇聯莫斯科大劇院觀摩學習芭蕾舞期間,收到周恩來總理從北京通過中國駐蘇聯莫斯科大使館發出的邀請,歡迎她到北京參加國慶節觀禮活動。
1955年9月30日,松山樹子參加在北京飯店舉行的國慶招待會。正是在這次招待會中,周恩來總理促成了中日兩國三位“白毛女”齊聚一堂、把手言歡的一段佳話。當時是在宴會進入高潮後,周總理先是對現場的外國記者説:“現在宣佈一件重要事情。”然後帶著兩位中國女演員走到松山樹子面前停下,向她伸出手並向參加宴會的全體來賓們介紹她:“朋友們,這裡有三位‘白毛女’,這位是在延安第一個扮演歌劇 《白毛女》的王昆同志;這位是演電影《白毛女》的田華同志,這位是日本朋友松山樹子先生,松山芭蕾團已把《白毛女》改編成芭蕾舞劇在日本上演了。”三位“白毛女”聽後非常激動欣喜地擁抱在一起,這既成為她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之一,又使她們結成深厚的國際友誼。而且更令人感動的是,周總理在與她們合影拍照時堅持站在旁邊的位置,還打趣説:“你們三個‘白毛女’不能分開!”
在時隔22年後,王昆在1977年5月跟隨天津歌舞團到日本訪問演出期間,曾拜訪松山芭蕾舞團,見到松山樹子等人,這兩位已經年過半百的“白毛女”再次相聚在一起。她們回憶起當年周總理介紹松山樹子的情景,王昆在感慨之餘還寫出一首中國古典詩贈送給松山樹子:“五五北京初識君,總理牽手且叮嚀;三個喜兒傳佳話,異國姐妹同臺人。七七東京杜鵑紅,鬢絲幾縷又重逢;君舞雪花我伴唱,猶聞總理擊節聲。”兩年之後,即1979年日本舉行第三屆中國電影節期間,田華到日本參加活動,這位電影版的“白毛女”扮演者也受到日本觀眾的熱烈歡迎。兩位中國“白毛女”的訪日活動,同樣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一個見證。
“芭蕾外交”:中日外交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時間再回溯到1958年“三八”婦女節那天,松山芭蕾舞團帶著芭蕾舞劇《白毛女》抵達中國,開始訪華行程。劇團從9日到11日期間在北京的天橋劇場進行綵排,于13日正式公演。當時北京觀眾紛紛連夜排隊買票觀看,並在看後盛讚芭蕾舞《白毛女》。當時北京也在上演王昆主演的歌劇《白毛女》、中國京劇團的京劇《白毛女》等,4個同時上演的版本由此形成“《白毛女》熱”盛景。然而遺憾的是,周總理當時因離京去外地開會,所以未能到場觀看松山芭蕾舞團首次來華演出的芭蕾舞《白毛女》,不過陳毅、郭沫若、丁西林等人與首都各界藝術家們在觀看該劇後都給予高度評價,《人民日報》在首演第二天也進行了報道。北京文聯禮堂在3月21日舉行盛大聯歡會,當時在京扮演“白毛女”的、包括松山樹子在內的5位女演員得以聚在一起歡談併合影。郭沫若、田漢等人也即興寫出詩歌以記錄這一盛況。
同年3月24日,松山芭蕾舞團所有人員從北京坐上去重慶的火車,開始奔赴重慶進行演出。他們在重慶演出圓滿結束之後,又到武漢進行訪問演出,最後一站到上海,在5月1日離開中國返回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共計演出28場,不僅受到中國各地觀眾的歡迎,同時還受到留在中國的日本人的歡迎,松山芭蕾舞團的訪華演出可以説是對後者思鄉之情的一種慰藉。
松山芭蕾舞團第二次大型訪華演出是在1964年。9月22日到12月12日期間,松山芭蕾舞團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南京市人民大會堂、廣州大會堂等地演出38場。這次訪華的特殊照顧之處在於,他們在中國多個城市巡演期間,始終有北京舞蹈學校、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團演員13人、中央樂團54人陪同,目的也是為了借鑒、學習松山芭蕾舞團把古典芭蕾舞改編成現代芭蕾舞劇的寶貴經驗。如果説日本芭蕾舞劇《白毛女》是松山樹子、清水正夫等日本藝術家汲取中國歌劇、京劇等藝術精髓、灌注日本精神之後而成的佳作,那麼中國芭蕾舞劇《白毛女》則是在吸收中日文化藝術精華之後産生的一個碩果,表明中日文化始終是在互相交流與彼此交融中共同進步與發展。
松山芭蕾舞團在1966年進行第三次訪華演出,組員在觀看上海舞蹈學校的芭蕾舞劇《白毛女》後還多次參加座談會,交流彼此的演出經驗。他們在1971年9月20日到12月2日進行第四次訪華演出,中日兩國的芭蕾舞劇《白毛女》再次得到直接交流,進行藝術切磋,二者在藝術水準上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1972年7月,上海芭蕾舞劇團在中日友好協會秘書長孫平化的帶領下訪問日本並演出《白毛女》,同年9月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芭蕾外交”事件。“芭蕾外交”事件不但成為中日外交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使中日人民永遠銘記《白毛女》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此後,芭蕾舞劇《白毛女》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代表團訪問海外國家的一個經典文化節目,從20世紀80年代直至今天仍然活躍在世界各地的舞臺上。
“《白毛女》是一部一流的歌舞劇,幾乎擁有所有的傳統技巧”
《白毛女》劇本的英文版,最早是由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與戴乃迭夫婦根據1954年重新出版的《白毛女》修訂版進行翻譯,並在1954年由外文出版社首次出版發行的。西裏爾�白之在1963年的文章《中國共産主義文學:傳統形式的堅持》中認為,在1940年代的中國歌劇中,“一種得到高度稱讚的創新形式是秧歌劇,即把陜西農民的‘插秧歌’與多種通俗歌曲形式一起融合到話劇中,《白毛女》的成功激發了大量的模倣者。”
首次收錄《白毛女》英文版劇本全文的書籍則是1970年由沃爾特�梅澤夫夫婦共同主編的《共産主義中國的現代戲劇》,不僅收錄楊憲益夫婦翻譯的《白毛女》,還收錄他們翻譯的魯迅的話劇體小説《過客》、現代京劇《紅燈記》等共計9部中國戲劇作品。該書的“導言”稱讚這些劇作各有優點,尤其是高度讚揚《白毛女》繼承並改造中國舊劇的文學成就:“作為戲劇,《白毛女》是一部一流的歌舞劇,幾乎擁有所有的傳統技巧……本劇的確承襲了中國傳統的大團圓結局,在最後一場戲中紅軍到來,拯救了每一個應該得到拯救的人。”
而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在1973年與1974年期間曾出現過兩篇專門評論歌劇和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文章。其中時任美國緬恩大學助理教授的諾曼�威爾金森在1974年發表的文章《〈白毛女〉:從秧歌到現代革命芭蕾舞》中梳理了中國秧歌劇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延安革命文藝對它的改造過程,認為《白毛女》是最成功的秧歌劇,而且讚揚“《白毛女》很好讀,情節發展清晰且故事推進很快。”其中喜兒與其父楊白勞的性格特徵都被細緻描繪出來,就算是反面人物黃世仁的形象也令人可信,它堪稱是共産主義戲劇史中的一個里程碑。對於1965年的芭蕾舞劇《白毛女》對此前秧歌劇的巨大改編,作者認為楊白勞因為保護家庭和女兒被黃世仁他們槍殺的情節比前者自殺更值得仔細描繪,而且在芭蕾舞中增添民謠、合唱與人物的現代服裝打扮等,反而有助於這種新式“混血”的中國現代革命芭蕾舞劇的成功。在舞臺演出實踐中同樣非常成功。
到1975年,美國人馬丁�艾本主編了當時的暢銷書《共産主義中國的五幕戲劇》,其中依然收錄楊憲益夫婦翻譯的《白毛女》和《紅燈記》兩劇,並在當時美國觀眾已經較熟悉《白毛女》芭蕾舞劇的情況下,對其評價同樣持肯定與讚揚態度,同樣可從該書的“導言”中看出。“導言”以批評西方社會對中國長久以來的誤解與誤會為開頭:“在超過四分之一的世紀中,中國被(西方)誤解。”編選者因此大聲呼籲:“西方人應該避免出現那些支援仍狂熱地污名化與預設醜化當代中國文學與藝術的氛圍。我們並非在處理原始部落中帶有異域風情的、令人著迷的儀式,而是在處理一種文化傳承,它本應該就是人類整體文化傳承的一個組成部分。”編選者在附於《白毛女》劇本前面的簡介與評價中特地提到芭蕾舞劇《白毛女》所出現的很多變化,認為“無論採用哪種形式,《白毛女》都對人們具有潛在的娛樂性和教育意義。”承認不同表演形式的《白毛女》均擁有高度的文學價值與成就,這也表明《白毛女》在西方社會得到肯定與讚揚,為其後在海外的繼續傳播奠定堅實基礎。
除了《白毛女》,以《青春之歌》《紅旗譜》《創業史》等為代表的中國紅色經典在海外不斷得到重評,且被賦予契合不同歷史時代的新內涵與新特徵。這説明它們在海外始終得到廣泛傳播並被廣泛接受,成為持續傳播新中國形象的重要媒介與窗口。更重要的是,這説明只有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才能跨越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這也是這些中國紅色經典在海外得以持續傳播給我們的啟示。
(作者:張清芳,係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河北師範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