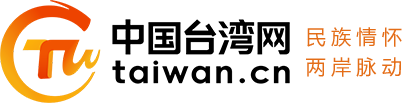文學與電影是否開掘了疾病某種深層的意義?
文學與電影是否開掘了疾病某種深層的意義?
在病毒籠罩的陰影下,仍有愛情在燃燒
本報記者 陳熙涵
2020,一個“愛你愛你”的年份,誰也沒想到會在全民抗擊疫情中開始。當疫情遇到愛情,會發生什麼?在《霍亂時期的愛情》的結尾,加西亞�馬爾克斯讓年老的阿裏薩和費爾米娜擁抱著躺在一艘內河航船上,船頭豎起了代表了霍亂的黃旗,宣告著他們再也不上岸了。當船長問他們愛了有多久,阿裏薩説:“53年7個月11天以來的日日夜夜,一生一世。”在這個結局裏,在死亡抵達之前,愛情熬出了頭。
像這樣在災難面前,在死亡籠罩的陰影下,愛情燃燒著生命之光的文學藝術作品並不少。這是因為愛與死,從來就是藝術永恒不變的主題。在人類歷史上,如果説有多少次令人驚懼的傳染性疾病流行,那麼在後世也就留下過多少與之有關的經典之作,而愛情總是那中間被人深深銘記的部分。
這也多少解釋了一些經典的改編自霍亂文學的電影為何都在愛情這個點上進行深耕開掘,在大開大闔與生死之際,人與人之間的那一份情感上的關聯,使那些要命的疾病開始具有了某種深層的美學意義。
誰説愛戀不是一場霍亂
阿裏薩的母親説:“我兒子唯一得過的就是霍亂。”事情真是這樣嗎?他兒子53年對費爾米娜的愛戀不是一種病嗎?心理學家弗蘭克�托裏斯就認為相思的狀態與精神疾病接近,癲狂、抑鬱、迷茫、狂躁、妄想是它的典型症狀。
《霍亂時期的愛情》裏,阿裏薩的母親以為兒子患了霍亂,其實是他對費爾米娜的一見鍾情。阿裏薩把情書遞給費爾米娜等待回信的日子裏,茶飯不思夜夜難眠,“他腹瀉、吐綠水,暈頭轉向,還常常昏厥”。馬爾克斯在這故事裏再明確不過地建造了霍亂與愛情的聯繫:真正的愛情與霍亂很相似。也有人説,“馬爾克斯用令人恐懼的霍亂影射愛情,似乎想告知人們,愛情雖然甜美,但它折磨起人來,會讓人生不如死。但是,不經過這樣的生死考驗,誰也無法得到真正的愛情。”
“我對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沒能為愛而死”,這句出現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的高光名句,是這個以魔幻出名的作家的現實分水嶺。《霍亂時期的愛情》是馬爾克斯獲諾貝爾文學獎(1982年)之後創作的作品,其原著的首印量是馬爾克斯另一部經典代表作《百年孤獨》的150倍,光是中文版的銷量就輕鬆突破百萬冊。據稱,馬爾克斯有一天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一對故地重遊的老人,竟被載他們出遊的船夫用槳打死了,為的是搶走他們身上帶的錢。後來,新聞爆出他們是一對秘密情人,40年來一直一起旅行,但他們各自都有幸福而穩定的家庭,且子孫滿堂。
之後,馬爾克斯便以這對老人為切入口,糅合了自己父母年輕時的愛情故事寫出了《霍亂時期的愛情》。它講了一段跨越了53年的不可能的愛情,以及人面對漫長時間的孤獨感,而哥倫比亞的歷史,如戰爭、霍亂則穿插其中,營造出人在身處時代時的宿命:縱使分離是絕望的,竟成了愛情唯一的出路。
我們可以看到,《霍亂時期的愛情》雖含有“霍亂”兩個字,但其實霍亂時期只是愛情發生的背景,死亡隨時可能會發生,森林被輪船的發動機所吞噬,海牛絕跡,但是愛情還在持續。這是一個多麼鼓舞人的暗示呵,疫病從來都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先於我們而來,即使我們不在了,它還可能繼續存在。死亡的威脅掩飾不了生命的熱力。加繆説:“鼠疫是什麼呢?鼠疫不過就是生活罷了。”
人類什麼時候離開過這些呢?
瘟疫面前,愛情只能是慰藉麼
生老病死前,愛情總要被放大。霍亂時期的愛情,死亡才可以為重燃的愛火定格,所以沃特一定要死。不然,災難過去之後的日子,被忽略的醜陋和缺憾依然會不失時機地泛起。只有死去,這份愛意才得以永垂不朽。
在中英合拍電影《面紗》中,老修女對頹喪的吉蒂説:“職責就是在手臟的時候去洗乾淨。”日久不一定生情,你一時衝動以為的愛也不一定是愛情。為什麼你常常覺得他(她)並非那個對的人,因為你總是想從對方身上找到某些他(她)從來都不具備的品質,而不是他(她)與生俱來的閃光之處。這使得愛總在遙遠的附近,愛就藏在面紗的後面。
電影《面紗》同樣講述了一段霍亂中的感情。上世紀20年代,一對年輕的英國夫婦來到中國鄉村生活,在這個美景如畫又霍亂肆虐的偏遠小城,他們經歷了在其故鄉英國舒適生活中絕對無法想像和體驗的情感波瀾,並領悟到了愛的真諦。
故事以女主角開篇。吉蒂是一個在浮華社交圈中如魚得水的姑娘,她美貌但卻十分虛榮,她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嫁給了沉默寡言的醫生、細菌學專家沃特�費恩。婚後,沃特再把吉蒂帶到了上海。兩人終因性格差異和缺乏共同語言而生出嫌隙。吉蒂和迷人的已婚男子查理�唐森發生了婚外情……
“莫去掀起那描畫的面紗,那蕓蕓眾生,稱之為生活”。電影《面紗》改編自英國小説家毛姆的小説《華麗的面紗》。據説,毛姆小説的靈感便來自雪萊這首十四行詩。不忠被發現後,沃特給吉蒂兩種選擇:要麼隨他去中國一個霍亂肆虐的地方救治病患,要麼讓唐森離婚和吉蒂結婚。他之所以敢這麼説,是因為吃準了唐森不會放棄聰明能幹的妻子,更不會放棄總督的進階之路去選擇和吉蒂在一起。
不出所料,吉蒂遭到了拒絕。她沒得選擇,只能跟丈夫一起去。電影其實是從這裡才真正意義上開始了:她沒想到,這個代表著死亡之地的湄潭府,才是她生命的真正開始。
眾所週知,毛姆的尖刻是出名的。在《華麗的面紗》結尾,沃特至死也沒有得到吉蒂的愛情。瘟疫面前,愛情只能是慰藉,而不是救世的力量,才是毛姆想説的。不僅如此,毛姆還祭出最透徹的臺詞:女人不會因為男人道德高尚而愛上他。
這對於期待著美好結局的觀眾是不是很幻滅?但很抱歉,毛姆説這就是生活的真相。
電影《面紗》顯然試圖對此作出一些改變,給影片添點兒溫情。但正因為這部分改變終究使該片顯得面目模糊。原著中對沃特的刻畫著墨並不多,特別是到了湄潭府後的他更像一位隱形了的男主角。而電影則將這個人物的悲劇性刻畫得相當完整。首先,他對吉蒂的一往情深是盲目的,他並不知道她想要什麼,自己又能給她什麼,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表達。但他並不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他全程旁觀自己的妻子接受情人的背叛這一令人心碎的現實,帶著一身的難堪和絕望,跟他前往疫區。
到了疫區後,沃特“絕世好男人”的戲碼紛紛上演了。他不但表現出作為醫生的義無反顧,同時在妻子的心裏不斷播撒後悔。就此,戲路開始向好萊塢傳統套路一路飛奔。與此同時,在這個充滿死亡氣息的地方,吉蒂這個虛榮的女孩在救助幫護中褪盡了一個貴族小姐的精緻利己主義,她早已不再是派對王后,她與沃特重新開始打量起彼此及她們的婚姻。
電影裏一筆帶過了毛姆小説中從不曾回避的尖銳——沃特的遺言。在遺言中間,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他把吉蒂帶到湄潭府是有意讓她在此感染霍亂而死,而得到背叛的他也早已心如死灰刻意尋死。而電影中,則是兩人重新認識了對方,要不是沃特不幸染病去世,他們隨時就要開始重新相愛。但小説裏,沃特是在做實驗時被感染的,他一直在拿自己的身體做試驗,由此可以看出是他殺死了自己。他的心碎了,再也沒能拼起來。
霍亂時期的愛情,死亡才可以為重燃的愛火定格。所以,小説也好,電影也罷,沃特一定要死。不然,災難過去之後的日子,被忽略的醜陋和缺憾依然會不失時機地在吉蒂的婚姻生活中泛起。只有死去,這份愛意才得以永垂不朽。
可以説,毛姆在《面紗》裏對沃特與吉蒂從冷漠、隔閡、彼此厭棄,到在異國極端環境裏的生活狀態,都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愛情電影套路,他甚至對於完滿的形式感沒有任何追求。在原著中,與複雜的時代特徵比起來,愛情從一開始就顯得無足輕重。而電影則抓取了毛姆對人性刻畫的部分,擯棄了原著中近乎殘忍的現實色彩。當然,這麼做顯然更切合觀影的心理期待——生離死別之際,兩個人終於揭開了感情世界的面紗,吉蒂也就此完成了一個女人的自我成長,走向了田野,走向了獨立。
危機常考量藝術家對人類情感與道德的透析能力
作品讓男主人公身處屋頂的意義在於,通過一個個俯瞰鏡頭,為這場發生在法國17世紀的瘟疫提供了一個鮮有的高空視角。更深層次的意味在於,逼視種種發生在人心深處的疫變:疾病帶給人類的終極考驗,不僅是對疾患的警覺,人與人的疏離和冷漠才是真正的病毒,而人類社會最大的恐懼便是人性的喪失。
説到在文學圈享有盛名的疫變電影,《屋頂上的輕騎兵》一定是個繞不過去的名字。十多年前,法國文學家讓�吉奧諾的這部作品之所以在中國文青中間口口相傳,不惟它的小説好看,在很大程度上還得益於它的電影,得益於電影中女主角扮演者朱麗葉�比諾什和奧利維耶�馬蒂爾內在該片拍攝期間假戲真做、共墜愛河的傳奇故事。
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30年代,來自義大利的騎兵上校安傑洛�帕蒂,因被童年好友的出賣而身陷囹圄,不得不逃亡到法國南部普羅旺斯,更加不幸的是他遇上了該地區爆發滅絕性的霍亂。城內到處是屍體,烏鴉從充滿死亡氣息的窗口飛向樹梢,遠處的火光焚燒著成堆的屍體,天空是恐怖的陰霾,士兵們設置了重重障礙,阻止外來人口進入瘟疫區,並設置了隔離區,將來自疫區的人關押在內。
迫於無奈,安傑洛躲避在法國鄉間哥特式和羅馬式建築交錯的廣袤的屋檐上,成為了一名名副其實的屋頂上的輕騎兵,俯瞰著腳下發生的一切——尊嚴與良知在死亡的威脅下已經泯滅,猜疑與自相殘殺成就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劇。
文學史上,危機常考量藝術家對人類情感與道德的透析能力,以及他們將通過怎樣的切入角度來展開各自敘事。在讓�吉奧諾的筆下,讓男主人公身處屋頂的意義在於,通過一個個俯瞰鏡頭,為這場發生在法國19世紀的瘟疫提供了一個鮮有的高空視角。其更深層次的意味在於,通過安傑洛的觀看,描摹出正在發生於人心深處的疫變,從而指出疾病帶給人類的終極考驗——我不僅要對疾患保持警覺,更要警覺人與人在災難中的疏離和冷漠,這才是一種真正的病毒!就像該書出版方、法國伽裏瑪出版社在內容提要裏所寫的:“我們只看見一個年輕的輕騎兵在層出不窮的悲劇中長途跋涉……我們會認為,司湯達和巴爾扎克找到了他們的接班人”,這是許多經典文學作品常常具有的特質——一部傑作因一個人成為了永恒存在。
為躲避大雨,安傑洛從屋頂的天窗爬進了一戶農家,遇見了守在疫區苦苦等待丈夫歸來的侯爵夫人寶琳娜。銀色燭光下,侯爵夫人長裙曳地,端莊而美麗。見到從天而降的上校,夫人處變不驚,給了他食物和水,也給了他力量。長長的法式餐桌上,夫人談笑風生,優雅自若,可又有誰知道她不動聲色地在桌布底下暗扣著一把對準上校的手槍……
輕騎兵總在給母親寫信,“你教會了我怎樣生活。我每天因此而感謝您……為了與你重新見面,我要獨自奮鬥,讓義大利獲得解放。”這與其説是寫給母親的信,不如説是寫給自己,在安傑洛的心裏有一個兼濟天下的理想,這使他心裏始終裝著別人,為了救治病人他從不顧及自己。他許諾可以幫助寶琳娜越過封鎖回到北方尋找她的丈夫。就這樣,他一路護送著她,他們騎著馬在廣袤的草原上賓士。
這註定是安傑洛與寶琳娜的故事,發生在澎湃的革命浪潮之下,發生在霍亂爆發的年代。有一天,他們在一座古堡停留,他生了溫暖的爐火,燒茶燙酒,她為他穿上他們第一次見面時的裙子。溫暖的爐火旁,她説:“你真的很古怪,你從馬諾斯跟著我,不計時間,可是現在,你卻匆忙收拾行李,好像要逃跑一樣”,他只是報以無言的微笑,以優雅和飽含傷感的眼神回絕愛意的滋長,他説:“原諒我。”他不能承諾什麼,因為一個隨時準備去死的人不配擁有愛情,更不能許下承諾。
瘟疫如暴風雨般襲來,寶琳娜感染了霍亂從樓梯上墜下,掙紮在死亡線上。這時,安傑洛又一次改了自己的行程,他冒著被感染的危險,用鄉間醫生的土辦法用酒精揉搓侯爵夫人發紫的身體,在幾近絕望的邊緣,救了寶琳娜的命。瘟疫帶給世間苦難的同時竟也成就了人世間最真摯、美麗、不摻雜肉欲的愛情。而這愛情最終沒有成為羈絆和互相佔有,秉持著高貴的騎士精神,安傑洛一路護送寶琳娜找到了年邁的、富有的丈夫。而他自己則選擇策馬離開,奔向了火熱的革命……而寶琳娜的生活雖恢復了往日的寧靜,但在她的內心深處,安傑洛已經無法被忘卻,隔著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她常常遠遙著安傑洛奔向的地方。
與《霍亂時期的愛情》有些相似,電影《屋頂上的輕騎兵》描摹的對象也絕非疫情本身,在講述一個霍亂流行時期的動人愛情故事時,流行疫病的象徵意義與隱喻,被極大地彰顯出來。看原著小説,也許這種感覺會更強烈,感染霍亂的情境在讓�吉奧諾的筆下都很不寫實,比如安傑洛和病患接觸,幫他們擦身治療,甚至在被霍亂滅門的大宅子裏生活了一段時間,卻從未被感染。霍亂放大了自私、仇恨、恐懼、被動等特徵,只要具備以上特徵的人,都接連被霍亂放倒。而安傑洛蔑視傳染,反而安然無恙。所以,作者想説的是,製造了這場疫情的是對霍亂的恐懼,而非霍亂本身。事實上,作者讓�吉奧諾在一次採訪中證實了這種看法,他説:“霍亂就像一個化學元素,讓最卑劣和最高尚的情感,赤裸裸地彰顯在我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