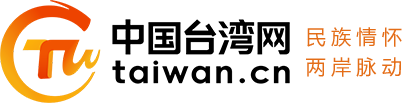學習故事丨胡繩:打開煙幕,一頭撞進哲學神殿裏去
【編者按】
希臘神話説,普羅米修斯盜天火照亮塵世。
馬克思説,我就是普羅米修斯!
在20世紀上葉的中國,也有這樣一群普羅米修斯:他們將馬克思主義的光亮帶到黑暗不知方向的東方古國,用理論照亮新中國的前路;
他們將信仰的星星之火,燃成銳利的理論武器,燎原舊世界,催生新中國。
我們稱呼他們為:追光者。
他們追逐的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穿過了舊中國的陰霾,正在一代代共産黨人的呵護下,飛向時代前沿,點亮新時代的光榮夢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的,“馬克思給我們留下的最有價值、最具影響力的精神財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猶如壯麗的日出,照亮了人類探索歷史規律和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回望來路,我們同樣不能忘記一路用理論守護中國穩健生長的他們。
一、敢想敢做,拋棄學校的刻板説教
還記得語文課本裏的《想和做》嗎?
“有些人只會空想,不會做事。他們憑空想了許多念頭,滔滔不絕地説了許多空話,可是從來沒有認真做過一件事。”
“也有些人只顧做事,不動腦筋。他們一天忙到晚,做他們一向做慣的或者別人要他們做的事。”
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胡繩。
正如他筆下所寫,沒有空想,沒有死做,這個叛逆的青年甫一接觸社會,就把敢想敢做的闖勁發揮到了極致。
那是1932年的1月28日,上海正下著大雪,四處冰凍。
跪在雪地裏堅決抗敵的上海十九路軍,沒有等來他們的後援。即便他們缺少物資,穿著單衣短褲,可相比于天氣,更冷的是人心。
他們阻止了日軍海軍陸戰隊佔領淞滬鐵路防線,卻沒能阻止後方“停止進攻”的命令。
將士們懊惱地放下了手中的步槍,熱血的百姓們放下了趕著做出來的土制手榴彈。國民黨政府這道“忍辱求全”的急電,遠勝日軍的槍炮,終於擊潰了中國人自己的防線。
一位將士忍受不了這樣的屈辱,抱著步槍衝向日軍陣地,隨著對面的幾聲槍響,倒地不起。他的血染在皚皚的雪地上。
聽聞這一切的胡繩,感覺自己的心被刺痛了。
那一年,他14歲。
可早慧的他早已看穿社會大勢——這一切的原因,僅僅在於國民黨政府正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所以對日繼續執行不抵抗政策。
比戰敗更讓人無力與憤怒的,是本有機會,卻不戰而敗。更何況,這一場戰爭本就是日方挑釁,殺害中國警員,還提出“道歉、懲兇、賠償”等無理要求。
屈辱與憤怒在胡繩的心中留下印記,他開始思考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三民主義”救不了中國,散佈謠言污衊馬克思主義和共産黨的國民黨,更趕不走侵華日軍。
抱著這樣“叛逆”的思想,胡繩開始接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共産主義ABC》等“禁書”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從瞿秋白的書中了解到共産黨正經歷的鬥爭與創造的理論,也知道了蘇聯在世界被壓迫人民鬥爭中的地位。
一顆真切的嚮往之心被點燃了。
想了就要去做,“北漂”青年的“叛逆”之旅,開始了。
二、“北漂”“上漂”,撞進古怪奧妙的哲學神殿
16歲,他來到北京,進入北大哲學系,成了“少年大學生”。
他渴望在這裡找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找到救國救民的途徑。
然而大學裏的哲學課堂,“教授夾著大皮包上來了,講的呢,不外是什麼最高的絕對的‘善’”,是一大串亞裏士多德、休謨、康得、黑格爾的人名。
“講到玄妙得連教授自己也未必相信的時候,講壇下十幾隻耳朵都張大了。”
但張大的耳朵裏,不包括胡繩。
他可不是個死讀書的學生。正如後來他在自己的著作《哲學漫談》中所寫,“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的歷史把哲學這個東西遮上了一重重的煙幕,弄得它變成了一個古怪奧妙的神殿,我們要討論哲學,就不得不打開這些煙幕,一直撞進這神殿裏去。”
要撞進哲學神殿,就不能跟著老教授慢吞吞的步伐,胡繩開始“揀可聽的課聽之,不愛聽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圖書館找點書看看”。
這段時期刻苦的讀書自修,為他後來的哲學之旅奠定了紮實的理論基礎。
一年後,胡繩又來到風雲際會、各色思想潮涌的上海,他想在“神殿”裏探尋更多的寶藏,也想把“神殿”裏的煙幕打開,讓更多的人看看裏面的奧妙。
歷史很快給了他機會。
以寫作為生的他,無意間偶遇著名的馬列著作翻譯家張仲實先生。先生邀他給“青年自學叢書”寫一本書,並出了“新哲學的人生觀”這個題目。
這正是他想説的!
很快,《新哲學的人生觀》出爐。在書中,他打破了常規哲學教材的敘述脈絡,從哲學角度的“人是什麼”談起,繼而講到哲學怎樣處理人生觀的問題。
然而,只是鼓勵青年們樹立積極的人生觀還不夠,胡繩渴望將自己在神殿中找到的寶藏傾馕而出。
於是,《哲學漫談》問世了。他以通信的方式,把哲學從教授的講壇中解放了出來,到達了社會大眾,並深刻改變著他們的認識。
例如,書中提到“哲學儘管討論的是最高的概念和一般的法則,卻並不能因此就證明哲學是空洞玄妙的。”
為了講解這個“最高的概念”,胡繩化抽象為具體,“這是張三、那是李四,這是趙德勝、那是黃阿虎,每個人都有他的特殊的形狀神氣,……但是一説到‘人’,我們就把他們各自的特點除外了,構成了一個‘人’的概念。”
許多哲學家認為,哲學上的概念和法則,因為是最高的、最一般的,所以是用“肉眼”觀察不到的,我們只有靠“純理性”才能把握到它們。
對於這樣把哲學複雜化、神秘化的觀念,胡繩也在書中用通俗的語言給予了批判,“倘然這樣説是對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説:並不是因為先有了張三、李四、趙德勝、黃阿虎才産生‘人’的概念,‘人’的概念是在哲學家的頭腦裏空洞地構成的。——這真是什麼話啊!基督教的聖經説上帝創造了人,難道這些哲學家是‘上帝’嗎?”
寥寥數語,便解釋清楚了物質與意識的辯證關係。這樣大眾化的語言,讓更多的普通人得以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哲學,繼而運用哲學。
過去,太多的人把哲學講成了深奧不可捉摸的東西,他渴望打開這些籠罩在哲學之上的煙幕,讓人們看看它的真容,讓進步青年們借助這實用的理論,看清而今的形勢,找到人生的方向。
從想到做,這個“叛逆”青年把神殿裏的煙幕打開,循循善誘地抱出了馬克思主義,也為今後的青年們,抱出了一個光明燦爛的未來。
(文/雁丘 朗讀:田萌 音頻製作:曾慧 視頻製作:張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