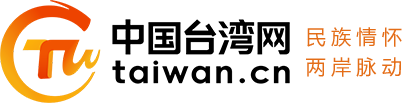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背心院士”高伯龍:穿著五塊錢的背心,幹著上億元的大事

△2001年,高伯龍正在進行科研工作
陽光透過窗戶,照在兩隻緊緊握著的手上。
這是兩隻普通而又蒼老的手。和許多老年人的手一樣,粗糙、佈滿老年斑。
這又是兩隻極不普通的手。它們從20世紀70年代“握”到一起,就再也沒有鬆開。它們和更多雙手一起,開闢了具有中國自主智慧財産權的鐳射陀螺研發道路。
這兩隻手的主人,一位是89歲的高伯龍,一位是82歲的丁金星。

△2017年9月8日,高伯龍院士在病房堅持查閱資料。何書遠 攝
這是2017年夏季的一天。此刻,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防科技大學教授高伯龍的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倚靠在病床上,他無比惋惜地對丁金星説:“老丁,新型鐳射陀螺的研製,我怕是完不成了……”話未講完,他的眼眶裏已噙滿淚水。
丁金星也哽咽了,淚水順著臉頰無聲滑落。他沒有説話,只是更加有力地握住高伯龍院士的手。
“這是我們相識近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落淚……”高伯龍院士去世兩年後,當時的情形依舊清晰地烙印在丁金星的腦海中。
當年,他們意氣風發,戰鬥在湘江之畔,創造了世界鐳射陀螺領域裏的“中國精度”。
如今,高伯龍院士已經離開。他那眼底的熱淚,仍留在“老搭檔”丁金星心中。那句“我怕是完不成了”,也成了高伯龍院士與畢生奮鬥事業的訣別書。
回望這位中國“鐳射陀螺奠基人”的一生,高伯龍院士就像一束能量高度集中的光芒,照亮著鐳射陀螺自主創新的征程。
光之魂:報國之志從未偏航
“一個人的志願和選擇
應當符合國家的需要”
陽光透過層層綠葉,將點點光斑灑在一座外觀極為普通的樓房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這座樓是一個沉默的存在。
這裡,便是如今已名滿天下的鐳射陀螺實驗樓。它還有一個頗具神秘色彩的代號——208教研室。
這裡,也是高伯龍院士奮鬥了一輩子的“戰場”。有關他的一切,都可以從這座樓講起。
20世紀60年代,美國研製出世界上第一台鐳射陀螺實驗裝置。鐳射陀螺,被稱為慣性導航系統的“心臟”,是飛機、艦船、導彈等精確定位和精準制導的核心部件。
這一科研成果引發世界震動。那時,已過而立之年的高伯龍是哈軍工的一名物理教員。當時的他並不知道,10年之後,他將與這枚小小的“陀螺”共同高速旋轉,直到生命盡頭。
“搞鐳射陀螺,對我來説是一次艱難的選擇。因為,你生活在高山上,必須學會爬山而不能想著去游泳。”多年後,高伯龍院士這樣描述自己的選擇,“一個人的志願和選擇應當符合國家的需要”。
把國家的需要當作自己的需要,把國家的選擇當作自己的選擇。這是高伯龍院士給出的人生答案。但回顧院士一生,鐳射陀螺並不是他答案中的唯一選項。
少年時代,日寇入侵,神州板蕩。高伯龍輾轉三地,入讀8所學校才上完小學。一路顛沛流離,一路兵荒馬亂,高伯龍看在眼裏,恨在心中。他在給堂妹高長龍的信中寫道:“我現在雖然還沒有槍,但用拳頭也要把敵人打死。”

△1961年,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工作的高伯龍
深受父親的影響,熱愛數理的高伯龍發奮學習,立志以科學救國、強國,最終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不久,決心在理論物理領域幹一番事業的高伯龍,迎面遇上大時代——剛剛成立的哈軍工急需教師骨幹,一紙調令,高伯龍成了哈軍工的一名物理教師。
彼時,高伯龍唸唸不忘的仍是理論物理研究。在哈軍工執教兩年後,他報考了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專業方向的研究生,並以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得知情況後,哈軍工首任院長兼政委陳賡大將專門把高伯龍請到家裏吃飯挽留。後來,高伯龍對自己的清華同窗楊士莪説:“陳賡院長請我到家裏吃飯,我就知道走不了了。”
從前半生魂牽夢繞的理論物理,到後半生傾力投入的應用物理,個人命運之河的偶然轉折,成就了一項科研事業的全新起點。

△高伯龍教授在指導科研人員調試鐳射器
1970年,哈軍工遷往長沙,後來更名為國防科技大學。就在哈軍工南遷的第2年,科學家錢學森將兩張寫著鐳射陀螺大致技術原理的小紙片,鄭重地交給了他們。
“高伯龍一來,局面馬上就不一樣了!”丁金星説起與高伯龍院士相識的場景,笑容滿面。
茨威格説,在一個人的命運之中,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年富力強時發現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單看高伯龍的履歷,51歲晉陞教授,69歲評院士,屬典型的大器晚成。但幸運的是,高伯龍遇見了鐳射陀螺事業,而中國的鐳射陀螺事業也遇見了高伯龍。
從此,共和國鐳射陀螺科研事業拉開了光榮與夢想的幕布,開啟了艱難與輝煌的征程。
光之旅:瞄準前沿加速追趕
“我們起步已經晚了,
如果現在不抓緊,啥時能趕得上”
正如公眾對“鐳射陀螺”這個專業名詞的陌生,很多年裏,高伯龍這個在專業領域內如雷貫耳的名字,並不為大眾所熟知。
翻閱有關新聞檔案,各大媒體對高伯龍及其鐳射陀螺創新團隊的報道,集中在2014年。
在當年的報道中,高伯龍率領的鐳射陀螺創新團隊第一次走進公眾視野。這一刻,距離鐳射陀螺開始研製已經過去整整43年;這一刻,團隊的靈魂人物高伯龍院士卻因積勞成疾住進了醫院。

△1991年,高伯龍參加鐳射陀螺評議會
43年裏,究竟發生了什麼?如今回過頭來看,團隊中的科研人員都説: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張斌在1991年保送就讀高伯龍的碩士研究生。第一次來到這間由食堂改成的實驗室時,他著實驚呆了:在這間放滿了陳舊實驗設備的“小作坊”裏,竟然還放著油鹽醬醋……
後來,張斌明白了:“為了節省時間,老師經常在實驗室裏下麵條。這些調料根本不是救急用的,而是實驗室常備啊!”

△1991年,高伯龍指導博士生工作
“自主設計”4個字背後蘊含的艱辛,或許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方能體會。鐳射器檢測要求在封閉、潔凈的環境中進行,沒有空調,不能用電扇,高伯龍和同事們在密不透風的“大悶罐”裏,通宵達旦做測試……
一次,高伯龍連續做了十幾個小時試驗,回到家中腳腫得連襪子都脫不下來。愛人曾遂珍看了心疼得淚水在眼眶裏打轉:“為啥就不能悠著點幹?”高伯龍笑笑説:“我們起步已經晚了,如果現在不抓緊,啥時能趕得上?”
鐳射陀螺雖小,卻整合了光、電、機、材料等諸多領域尖端技術。它不僅是一個全新的領域,更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作為這一領域的後來者,高伯龍和他的創新團隊一刻也沒有停下加速追趕的腳步。某種意義上,“追趕世界前沿”這一目標始終吸引著他們、伴隨著他們、考驗著他們。

△1990年,高伯龍教授在進行科研工作
擺在高伯龍和團隊面前的挑戰,不僅是物質條件的艱苦。事實上,從起跑那一刻起,高伯龍便是廣受質疑的“少數派”。
從“少數派”變成“技術權威”,這正是高伯龍傳奇故事中最為激動人心之處。
1975年,在全國鐳射陀螺學術交流會上,高伯龍一鳴驚人——依照我國當時的工藝水準,必須採用四頻差動陀螺方案!此言一齣,等於否定了國內的通行方案,一時四下譁然。但高伯龍用紮實的理論和計算説服了眾多與會專家。
次年,高伯龍寫出中國鐳射陀螺理論的奠基之作《環形鐳射講義》。直到今天,研究鐳射陀螺的人不學這本書,就不敢説“入了門”。
攻關之路多險阻。1984年,實驗室樣機鑒定通過時,一陣“冷風”襲來:由於美國徹底放棄同類型鐳射陀螺研製,國內質疑聲再起:“國外有的你們不幹,國外幹不成的你們反而幹。”
“外國有的、先進的,我們要跟蹤,將來要有,但並沒有説外國沒有的我們不許有。”10年後,某型鐳射陀螺工程樣機通過鑒定,證明了高伯龍所言非虛。
就在鐳射陀螺工程樣機鑒定順利通過的同時,一批號稱“檢測之王”的全內腔He-Ne綠光鐳射器問世,引起業內轟動。這也意味著中國在鍍膜的膜係設計和技術工藝水準上實現重大突破,成為繼美、德之後第3個掌握該技術的國家。

△2001年,高伯龍進行科研工作
加速追趕的成績,讓世界為之驚訝。捷報頻傳之際,高伯龍又盯上了新的高地——新型鐳射陀螺,並將目光投向鐳射陀螺最主要的應用領域——組建慣性導航系統。
那時,國內已有多家單位開展此類研製,採用國際主流的慣性導航系統。這個系統到底行不行?高伯龍再次給出與眾不同的答案——必須給該系統加轉臺,否則無法滿足長時間、高精度的慣性導航需要。
這個方案,又是一個無經驗借鑒的中國特色。在一場專為旋轉式慣性導航系統召開的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大多對此持否定態度。
這一幕,和1984年四頻差動鐳射陀螺的遇冷,何其相似!高伯龍的答案仍然是:埋頭繼續幹,成功才能得到承認!
在他的悉心指導下,2006年12月,國內首套使用新型鐳射陀螺的單軸旋轉式慣性導航系統面世。4年後,雙軸旋轉式慣性導航系統面世,精度國內第一。如今,旋轉式慣性導航系統已成為國內主流。
光之焰:赤子情懷至真至純
“穿著五塊錢的背心,
幹著上億元的大事”
2014年,鐳射陀螺創新團隊走入公眾視野。電視裏,高伯龍院士那幾秒鐘的鏡頭,給人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他穿著白背心,全神貫注地盯著電腦螢幕,兩根彎曲的手指慢慢敲擊著鍵盤……
有網友評論:“高伯龍院士穿著五塊錢的背心,幹著上億元的大事。”也有網友説:“這是真正的偉大。”

“背心院士”和學生們在一起
如今,高伯龍院士去世兩年了。但校園裏那個佝僂的背影,永遠印在很多人的心中——夏天,永遠都是一身老式作訓服,一雙黃膠底解放鞋;冬天,不是一件軍大衣,就是一件灰色羽絨服。
後來高伯龍的學生張文才知道,這件灰色的羽絨服,導師已經穿了30多年。張文聽他總這樣説:“穿習慣了,再買新的浪費錢,浪費時間。”
學生江文傑至今記得,1993年四頻差動鐳射陀螺工程樣機鑒定出現問題時,高伯龍跟他説的一番話:“我花了20年時間,花了國家那麼多錢,搞成這樣,我是有罪的。” 當時,導師前所未有的沉痛語氣讓他深受震動。
多年後,早已是院士的高伯龍,在給中學畢業紀念冊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唯一能安慰的是,沒有做過虧心事,到底還幹了一些事,對人民和社會能作交代,雖然還很不夠。”

△高伯龍生前穿戴的衣物。陳思 攝
在外人眼中,高伯龍院士好像生活在真空裏。但在子女眼中,這個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的老頭,卻是位骨子裏浪漫的父親。
高伯龍的女兒至今記得這樣一個場景:“有一次我剛回家,就聽見電視裏男主角跟女主角説了一句‘我愛你’。沒想到,我爸一扭頭對著我媽也説了一句‘我愛你’。”
高伯龍住院期間,愛人為了陪護也住到醫院。女兒常常看著父母用紙筆交流出神。她覺得,看到父母,就看到了愛的模樣。
《高伯龍傳》中,高伯龍的摯友蕭枝葵曾回憶了這樣一個細節——
“孩子生病的時候,他常常是懷裏抱一個,背上背一個,來醫院找我看病。他很愛孩子,對孩子管教也很嚴……他鼓勵孩子好好讀書,不過多干涉,也沒有什麼具體輔導,就是跟孩子聊聊天,引導孩子,讓孩子自立。”
張文的腦海裏一直記著這樣一幅場景——
高伯龍住院以後,他的同班同學、中國工程院院士楊士莪夫婦到長沙來探望他。病房裏,兩人聊起往事,竟一起唱起了當年的歌。唱完之後,楊士莪説:“可惜了,差一把手風琴。”高伯龍接著説:“可不是,還少一把口琴呢!”説完,兩人哈哈大笑。
坐在一旁的張文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她“從沒想到教授還有這樣一面”。如今,再次想起這幅珍貴的畫面,張文又有了新的體會:“他們其實和年輕時的我們一樣,愛唱愛笑。説不定,他們年輕時,比現在的我們還要潮呢!”

2011年高伯龍參加清華大學百年校慶
清晨,走在國防科技大學校園裏,一張張青春面孔與我們擦肩而過。陽光下,年輕一代的臉上寫滿對未來的憧憬,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龍。
入夜,鐳射陀螺實驗樓裏,一盞盞燈亮了起來。燈光下,張文和同事們聚精會神地忙碌著,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龍……
一束光可以照多遠?一束光可以傳遞多久?答案,或許就在清晨陽光下的一張張青春面孔裏,就在入夜後實驗室亮起的一盞盞燈光裏……
來源:軍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