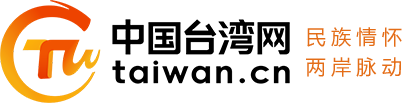藝術地描摹時代的情感底色
【文藝觀潮】
藝術地描摹時代的情感底色
——七十年來文學對家國情懷書寫概觀
作者:林清華(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中國文學素有“文以載道”的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皆是中國歷代文人的自覺追求。作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詞,“家國情懷”也從未在當代文學作品中缺席。“家國同構”與“家國一體”是家國情懷亙古不變的基本內涵,但其表現形式卻是流動的,有著多元的、複雜的面向。對於當代作家而言,他們的作品必然要帶上各自所處的時代或深或淺的印跡。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變動不居的社會情態,無不在七十年的當代文學中得到呼應與書寫。可以説,當代文學七十年,也是家國情懷不斷深化與擴展、內涵與表達從單一走向多元的七十年。

新中國成立初,《祖國頌》《投入火熱的鬥爭》與《青春之歌》所體現的宏大家國情懷,成了這個時期文學書寫的出發點和最後的歸宿。圖為電影《青春之歌》(1959年)海報。資料圖片

《大江東去》展現了個體在改革開放的大時代裏和國家共進退的豪邁與壯闊,由此建構屬於新時代文學作品獨有的家國情懷。圖為由該作品改編成的電視劇《大江大河》劇照。資料圖片
定格時代的蓬勃朝氣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蓬勃朝氣與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在阮章競、田間、郭小川與賀敬之等人的詩歌創作中得到極致的彰顯,彰顯出這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楊沫的長篇小説《青春之歌》有著昂揚的青春氣息,可以視為五四傳統在當代文學的延續,但在氣質上迥異於《莎菲女士的日記》或《沉淪》等現代文學作品。知識分子的痛苦與猶疑在《青春之歌》中幾乎消隱,取而代之的是對精神解放的認真追求和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熱切嚮往。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總是以一種“史詩性”的面目出現。柳青的《創業史》與梁斌的《紅旗譜》概不例外。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史詩色彩濃郁的作品,是對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的時代氛圍的呼應,也是對家國前途充滿堅定信念與熱情憧憬的文學化宣示。換言之,這是一個自覺地把個人訴求委身於國家前途的文學時代,《祖國頌》《投入火熱的鬥爭》與《青春之歌》所體現的宏大家國情懷,成了這個時期文學書寫的出發點和最後的歸宿,也是當代文學七十年所呈現的第一個面向。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青春之歌》中的個體解放與人性覺醒具備了更多的現代性,它依稀開啟了“現代中國”的文學想像。新中國的成立,文學也必然要相應地從過度宏大的家國敘事,轉向重視國家的每個個體的現代生命體驗。唯有個體的現代性實現,才有現代中國的成型。
人的價值得到進一步強化
改革開放是另一個偉大時代的開啟,也是當代文學一個新的起點。對民族精神的眷戀與對家國前途的憂思重新迸發,化作“歸來者”筆下一行行鮮活的文字和一個個生動可感的人物。作家們成了普通民眾個體情緒與家國思慮的代筆人,受到社會的高度青睞。他們內心蘊含的崇高感與家國使命感再次被激發,紛紛以極大的激情與勇氣去直面現實人生、干預現實生活。前三十年過度宏大的國家敘事造成的個體壓抑與精神“傷痕”需要作家們去撫慰,也促使他們再次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日常生活與非英雄式的普通人物,譬如舒婷的《雙桅船》《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和顧城的《一代人》。新崛起的詩人們在反思歷史的同時,雖然也延續著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患意識,但其視角開始更多地轉向個體化的生命體驗。當代文學家國情懷的面向由此開始走向多元,“人”又一次出現在家國同構體系的重要位置。“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等新的文學現象無不建構在“人”的意義復蘇之上,宏大的國家敘事逐漸與幽微的個人體驗靠攏並置。
隨著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浪潮席捲全國,當代文學從“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過渡到“改革文學”,也就成為一種必然。作家們帶著一種神聖的使命感熱情地回應著改革大潮,但他們的著眼點顯然已經發生了轉移。如果説《喬廠長上任記》還在著力塑造一個國家英雄式的人物,《陳奐生上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已經不再迷戀或滿足於英雄的塑造,而把改革精神更多地附著于普通個體,去表達他們在時代之中的日常生活與情態變遷。在人、家、國三位一體的價值結構中,人的價值得到進一步強化,這當然是當代文學與所處時代的一種良性互動,也是其家國情懷應該有的第二個面向,並持續至今。
追求民族化審美方式
隨著現代化建設的進一步深化,中國開放的大門越打越開,西方現代文化與思想進入中國變得快速而便捷,直接影響了20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和探索戲劇的萌發。先鋒文學和探索戲劇更加強調個體的舒展與極度個性化的表達,試圖打破之前三十年累積的過度宏大的家國敘事對個體經驗的壓抑。它們不標榜家國情懷,也並非擯棄家國情懷,而是從最細微的個體體驗入手,提供另外一個思考個體與家國關係的維度。
當然,不斷更新並迅速失寵的西方現代文化思潮的進入,有時候也會讓中國作家們應接不暇而變得茫然,以王蒙、韓少功、阿城等為代表的作家乾脆返身,到悠久傳統中國尋求寄託與解決問題的路徑。“尋根文學”的興起,意味著當代文學的民族審美自覺的開啟。與現代文學主要以揭露與批判傳統文化的基調不同,這些作家的作品,在強調現代意識滲透的同時,也開始有意識地追求民族化的審美方式,著力表現獨特的民族文化表徵。
正如陳思和教授所言:“文化尋根派作家們對於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認同或反省,都投射在他們那融合了傳統與現代、特別富於想像力的藝術風格中。”阿城的“三王”系列、韓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都在試圖從民間與鄉土的關懷中,尋求傳統文化的病症與潛在的頑強生命力。這直接影響到後來者莫言基於民間立場講述家國故事的一系列小説作品。在這個階段,當代文學更多地走向民間與鄉土,與海外華人文學的故土書寫一起,展現出另外一個不該被遮蔽的維度,可視為當代文學七十年家國情懷的第三個面向。
家國情懷的文學表達更加飽滿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形態的轉型急速向前,改革開放的大潮總是在瞬息之間改變各個領域的存在方式,以致個體的生命體驗也從原先被規約化的、相對穩定的狀態變得零碎而尖銳。商品社會的來臨,使民眾的焦點從精神層面迅速轉向了物質層面。與此相呼應的,是直接促成當代文學從精英化敘事轉向對個人生存空間的理解與表達。但是,當代文學的家國情懷並沒有也不會就此消隱,只是變得更加多元而複雜,也更加去關注國家發展過程中個體的現代性問題。
當代文學家國情懷的三個面向開始交融並呈,既有以王安憶的《長恨歌》,韓少功的《馬橋詞典》,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秦腔》《山本》為代表的民間敘事,也有以二月河的“帝王系列”為代表的國家敘事,更有關注個體生命體驗與成長的年輕一代作家的個體敘事。新一代作家阿耐的《大江東去》是一個典型的範例。這部作品所展現的青春氣息,是個體在改革開放的大時代裏和國家共進退的豪邁與壯闊,由此建構屬於新時代文學作品獨有的家國情懷。《大江東去》在被改編成電視劇《大江大河》之後,即便失去了原著的部分深刻性,也依然迅速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共鳴。以人、家、國三位一體同構的現代價值體系,在這個時代獲得了普遍的認同與表達,是當代文學在家國情懷的書寫層面獨特的成就。
現代中國的建構依然是進行時,當代文學也不例外。家國情懷的文學表達在這個時代非但不會消隱,反而會更加飽滿。面對更加急遽的社會形態變遷和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國文學的當代書寫者們,依然需要立足民族文化的根基,根據不同的生命體驗與擅長的表達路徑,去描摹此時中國的情感底色,直面更加複雜多元的問題,與這個偉大的時代同呼吸、共成長。
《光明日報》( 2019年09月1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