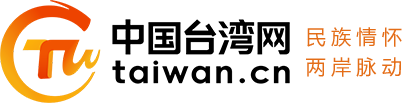你不知道的北京地鐵:有地鐵司機一天喝11包咖啡
冰點特稿第1124期
你不知道的北京地鐵
北京地鐵每天都在發生讓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有的地鐵司機一天要喝11包咖啡,地鐵司機每天要重復960多次手勢動作。一名巡道工每個月都會磨破5雙棉襪,每年要檢查12萬個鐵軌零件。早晚高峰時,車站廣播員要把一句話重復1800多次。
平均每月都會有20多只鞋,70多個背包玩偶挂件掉落在西二旗站臺下面的道床上。站務員曾在那裏撿到一個裝有5本房産證的公文包。
已經沿著10號線,把金臺夕照到分鐘寺這截北京最繁華地段走了630多次的巡道工,卻從來沒有走進過頭頂上的任何一棟建築。
一家地鐵站旁的便利店,每天接待的第一位顧客,永遠都是地鐵員工。
北京運營著全世界最繁忙的地鐵系統,僅地鐵司機就超過6000名,相當於兩所大型中學的人數規模。2017年共有38.7億人次乘坐北京地鐵,比同年全國鐵路客運總運量都要多。
這座城市幾乎一年開通一條新線,只用了不到15年時間,地鐵線路圖就從“一圈一線”變成了現在的“電路板”,新開通的16號線每公里造價達到了12億元。
很多人每天都乘坐地鐵,卻對這個龐大的系統知之甚少,白天乘客不懂地鐵夜裏的黑,24小時它一刻都沒停止過緊張的運作。
司機
11月一個週二的下午5點,地鐵司機王凱華衝了當天的第七包咖啡。列車從休息室外駛過,桌子上的杯子和鋼勺因振動發出輕微的碰撞聲。起身前,他停頓幾秒感受心跳的頻率,希望咖啡能讓它略微加速。
再過15分鐘,列車會準時停靠在北京地鐵1號線四惠東站的站臺,王凱華要接替交班的司機,開始緊張且單調的晚高峰運營。他要對抗的,是困意——這個職業最大的難題之一。
為了提神,地鐵公司曾安排專人在東單站給司機發“秀逗”糖(一種口味較酸的糖果),也曾給司機配發“重力感應提示器”,挂在耳朵上,只要頭低到一定角度,提示器就會振動。
如今,在四惠東站司機休息室裏,十幾箱速溶咖啡堆放在墻角,足足有兩米多高。這是向司機“無限供應”的“福利”,最多的時候,王凱華一天喝了11包咖啡。
在四惠東站,即便是十幾年的老乘客也容易忽視,由東向西站臺一側的白墻上,那扇並不顯眼的鐵門。
1號線的“輪乘中心”就隱藏在這扇鐵門後面。司機把地鐵從蘋果園站開過來後,下車在這裡休息,等待下一列需要自己駕駛的班次。從家裏趕來上班的司機也會先到這裡,換上制服,做開車前的最後準備。
大部分時候,這間屋子都保持著沉默的氛圍,司機們偶爾有幾句交談,也多與工作有關。
王凱華的話同樣不多,這個29歲的地鐵司機已經有7年的“駕齡”,這樣的時間足以改變他的性格。
王凱華每天的工作場所是不到3平方米的駕駛室。為了防止眩光,列車行駛時駕駛室裏不允許開燈。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他都穿行在幽暗裏,前方是看不到盡頭的隧道,周圍是一成不變的灰色水泥。
駕駛室和乘客車廂間是一道不到10釐米厚的鐵門,把列車隔離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邊是明亮如白天的車廂,每天載著不同的人,發生著不同的事情。他們聊著不同的話題,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情緒。
另一邊的王凱華只能感受到“孤獨和枯燥”,他已經在同一條線路上往返了2500多個來回,每天要重復960次標準化動作:指示燈或者信號燈亮起時,他都要用手勢指出來,同時還要説出相應的密碼。
“我閉上眼就能判斷出車的位置。”他熟悉每一段區間的特點,能感受出列車撞擊鋼軌時,發出的不同聲響。那些有細微差別的顛簸,他感覺也“相當明顯”。
他還記得司機考試時,有一項科目是“猜速度”。考官把速度表遮住,考生要憑感覺估算出列車行駛速度,“一般誤差都不會超過1公里/小時”。
1號線一共70輛列車,在乘客眼裏這些地鐵都是同一副模樣,但王凱華清楚每一輛車的“小脾氣”:有的車勁兒大,滿載時牽引依然不吃力,有的車制動好,進站停車穩。
在1號線隧道裏,他更喜歡從西往東開,因為“車站越來越寬敞,站臺上的人越來越多,心情也跟著舒暢些。”相反的路線,只會越來越壓抑。
他羨慕那些開地上線路的輕軌司機,“至少能看到一年四季的變化,晴天陰天、下雨下雪時都不一樣。”
每次跑完一趟車,王凱華都會到輪乘中心的門外抽一支煙,那裏永遠都不會只有他一個人。門口的兩個垃圾桶裏,煙頭已經堆出了尖。
在隧道裏待久了,王凱華每天都要重新適應光明。他最怕列車從四惠站駛出隧道的那一瞬間,刺眼的白光直射到他的眼睛,甚至能讓他短暫“失明”。
還有些光明是來不及準備的。幾乎每天,車廂裏都會有乘客隔著玻璃對著駕駛室拍照,每次閃光燈突然亮起,王凱華的眼前就會一片煞白,然後陷入幾秒的黑暗。
乘客對地鐵司機的好奇不僅付諸相機。王凱華在工作期間沒功夫回頭看,但是駕駛室的擋風玻璃上能隱約反射出背後正在發生的事。有時隔離門上那個豎條形的玻璃,從上到下擠滿了人頭,“每個人都對我的後腦勺笑,很詭異”。
還有人乾脆邊看邊敲門,想要一個不可能得到的回應。
地鐵司機除了忍耐枯燥,精神也要時刻緊繃。
北京地鐵站的站臺前端,都設置了一個計時器。早高峰期間,王凱華從蘋果園站啟動列車時,計時器開始從“100”倒計時,這説明列車在這一站早點100秒。列車開到國貿站時,頭頂上的計時牌已經開始正計時,這意味著列車已經晚點。
在1號線,正計時的數字每跳動1秒,就會有300多人上不了車。
即使在平峰運營時,王凱華也沒法放鬆下來。
“雖然列車現在的安全性已經很高了,但是一想到我後面還拉了1000多人,我就緊張。”王凱華皺了皺眉頭説。
時間久了,王凱華甚至會出現精神恍惚。有時從一個站出發後,他會懷疑自己剛剛是不是忘記打開車門。
“幹這個之後,我都有了強迫症,家裏人再也不説我丟三落四了。”王凱華説。
最尷尬的是行車時忽然想上廁所,遇到這種情況,司機還要向行車調度中心請示。得到同意後,司機要從停站上節省出時間。或者是起身、下車、開門的動作快一些,或者看站臺上乘客少時,早點關門。
“有時廁所要分幾次才能上完。”王凱華露出尷尬的笑容,“節省出的時間有限,不能耽誤發車。”
如果輪到晚班,一天運營結束後王凱華要回到車輛段宿舍睡覺,第二天一早再跑一圈後晚班才算結束。早上發車前一個小時,會有專人喊他起床。上車前,王凱華會拿著手電圍著120米長的列車轉上兩圈,做例行檢查。隨後上車,接觸軌供電,列車緩慢出庫,進入正線。
有時早晨下班時,王凱華會剛好遇上早高峰。他到輪乘中心換下制服,然後扎進站臺上的人群,和他們一起擠進車廂。這個時候,沒人知道他的身份,他只是一個需要回家的普通人。
王凱華記得自己第一次駕駛正式運營的列車,快要到達國貿站時,為了對準站臺停車位置,他提前減速制動。列車緩緩前進,隧道前方開始出現光明,接著他看到了站臺上大批候車的人群。在此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那是他第一次有種被迎接、被期待的感覺。
西二旗
下午5點15分,在城市另一端的西二旗地鐵站,站務員黨卓振正在進站口外佈置限流的柵欄。晚高峰即將到來,天色逐漸變暗,空曠的高架車站就像個風洞,幾個乘客走上站臺,裹緊棉衣,把頭縮進衣領裏。
晚上6點半,西二旗站的客流量達到峰值,站外的長隊沿著限流通道緩慢移動,站內已經被黑壓壓的人群塞滿。人們呼出的熱氣向上蒸騰,有人敞開了棉衣,相比下午,站廳裏的溫度上升了6℃。
黨卓振説,西二旗地鐵站是“每天都在發生奇跡”的地方。
在這裡,平均每月有20隻鞋、70多個背包玩偶挂件掉落在站臺下的道床上。車站特意準備了拖鞋,方便那些擠掉鞋子的人回家。站務員在清理軌道時,撿到的最貴重物品,是一個裝有5本房産證的公文包,失主“感謝到不行”。
西二旗站是北京最擁擠的地鐵站之一,每天有30萬人次在這裡乘車,比春運時北京西站每天的客流量都要大。
一個新來的站務員沒經歷過西二旗的“盛況”,在早高峰維持秩序時,被洶湧的人流擠上車,直到知春路站才擠下車返程。
這裡是13號線和昌平線的換乘站。在昌平線上的沙河站,站務員每天早上5點剛打開車站門,外面等候的人群就已經排起了長隊。早高峰時,沙河站的隊伍能排2公里長,很多人“推開家門就開始排隊”。
西二旗站每天的人流就像潮汐。早上漲潮時,滿載率超過140%的列車從昌平線開來,乘客在這裡換乘、下車,晚上退潮時,人們再從這裡出城,回到住處。
早晚高峰時,車站廣播員要在4個小時內重復1800多次“列車到站,先下後上,請在車門兩側候車”,每次廣播到最後,他們都會“眼花、幾乎要暈倒”。
如果一個人想要在早高峰的西二旗成功擠上地鐵,那麼就算他已經通過安檢,平均也需要再花費16分鐘。司機要保證在昌平線上的每個站都早點,到西二旗時才能留出足夠冗余,“因為西二旗站必定晚點”。
人最多的時候,在這裡等候上車的隊伍能排到20多米長。車門一開,原本靜止的隊伍馬上開始小碎步移動,人們甚至能感到站臺振動。有的人上了車,包落在了外面,有的包被擠上了車,人卻卡在了車外。
西二旗站區副站區長李思野見過千奇百怪的上車方式,有人雙手抓住地鐵扶桿,雙腳懸空,身體與車頂呈接近20度的夾角搭在人群之上。
一個退休後在西二旗服務了8年的文明引導員,總結出在西二旗成功上車的“秘笈”:“小夥子打頭陣”“側身突圍”。
高峰時車廂裏的乘客經常擠到頂住車門,造成車門無法機械鎖閉,站務員要手動把兩扇車門強行拉上。這要求站務員必須有足夠強的臂力,以至於現在,西二旗站只有男性站務員才有“資格”站在早晚高峰的站臺上。
因為處在網際網路産業圈的圓心,每天從西二旗站下車的人和上車的人一樣多。一位老太太曾經這樣形容乘客在西二旗下車的場面:“高峰時車門一打開,地鐵就像‘嘩’地吐了一樣。”
即便如此,哪怕只是晚了一秒鐘,下車的乘客也會被拼命往裏擠的人潮硬生生帶回車廂。西二旗站的一位值班站長曹宇經常會在車門關閉前,看到一隻忽然從人群中伸出的胳膊。幾乎不能猶豫,站務員就要迅速抓住,把這只胳膊的主人拽出車廂。
大部分時候,西二旗站的乘客都能保持平靜的情緒,但仍無法避免偶爾發生的衝突。曹宇發現,乘客“幹架”的概率,夏天比冬天要高,早高峰要高過晚高峰。
“夏天比冬天火氣大,早高峰急著上班,晚高峰沒那麼著急回家。”曹宇分析。
每天面對如此複雜的早晚高峰,維持整個車站秩序的只有27名員工。綜控員要時刻盯著電腦螢幕,上面不停移動的紅條,代表列車的運作狀態。站務員則在售檢票、接送列車間輪流換崗。
曹宇剛調到西二旗當值班站長時,壓力太大整晚睡不著覺,最後被醫生診斷為精神衰弱,“喝了半年中藥”。
因為是高架線路,車站裏是典型的“夏熱冬涼”。夏天時,“站務員的衣服沒有幹過”。到了冬天,穿堂風從“兩頭透氣”的車站毫無障礙地通過。去年最冷的一天,車站二層站臺上的溫度達到-26℃。
“最冷的時候,我們車站的站務員分不出男女。”李思野笑笑説,“都把自己裹得只剩眼睛,衣服裏面挂的全是暖寶寶。”
和地鐵司機一樣,地鐵站務的晚班也要負責當天的晚高峰,和第二天的早高峰。一天的運營結束後,清理完站臺軌道的員工回到地鐵站負一層的宿舍。時間往往是深夜1點,休息時間才會到來。
3個半小時後,新一天的工作開始。第一列開往西直門的列車45分鐘後就要到站,站務員要在這段時間內完成所有的準備工作。
5點整,黨卓振打開站門,外面已經有背著編織袋的老鄉正在等候。他們要趕火車,是每天西二旗首班車上最常見到的乘客。
黨卓振來到車站旁的便利店,叫醒趴在桌子上睡覺的店員,買了一瓶牛奶、兩個三明治。店員告訴記者,自己每天迎接的第一個顧客,永遠都是過來買早餐地鐵員工。
終點站
李思野喜歡站在車站的二層連廊上向下觀察,這裡總會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
西二旗站是個屬於年輕人的車站,這裡被各種軟體園、科技園和創意園包圍,有大量自嘲為“碼農”的程式員,也有手裏握著幾個項目的創業者。
李思野發現,每到節日就會有很多捧著鮮花或者禮物在站臺上等候的小夥子。每年情人節,晚上結束運營後,車站裏到處都是散落的花瓣,也有成束的鮮花塞在垃圾桶裏。萬聖節時,李思野曾見過一群“兵馬俑”排著隊走上地鐵。
每逢畢業季,車站裏就會多出很多西裝革履、背著雙肩包的年輕人,出站口也會聚集一群散發租房廣告的仲介。
西二旗地鐵站是一個喜悅和悲傷匯集的地方。有人剛剛挂上一通電話,就在車站裏忍不住笑出聲。也有人垂頭喪氣,領帶鬆開,木然地站在站臺上。
這裡也是個汗水和淚水混雜的地方。夏季早高峰時,車門一開,總會有三四個小姑娘“刷刷”暈倒。甦醒後,她們幾乎都會告訴工作人員,自己因為急著上班沒有顧上吃早餐。因此,除了拖鞋,車站也常備了糖果應對突發情況。
這裡有人失戀,有人失意。黨卓振曾在晚上結束運營後,碰到蹲在站臺上“哭到崩潰”的女孩。也見過癱坐在地上,不顧形象的中年男人。
與西二旗站不同,在7號線終點站焦化廠站,每天最後幾班地鐵在這裡停靠後,就要繼續向前開進車輛段。站務員要到車廂“清車”,他們經常遇到抱著背包在車上睡著,不知坐過多少站的乘客。每逢週末、節假日,車站裏都會有醉酒的乘客,講不清自己的家在哪。
“這是終點站,該回家了。”每次試圖叫醒這些人時,站務員都會這麼説。
還有一些剛來北京的外地老鄉,明明要去西客站,結果兩個小時後,坐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焦化廠的站臺上。
地鐵站就是這樣的一個集合,都市裏的現代人在這裡集中亮相。它就像城市的一個平行世界,映射出人世百態,展示出人們真實的樣子。
不斷延伸的地鐵線路也見證了這座城市的生長。7號線焦化廠站剛開通時,只有一條土路通向車站,晚上來上班的站務員有時甚至會迷路。
8年前,西二旗站剛運營時,每天只有6萬人次的客流量。李思野幾乎看著周圍的樓房高度和車站的客流數字一起上升。
這麼多年來,有人每天都會出現在地鐵站裏,有人會在某一天突然消失。西二旗的地鐵每天還是會準時停靠在站臺,就像這座城市,從沒有中斷過它原本的節奏。
巡道工
司機和站務員都休息後,地鐵線路工人就要開始工作了。每天零點後,北京的地鐵隧道裏都會有200多個工種、超過1000名工人在同時忙碌。
這裡不是摩天大樓、熙熙攘攘的北京,這裡是地下30米,沒有半點聲響的北京。隧道裏的空氣混合著灰塵和機油的味道,列車閘瓦和鋼軌磨損的金屬碎屑覆蓋在水泥地面上,手電照上去,會發出星星點點的光澤。
26歲的姜勝負責10號線金臺夕照站到分鐘寺站的巡道工作,他頭頂上方是北京最繁華的區域,央視新大樓、國貿商城、銀泰中心就處在必經之路上。每晚地面上的酒吧把音量開到最大,KTV裏的派對歡唱正酣時,姜勝也在地下開始了他的工作。
他工作的地方,和最偏僻的隧道沒有太多差別。這裡只有鋼軌、電纜和水泥,因為修建年代較早,就連燈光都要黯淡幾分。
4年來,姜勝已經在這條線路上走了630多次,連方向都沒變過,但他從來沒有走進過頭頂上的任何一棟建築,也沒見過那些商場和購物中心裏面的樣子。
“沒什麼事去那幹啥?”姜勝的生活幾乎只有工作和睡覺,隧道外的世界似乎與他沒有太多聯繫。
每天上班,他下午6點半就要從密雲區的家中出發,3個小時後到達金臺夕照站。他的休息室在站臺盡頭的一間小房子裏,沒有窗戶。
房間裏除了一些軌道搶修設備,一個櫃子,兩張高低床,再沒有別的物件。最近房間的燈壞了,他打開手電當做光源,和工友一起坐在床上翻手機,等待最後一班地鐵從門外駛過。
他負責的這段線路長7.8公里,一年下來要在隧道裏走1400公里,檢查超過12萬個軌道零件。他的工具包裏裝著各種型號的錘子、扳手、改刀,有12公斤重。動身時,書包發出輕微的金屬碰撞聲。
損耗最快的是襪子,姜勝每月最少要穿壞5雙棉襪。他自稱“腳王”,“幹這份工作前,全家我走路最慢,現在走路,家人要小跑才能追上。”
姜勝説之前最怕陪女朋友逛街,現在可以逛到女朋友走不動。他的微信運動排名裏,幾名巡道工工友長期霸榜。
“腳王”最難忍受的,是孤獨和壓抑。每天在空無一人的隧道裏走上接近3個小時,周圍空氣和光線一樣死寂。大部分時候,他都低著頭把眼光集中在手電照射的鐵軌上。但總是在某個瞬間,他會被深深的孤獨感籠罩,“超想找個人説説話”。
已經當了17年的巡道工李師傅也有同樣的感受。隧道因挖掘方式不同分為方形和圓形,相比之下,他更喜歡方形的隧道。
“圓形隧道就像一根管子,看不到出口。”李師傅感嘆。只不過,大部分時候他都要行走在圓形的隧道裏,就像一條困在水管裏的魚,只有一個方向。
他説巡道工過的是“美國時間”,每天都黑白顛倒。時間久了,不管自己在不在家,妻子都會在每天淩晨3點半左右醒來,這是他工作日每天到家的時間。
李師傅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臉,在隧道裏兩個多小時,“洗臉水都是黑的”。他發現不知什麼時候,自己的“起床氣”變得很大,每天睡醒後,就會無緣無故生氣。
他負責的線路上,有一段1.6公里的彎道,路基在這裡設置了一定的傾斜坡度。背著10多公斤的工具包,身體重心轉移到右側,日復一日朝著同一個方向在這段路上走過1500多次後,李師傅感覺“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平時走路也會覺得右腿抬腿困難。
巡道時,李師傅會用錘子敲擊鐵軌。通過撞擊發出的不同聲音,反饋出不同的力度,他就能判斷鐵軌內部是否結實,或者斷裂。
隧道裏沒有太多“新鮮”的東西。冬天時,李師傅在洞子裏見過一些貓狗的屍體。到了夏天,隧道裏會有蝙蝠,他經常一錘子下去,一群蝙蝠呼啦啦地從頭上飛了過去。
大部分時候,巡道工作都很難有收穫。但每次微小的發現,都是關係到列車運作安全的大事。
李師傅曾發現過兩根鋼軌連接處,一處超過兩釐米的縫隙。如果不及時處理,列車車輪不斷碾軋造成鋼軌錯位,嚴重時甚至可能發生脫軌事故。
每天淩晨3點左右,姜勝和李師傅會分別從各自的隧道出來,走上站臺。在綜控室做完登記,確保沒有工具落在隧道裏後,他們一天的工作才正式結束。
他們是一天中最早打開地鐵站門的人,外面的街道上空蕩蕩的,路邊總有黑車亮著雙閃。這時的溫度降到一天中最低,但卻是他們一天中最開心的時刻——冰涼的空氣灌進鼻孔,終於重返地面了。
李師傅要坐夜班車27路公交車回家,每次車裏都會坐滿了代駕司機,有人聊著晚上發生的故事,有人發出沉重的鼾聲。車窗外,路邊的早餐店已經開門,穿著棉襖的夫妻正在忙碌,水蒸氣在燈光下不斷升騰。
這些場面讓他感到安寧。兩個小時後,第一撥兒乘客即將到達站臺,沿著他剛剛檢查過的軌道,開始一天的工作。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楊海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