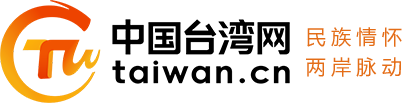他們在為滇越鐵路留下影像

點擊查看視頻
每年三四月間,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壩子周邊山野的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牛屎馬糞與雜草混合發酵後的臭氣,這是一股迎接鮮花與果實的臭氣。5月,臭氣開始變成香氣,除了山花的香,還有泥土原汁原味的香。
張永寧已經非常熟悉這些大自然的氣味,一年多來,他和他的團隊無數次行走在滇越鐵路沿線,跟隨著鋼軌穿山越嶺,用影像記錄著至今還與百年鐵路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村寨、那些人。
多年以來,雲南藝術學院教授張永寧對滇越鐵路一直有一種難以描述的迷戀。小時候,和許多“老昆明”一樣,他的家裏也曾經有過洋火、洋鹼、洋鐵桶、洋瓷碗。這些生活用品,因為經由滇越鐵路運輸到昆明,都加了一個“洋”字。
在雲南文化中,鐵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火車沒有汽車快”“火車不通國內通國外”,雲南十八怪中,有兩怪和鐵路相關。
1910年通車,連接越南海防市、中國河口到昆明的滇越鐵路,是雲南歷史上建設時間最早、建設難度最大,在中國和世界鐵路建設史上最具影響的鐵路工程之一,它也是目前國內為數不多、現存最長的米軌鐵路。(編者注:滇越鐵路的軌距為1米,比現在國內通行的標準軌窄43.5釐米,故稱米軌鐵路。)
通車之後的滇越鐵路,以30公里的緩慢時速實現了貨運及客運流通,促進了雲南的對外開放。抗戰時,它是西南地區重要的陸路運輸國際通道。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時,滇越鐵路也是滇南的一條大動脈。
然而,隨著泛亞鐵路、高速公路的修建,運作了上百年的滇越鐵路正受到威脅:客運停止,貨運減少。滇越鐵路從國際通道降為區域性運輸工具,正面臨著停運的危機。
2016年9月,張永寧申報的《終將消失的印跡——滇越鐵路影像紀行》項目,獲得了國家藝術基金的資助。一個由10多位藝術家、攝影家、大學教授、研究生共同參與的國家級文化項目,開始了對滇越鐵路為期兩年的影像記錄。
屏邊苗族自治縣的白河鄉,是滇越鐵路從雲南山地進入南溪河谷的第一個小鎮。由於地勢狹窄,小鎮沒有多餘的地方,白河橋車站鐵路兩側就成了鄉街,做買賣的攤位沿鐵路線綿延1公里長。當火車鳴笛聲傳來、火車臨近、道口橫桿放下時,叫賣的、趕集的才慢條斯理地讓出僅夠火車通行的空間。火車轟鳴著駛過後,人群又再次聚攏,繼續擺攤。
白河鄉是雲南至今唯一還留有鐵路鄉街的地方。過去客車還在運作時,這種火車帶來的市場,“一站一集市,逢站必鄉街”。趕街的日子,附近村寨的農民背著籮筐,坐上慢悠悠的火車去另一個站趕街。車廂裏,除了喧鬧的人聲,還有雞的叫聲。成捆的甘蔗、成籮的大米、鳳梨,剛從樹上砍下的香蕉,被甩到貨車廂裏,塞滿了火車的空間。
2003年,客車停運後,滇越鐵路上這種充滿中國式人情味的火車風情消失了,隨之消失的還有米軌線上的鄉街。
“只有走在這條鐵路上,才真正懂得當地人對滇越鐵路的感情。”項目組成員、雲南藝術學院教師、藝術家林迪説。
鐵路失去了活力,似乎也感染了沿線的人。在白河鄉的鄉街上,一位寂寞的老人望著伸向遠方的鋼軌對林迪説,她丈夫曾是白河橋站的鐵路職工,貨運減少後,大多數職工都走了,他們“沒本事沒關係,走不掉”,一直守著已經變為電所的車站。“運輸繁忙時,車站熱鬧好玩。現在每天拉的都是貨,看不見人”。
隨著貨運減少,沿線車站變得冷清、安靜,大批人員撤走或遠走他鄉謀生,許多站房人去樓空。那些曾經從各地來到鐵路上的農民,成為工人,隨著鐵路的冷落,他們又再次成為農民。
鐵路上,常有一名沿著鋼軌行走放牛的退休職工。他背著錄音機,磁帶放著當地民歌,聲音很大。他還有一個很大的茶杯和自製的彈弓,牛要是走遠了,他就撿起一塊石子,用彈弓把牛“喊”回來。
深山中峽谷邊的倮姑站,曾經生活著很多人,如今只剩7個人,其中2名是巡道工。每天沿著鐵軌巡道很寂寞,走幾公里也遇不見一個人,偶爾會看見野猴從山上下來,到南溪河邊撿食從上游漂下來的水果。
倮姑站還有一對打鐵的夫婦,丈夫70多歲,上世紀70年代招聘到車站工作,後來跟著當地的師傅學打鐵,打各種農具,火車來了就拉出去賣掉。現在他們不再打鐵了,打出來的農具拉不出去也賣不掉。他們在車站生活了40多年,捨不得離開,就在車站四週的空地上養豬、種苞谷。
列車最後的旅程是南溪河河谷,海拔從2030米降到91米,鐵路兩邊的山坡上是“頭頂香蕉,腳踩鳳梨”的豐收景象。
一隊有10多匹馬的馬幫正在運輸鳳梨、香蕉。馬鍋頭(隊長)長著紅鼻頭,因此自稱“紅鼻子馬幫”。馬幫馱著鳳梨、香蕉沿著鐵路走到公路邊,等待貨車拉走。
在因鐵路而興、因鐵路而衰的村寨裏,“人們談論滇越鐵路的口氣,就像談論一首不朽的詩”。在鐵路邊生活了一輩子的蔣文德老人,18歲就擔任村支書,現在他租住在個碧石鐵路石窩鋪車站,在車站周邊幾十畝地裏種植枇杷、桃子,附帶幫政府維護車站尚存的房屋。
“從某種意義來説,一條鐵路就是無數人的精神家園”。長期研究滇越鐵路的王福永是昆明鐵路局米軌保護與開發利用辦公室副主任,他認為,“對鐵路職工而言,滇越鐵路不僅是他們的‘飯碗’,更是他們的事業和依託;對當地百姓來説,滇越鐵路是他們的親戚,也是他們依靠的對象”。
多年來,昆明鐵路局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保護著滇越鐵路,雖然每年通過這條鐵路從昆明至河口的貨運量僅兩三百萬噸,但使用是最積極的保護方式。
“真正的保護是運作而不是停運。如果火車停運,只能叫抑制性保護。”王福永説。
在王福永看來,保護滇越鐵路,就是保護沿線的村寨和村民,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滇越鐵路沿線大部分是貧困山區,“保護與開發利用好滇越鐵路,是為了長久地造福這一區域的人們”。
近年來,滇越鐵路申遺和保護開發利用的呼聲越來越強烈。然而由於滇越鐵路在雲南境內橫跨4個地州16個市縣,由某個地區單獨保護難以執行,加之鐵路産權等問題,使得滇越鐵路的保護一直處於“共識容易,共進難”的局面。
2015年5月1日,一列由東風21型米軌內燃機車牽引、挂有6節車廂的旅遊小火車從建水縣古老的臨安站開出,沿著個碧石鐵路,駛過鳥語花香的建水壩子,到達有著無數雕梁畫棟、美輪美奐古宅的團山村。
個碧石鐵路是100年前中國人自己修建的一條只有6寸寬的中國最窄的鐵路。上世紀70年代改為米軌,納入滇越鐵路米軌鐵路網,直到2003年停止客運,2010年停止貨運。
3年前,建水縣政府與昆明鐵路局合作,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建水古城旅遊觀光小火車納入建水古城風貌恢復的組成部分。建於1925年的臨安站由此免於房地産開發。如今,坐大火車到建水看小火車的旅遊項目,每年吸引著數十萬旅遊者。
個碧石鐵路的起點,位於蒙自市城北10公里草壩鎮碧色寨村的山樑上。因兩條鐵路軌距不同,碧色寨車站曾是滇越鐵路與個碧石鐵路相交的樞紐,乘客和貨物都要在此換車。
上世紀60年代,寸軌拆除改造,碧色寨由特等站降為四等小站。雖然失去了往日的繁華,但早期鐵路車站的法式建築群卻得以保留下來。2017年,國家文物局對車站站臺、法國員工的宿舍、火車站酒吧、美孚石油公司遺址等進行保護修繕。而這一年,電影《芳華》讓碧色寨車站聲名遠播。據蒙自市碧眾合鄉村旅遊專業合作社的不完全統計,今年春節期間,碧色寨的旅遊者超過10萬人次。
建水小火車和蒙自碧色寨的保護與開發利用,受到廣泛讚譽,被認為是“滇越鐵路由運輸功能向文化旅遊功能轉變,為探索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提供了示範”。
2018年1月,滇越鐵路入選第一批“中國工業遺産保護名錄”,這為米軌鐵路全線保護帶來了福音。
“道路會給很多地方帶來繁榮,也會給很多地方帶來衰落。”雲南省社科院研究員、著名學者楊福泉認為,滇越鐵路面臨的問題,正是當下“路學”研究的方向。
滇越鐵路沿線所經過的雲南地區聚居了苗族、彝族、哈尼族、瑤族等12個少數民族,在465公里鐵路沿線,薈萃了壯美的自然奇觀、浩大的工程奇觀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奇觀,如此跨國、跨族、跨界、融自然和人文景觀于一體的文化遺産,世界上絕無僅有。然而這些卻因高速路的修建而被忽視了。
作為人類學的一個新議題,研究者們認為,高速道路強調大城市與大城市的直接連通,盡可能減少繞行;越快速的道路,中間消除的點就越多。高速路將人流、物流、資訊流等資源集中于大中城市,而它們之間的小城鎮和山村則被忽視了。“新道路在創造新動力的同時,也消減了一些鄉村的發展機遇”。
“通過研究道路變遷如何影響沿線人群在社會、文化和生計層面的改變和發展權等問題,對於制定滇越鐵路的保護政策是有現實意義的。”楊福泉説。
1903年,法國人馬爾波特來到雲南,擔任滇越鐵路工程隊的會計師。在雲南的5年間,他先後用一台木質暗盒皮腔相機和一台可換片盒的新款相機,拍下上千張滇越鐵路建築工地和沿線山水風光、民族生活的照片,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影像資料。
2017年8月,張永寧收到項目組成員、法國專家裴逸風提供的1000多張馬爾波特的老照片。這些照片讓張永寧心潮起伏、夜不能寐。“這800多公里路上的月和雲得去找找、看看”。
一年來,項目組多次沿著昆明到河口465公里的鋼軌,穿山越嶺,走村入鎮,行走拍攝。並從河口出境到越南老街,經海防到達河內,對越南段394公里的沿線進行拍攝。與馬爾波特不同的是,項目組還多了無人機航拍,以及對沿線人群的口述記錄。
“作為一條延續百年、至今還在運作的鐵路,滇越鐵路已經從一種工程設計先進的交通工具演變成需要從民族學、人類學進行研究的文化線路。”楊福泉説,目前把滇越鐵路作為“路學”研究,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
《滇越鐵路影像紀行》將於2018年下半年結束。截至目前,項目組已在昆明舉辦了3次專題攝影展,引起社會廣泛共鳴。
“這些影像展示了沿線村民與滇越鐵路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及道路變遷給當地城鄉結構帶來的歷史變遷,它們將是今後滇越鐵路‘路學’研究的珍貴資料。”楊福泉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