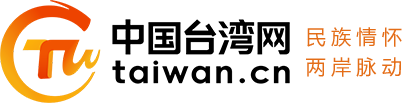大齡自閉症患者父母:我們走後,孩子怎麼辦?
“我現在只有一個願望,就是讓我比我的孩子活得久一點,一年就行。”
説這句話時,年過五十的溫絨和趙廷,幾乎同時擦了擦眼睛。
媽媽在哭,小宇卻説不出話,情急之下,他只能用雙手用力地拍打著大腿。“啪——啪——”的聲音在空曠的走廊裏迴響,小宇的掌心很快赤紅一片。
這是一個大齡自閉症患者家庭。23歲的小宇在兩歲那年被確診了自閉症,經歷了學校、機構、醫院的多年輾轉,最終無處可去的他被經營一家小型外貿公司的父親趙廷帶在身邊——在辦公室外面的茶水間裏,一把綠色的椅子和一張透明的圓桌,是他的位置。
患有自閉症的孩子不會一直是孩子,他們的父母也不會永遠年輕。當曾經的自閉症患兒在磕磕絆絆中逐漸成年,即使沒有其他疾病雪上加霜,單憑他們自己的力量,也很難順利與社會銜接,而與此同時,他們的父母正逐漸老去……這些問題,就像虛空中壓在家長胸口的巨石,帶給這些特殊家庭難以逃離的窒息。
“我的孩子沒有地方去了”
20歲那年,天津市河東區一間由工廠廠房改造的“亞杜蘭學坊”裏,張昊開始了一種嶄新的生活。沒有課的時候,他就坐在辦公室裏用列印紙寫下一些沒人能看懂的數字,喉嚨裏偶爾發出幾聲含混的呢喃,他的母親是這間學坊的創辦者吳桂香,坐在他的對面,溫柔地看著他。
有課的時候,他在其他教室裏學習。唱歌、烘焙,和其他患有自閉症孩子一起學習日常禮儀。他一米八的個頭,膚色很白,眼睛很亮。如果不是與他説話時遲遲聽不到回音,很難相信這個長相英俊的男孩患自閉症多年。
自閉症,又稱孤獨症,專業領域更傾向於稱為“專業發展障礙”,是發育障礙的一種,多數患者伴有智力問題和社交障礙。據五彩鹿自閉症研究院發佈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中國目前已約有超過1000萬自閉症譜係障礙人群。
張昊是亞杜蘭學坊的第一位學生。2016年,這裡第一次招生就接納了8個像張昊一樣年齡超過18歲且存在心智障礙的患者。公立培智學校和私立康養機構認為他們已經超出了受教育的年齡,而他們自身的能力水準又無法正常融入社會。兜兜轉轉,終於在這裡安下家。
對於吳桂香來説,創辦這間學坊的理由很簡單——“我的孩子沒有地方去了。”康養機構不收,張昊就只能被關在家裏。對於自閉症患者而言,長久的封閉,會使得曾經訓練出的生活習慣和自理能力逐漸退化,嚴重時還可能會導致躁鬱。“説起來很多人不信,就一個把用完的毛巾挂回掛鉤上的動作,我教了10多年,好不容易學會了,在家待了兩個月,他就又忘了。”吳桂香説。
張昊的遭遇並不是個例。在吳桂香創辦亞杜蘭3年後,自閉症青年劉銘的父親,51歲的劉碩聯合在培智學校認識的10名大齡自閉症患者家長,在天津市北辰區一個60多平方米的民宅中,也建起了一個家庭式的互助教室,兩三個家長輪流值班,來幫助那些到了就業的年齡,但能力不足或無單位接收的自閉症患者進行能力訓練,産生的一切費用由家長平攤。涂成淡藍色的墻壁上貼著一排模糊的照片,記錄下這幾顆遙遠星星的樣子。
偶然與茫然
劉銘的突然失語,讓劉碩始料未及。
兩歲半以前,劉銘一直是個聰明活潑的孩子,成長軌跡和正常兒童無異。之後,劉銘的症狀逐漸顯露出來,被確診為倒衰型自閉症。
許多自閉症患兒剛一齣生就語言能力發育遲緩、抗拒交流,與他們的父母相比,命運給劉碩的打擊來得更晚些,卻更猝不及防。之前還會説、會笑的孩子,一夜之間失語。“就像是正在打遊戲時網路故障,電腦裏的小人失去了和外面的聯繫,他就困在那裏,動不了,也出不去。”
從兒子確診自閉症開始,劉碩的情緒像坐過山車。在漫長的否定期之後,他接受了現實,開始帶著兒子進行能力訓練。那時他年輕,為了照顧兒子,把手頭的生意扔到一邊,有用不完的熱情。兒子怕生,不願見老師,他就自己錄視頻,從生活小事到溝通禮儀,一百多集,存在電腦裏放給兒子看。
陪兒子聽音樂,教他畫畫、讀書給他聽……劉碩希望兒子“能感知到一些精神層面的東西”。
劉碩對兒子的教育是成功的。在自閉症患者的群體裏,劉銘絕對是“優等生”。他情緒穩定,能做手工,能畫畫,還會彈鋼琴。有陌生人和他交流,也能用簡單的詞句表達。
即便這樣,劉碩還是覺得不夠。他希望自己能跑贏時間,在人生走到盡頭後,劉銘可以活下去。為此他發起了互助教室,就算他贏不了時間,11個同病相憐的家長,也可以在未來漫長的人生中彼此分擔,相互照顧。
“在父母走後,活下去。”聽起來很簡單的事情,對於自閉症患者的家長來説,卻可能是此生無解的難題。
在兒子患病20多年的時間裏,對身體病痛和年齡衰老的擔憂,隨著張昊抽穗拔節的身高,一天天瘋長在吳桂香的心裏。關於怎麼教育這些自閉症青年,讓他們能在沒有父母照顧的情況下,繼續走完自己的一生。迄今為止,沒人能夠找到答案。
2016年出版的《中國孤獨症家庭需求藍皮書》顯示,中國成年自閉症人士的就業率不到10%。“從學校畢業了之後去幹嘛是一件很難的事。很少有人願意招收一個自閉症患者,哪怕他的能力是可以的。”吳桂香説。
這也不是“只要我願意花錢,我就能自救”的事。吳桂香現在還記得,曾在培智學校認識一個學生家長,家中條件富裕,孩子患自閉症多年。孩子父母和親戚們説,“只要有人能在我們死後幫忙照顧孩子,我們願意把所有財産全部贈予,但沒人願意。”
自救和互助
經過了5年的發展,亞杜蘭學坊已經收容了20多個孩子進行康復訓練。欣欣向榮的小小課堂依然不能緩解吳桂香的焦慮。“就像‘亞杜蘭’這個詞的意思,它其實就是一個避難所,但未來會怎樣誰也不知道。”
許多家長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曾做過理財顧問的家長,研究過一款專門針對自閉症患者的香港信託産品;吳桂香則在幾年前參觀了享有盛名的“櫸之鄉”,那是一家日本自閉症患者終身養護機構,福利性質,享有政府補貼,大齡自閉症患者可以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完成簡單的手工作品,以自食其力,用售賣作品存下的錢支付養老費用。還有被家長寄予最大希望的“雙養模式”——父母在退休後帶著孩子住進養老院,家長故去後,孩子再由養老院繼續照顧。
每一條路,都寄託著家長們無盡的期待。但眼前最大的困難是,針對大齡自閉症患者的托養照護問題,目前尚無適應性強、複製率高的具體途徑。雙養機構需要補貼,陽光工場需要場地……要解決這些難題,僅靠家長自救,可以説是杯水車薪。
大齡自閉症患者無法融入社會,家長又要扛起家庭的責任,在他們從特教學校畢業的那天起,就仿佛消失在了人們的視野中。自閉症患者處在極端自我的精神世界之中,長時間不跟外界溝通,能力就會退化,情緒也會受到影響,久而久之甚至會出現暴力行為。“我之前去過一個家庭,孩子30多歲,用繩子綁在家裏。孩子的父母告訴我,長時間無法融入社會,他的情緒很不穩定,家裏很多東西都會被他砸碎。”劉碩説。
未來和希望
自力更生,帶領這些自閉症青年在社會中生存下去,給家長們帶來的體驗是複雜的。他們得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成就感和來自孩子們更為積極的反饋,但也更直接地感受到來自現實的重重阻力。
吳桂香決定建設自己的“櫸之鄉”。“我希望未來的亞杜蘭會是一個結合心智障礙患者輔助性就業、康養的機構,我們的孩子能夠在一個適合他們的環境裏,實現全面發展,有尊嚴地生活。”
這條路並不好走。雖然現在公眾對於自閉症患者的接受度在提高,但那些細微的偏見依舊無處不在。吳桂香想要在亞杜蘭學坊裏建一個烘焙作坊,通過網店線上售賣,孩子們能以此實現自給自足,甚至還可以上社保。
最初她很樂觀,以為只要能保證生産環境乾淨衛生,孩子們能夠熟練安全地操作設備就行。經過兩年多的訓練,孩子們學會了烘焙、裱花,做出的蛋糕好看又好吃。他們還帶著這些蛋糕參加過義賣,收到的錢全部捐到了貧困山區,給那些和他們一樣需要幫助的孩子。
那時她真心相信,她的孩子們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養活自己。但過了一段時間,她發現,總有一些時刻,她能窺見橫亙在外界與自閉症患者之間的,那道若隱若現的門檻。比如在辦食品衛生許可證時,有工作人員明晃晃地質疑:“他們有資格做蛋糕嗎?”
劉碩也是一樣。每週二和週四的下午,是他們的體育課。他會帶著孩子們去小區邊上的公園做體能訓練,多和人群接觸利於他們溝通能力的提高。孩子們排著隊,規規矩矩地走,在控制不住大叫時,家長們會立刻製止,他們盡可能地把自己隱藏在人們的視線之外。即使這樣,還是會遇到被圍觀的窘境,“人們圍著,用手機拍,我們就只能帶著他們回去,像逃跑一樣。”
看不見的門檻和偏見難倒了他們——因為還沒辦下來食品衛生許可證,亞杜蘭學坊裏的十幾個成年自閉症患者,只能在彼此過生日時做蛋糕給自己吃。2015年,中國殘聯、國家發展改革委、民政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關於發展殘疾人輔助性就業的意見》,其中規定,到2017年所有市轄區、到2020年所有縣(市、旗)應至少建有一所殘疾人輔助性就業機構,基本滿足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體殘疾人的就業需求。劉碩拿著文件去小區對面新建的黨群中心,希望能夠分出一塊場地給孩子們建輔助性就業的陽光工場。老年人的合唱室慢慢建起,能夠決定孩子們余生的工場卻遲遲沒有回音,“告訴我們等,可是沒人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從現實的層面來説,家長們對大齡自閉症患者余生的探索就是這樣了:只有極少數能力強、運氣好的孩子,能夠在社會的包容和接納下,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剩下的絕大多數,在各類機構和家中輾轉,磕磕絆絆,等待著一道光,能從他們生命的裂縫中照進來。(劉元旭、梁姊、尹思源)(文中部分受訪對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