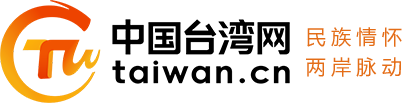三星堆文物為何再度引發高度關注
三星堆文物為何再度引發高度關注
【文化評析】
近來三星堆遺址又“火”了!在這一輪考古挖掘中,新發現的6個坑已出土金面具殘片、青銅神樹、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其中一件黃金面具體量非常大,有可能成為國內所發現的同時期最大黃金面具和最重金器。一時間網上熱議不斷,甚至有媒體將三星堆稱為“熱搜頂流”。
公眾紛紛討論三星堆遺址,彰顯了三星堆的獨特魅力和深沉內涵,強化的是文化自信的力量。申言之,一個擁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民族,其文明必定是持久、厚重、包容的,其自身主體性一定是鮮明、強烈、穩固的,三星堆遺址正印證了中華文明的如上特質。
三星堆遺址立足於中華文明的歷史厚度。3月22日,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朱熹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有什麼中國特色?”悠久綿延的中華文明如同一棵歷史沃土培育的參天大樹,枝繁葉茂,碩果纍纍,從枝葉可以追溯到根脈。三星堆遺址便與古蜀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認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別位於成都平原至川東及三峽一帶的兩支青銅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處,因而又共同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大文化圈(區)。自夏時期起,這個文化圈內開始滲入一些二里頭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時期,又大量接受了二里頭和殷墟文化的影響。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國考古學文化總譜係中的位置。”三星堆遺址共分四期,依次約當新石器時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最早的寶墩文化距今約4800~4000年前,歷史可謂悠久,其積澱亦因之深厚。
三星堆遺址彰顯著中華文明的文明高度。恩格斯在其經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認為:“文明時代乃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産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個過程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産,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他進而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以此論斷反觀三星堆遺址,其文明特徵極為顯著。從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盉與二里頭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質和大小以外,幾無區別;三星堆的“將軍盔”,也與河南安陽殷墟的同類器物非常近似。從青銅器上看,三星堆的銅尊、銅罍明顯受到了殷商青銅禮器的影響,可知在與彼時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匯中,古蜀文明得到了較大發展。
更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諸多帶有強烈信仰色彩的特徵性器物説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極一時的蜀地共主——魚鳧王朝的都城。這恰可與《蜀王本紀》中“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之記載相印證。古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神像、禮器和祭品,説明瞭古蜀文明的神權國家發展到了一個高峰,通過神權與王權的結合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燦爛文明。
三星堆文明呈現出中華文明的交流廣度。三星堆遺址具有東、西方文明的許多共同特質,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燦爛結晶。依據已發現的諸如金杖、青銅雕像、海貝等文物,我們可以大致判斷早在那時,古蜀國先人已與印度、中亞乃至兩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觸。由此設想,三星堆文明雖處於所謂“華夏邊緣”,但卻與西北方向的“陸上絲綢之路”很早就有著固定交通路線,南面可通過滇、緬、印之間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亞、東南亞以及中國沿海各地,甚至可以穿越歷來被視為“人類生命禁區”的青藏高原,與該地域文明發生交往。因此青銅時代的巴蜀與外部世界,絕不是一個彼此封閉的空間,這種開放性與包容性,給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強力支撐。
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它關乎對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歷史脈絡的探尋,對中華文明燦爛成就的理解,對中華文明世界貢獻的把握,更關係到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心、歷史主體性、民族凝聚力的認知與塑造,意義堪稱重大。80多年來,幾代中國考古學人篳路藍縷、接續探求,終於讓三星堆遺址綻放出絢爛的文明光輝。我們相信,此次的考古發現,也僅是輝煌博大的中華文明遺存之冰山一角,今後的發掘研究前景更可期,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事業定當再上層樓。
(作者:王學斌,係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