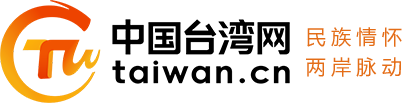藝術史上最美的十匹馬

畫中的馬找到了藝術史上的騎手,他們有馬的騎馬,無馬的騎夢。
從16000年前石器時代的法國拉斯科洞窟畫開始,馬就是藝術家最愛表現的動物。這大概是因為相比于其他非人類夥伴,馬有更多的靈性,更能與人溝通。
在繪畫中,馬最早是獵物,隨後成為衝鋒陷陣的戰馬,或者充當偉岸者的坐騎和勞動者的同伴。在整個藝術史中,只有宗教藝術鼎盛的早期基督教和拜佔庭時期比較少見馬的蹤影。在中世紀,城堡和騎士又怎能少得了馬?而到18世紀以後,馬在繪畫中經常與賽馬、獵狐等運動相關,德加就以描繪賽前的馬場而聞名,斯塔布斯筆下的賽馬更是匹匹鼎鼎大名。
每個時代的藝術家依照當時的潮流,都對馬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從巴洛克到浪漫主義到印象派再到抽象主義,繪畫語言不斷變化,對馬的解剖學研究逐步讓位於感性表達,在法國立體派畫家梅欽赫爾(Jean Metzinger)筆下,馬也變得跟“下樓梯的裸女”(杜尚)一樣難解。
在繪畫中,當馬的角色是坐騎,是忠心耿耿的隨從時,它總要與畫面的主人公相得益彰,比如説,委拉斯凱茲畫中羅斯王子胯下的小胖馬就跟王子一樣奶聲奶氣純真可愛(《羅斯王子騎馬像》,1635—1636),而大衛筆下的戰馬則跟正欲穿越阿爾卑斯山的拿破侖一樣打了雞血似的亢奮(《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口的拿破侖》,1800—1801)。
當馬作為畫面的主角時,它就是畫馬者的代言人。唐代的韓幹、宋代的李公麟、元代的趙孟頫固然不會直接將情懷題寫在馬旁,但其畫風中卻都隱含著教養和趣味。相比起來,當代人畫馬反而顯得太熱衷於注入意義。喜也好,怒也好,都不能由畫家來説,而要讓馬在紙上説。
在歷史上那麼多畫馬的傑作中,以下是最令人難忘的馬。其中有自唐代穿越而來的胖馬,也有為民族存亡奔波的瘦馬;有風中淩亂的馬,也有巋然不動的馬;有半途而廢的馬,也有因為太完美反而被討厭的馬;有市井間的勞動馬,也有馬戲團的聲色犬馬;還有畫家進行色彩與線條實驗的鮮艷馬。
《列子》中九方皋是相馬的高手,而在布羅茨基的詩歌《黑馬》裏,馬才是伯樂,“它在我們中間尋找騎手”。畫中的馬找到了藝術史上的騎手,他們有馬的騎馬,無馬的騎夢。
最神氣活現的馬:《照夜白圖》
唐代女人以胖為美,馬也是胖的好。照夜白就是一匹肥馬,杜甫還曾在《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中批評韓幹把馬畫得太肥了。
照夜白是西域大宛國進獻的“汗血馬”,作為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騎,照夜白平時吃得好養得好,除了皇帝誰都不能騎,所以膘肥體壯、油光锃亮。也因為是皇帝的馬,照夜白神氣活現,仰頭嘶鳴,奮蹄欲奔,拴也拴不住。在韓幹畫的那麼多馬中,照夜白是最有個性的,甚至看起來像是玄宗附體,簡單幾筆稍加渲染,已經勾勒出雄赳赳的姿態。
畫中馬的頭、頸、前身是真跡,後半身是補筆。畫上有南唐後主李煜所題“韓幹照夜白”,又有唐代張彥遠、宋代米芾題名。卷前有何子洇、吳説題首,卷後有元代危素、沈德潛等十一人題跋。
最風中淩亂的馬:《調良圖》
一陣大風刮過,吹亂了馬的鬃毛,吹飛了馬的尾巴,還差點吹掉了牽馬人的帽子。雖然馬一點兒也沒有動,只是穩穩低著頭,雖然趙孟頫沒有畫周圍景物,也沒給馬配上精美的鞍具,馬還是顯示出生動的動態,一眼望去,好像在看一幀動畫。馬是黑底的,人是白描的,畫得秀氣細膩,牽馬人似乎正在跟馬説話,問它感覺怎麼樣,是不是還願意繼續往前走。
趙孟頫潛心鑽研畫馬,明代王樨登在《浴馬圖》的跋語中就提到,趙孟頫畫馬十分投入,“嘗據床學馬滾塵狀”。《調良圖》是一幅真正以靜制動的佳作,誰看了都會相信風很大,誰看了都會同意馬很美。
最半途而廢的馬:斯福爾扎銅馬草圖
1482年,達·芬奇接受米蘭公爵盧多維科·斯福爾扎(Ludovico Sforza)的委託,為他製作世界上最大的青銅馬雕像。達·芬奇不僅希望這匹馬是世界上最大的,還希望它的姿勢是世界上最威的——兩條前腿騰空躍起。為此,1491—1493年間,他繪製了大量的草圖,跟他大多數的繪畫一樣,草圖沒有完成,但是照樣完美。
草圖雖好,可是在15世紀的技術條件下,達·芬奇做不到將10噸青銅溶液快速鑄模,也就無法讓世界上最大的馬用兩條腿站穩,他只能改變方案,讓馬採用傳統的小跑姿勢。1498年,達·芬奇還沒想到解決的辦法呢,斯福爾扎家族在米蘭的統治就被法國人推翻了,斯福爾扎銅馬的黏土模型被法國弓箭手拿來當靶子練箭了。
最令英國人討厭的馬:《響外套》
喬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畫了一輩子馬,這匹叫響外套(Whistlejacket)的馬是其中最完美無瑕的一匹。作為明星賽馬,響外套君在1759年的一場比賽中為它的主人羅京安侯爵贏得了2000英鎊。並且它成功地挂進了英國國家畫廊,成了偶像級的“國馬”。
但是,這匹閃閃發光的大馬竟然被英國人選為最令人討厭的十幅畫之一。倫敦現代藝術學院常務董事蓋伊·彼埃科恩評價説:“我始終無法認可對動物的崇拜,過於巨大的動物往往給人一種可怕的感覺。”
斯塔布斯的動物並不總是如此咄咄逼人,相反地,他最著名的馬是《被獅子驚起的馬》,而他對馬的深度了解也使1766年出版的《馬的解剖學》成為英國出版史上的名著。
斯塔布斯畫的馬甚至比大多數純種賽馬還要值錢,2011年,他繪製的18世紀賽馬名駒Gimcrack在倫敦佳士得拍出3600萬美元,創下他本人作品的世界拍賣紀錄。
最欲説還休的馬:《白色馬頭》
泰奧多爾·籍裏柯(Theodore Gericault)愛馬成癡,21歲時就因為畫了《輕騎兵軍官》而獲得金質獎章。為了研究馬,1814年他參加了復辟王朝路易十八的近衛騎兵隊;因為接近馬,1824年1月他墜馬而死。
《賽馬》、《輕騎兵軍官》、《艾普松賽馬》……籍裏柯畫馬的作品有上千幅,大多表現馬的動態。在若干名作之外,最令人感動的是這幅靜若處子的《白色馬頭》,他畫白馬的方式不像是在描繪動物,而像是在為一個朋友畫像,把它當作可以平等交流的同類。溫馴而堅定的棕色眼睛,斜披的鬢髮,仿佛從血色背景中款款而來,似乎欲言又止,又似乎歷經磨難。
最草根粗豪的馬:《馬市》
看了《馬市》,你也會為趕馬的漢子擔憂,擔心他們不能控制騷動的馬群。但同時,肥壯結實、毛色神態各異的駿馬又十分養眼,塵土飛揚,陽光打在它們身上,每一匹馬都活靈活現,呼之欲出。
羅莎·博納爾(Rosa Bonheur)以畫動物而聞名,為了研究動物的畫法,她甚至在工作室旁邊建了一個動物園,以便進行觀察。她在羅浮宮的名畫《納韋爾人的耕作》繼承了巴比松畫派的現實主義技法,為她贏得了跟米勒一樣的美名。跟斯塔布斯的良駒比起來,她的馬不是只拿來玩賞的,而是要勞動的,因此多了些粗豪的活力。
最聲色犬馬的馬:《在費爾南多馬戲團騎白馬》
亨利·德·圖盧茲—勞特累克(Toulouse-Lautrec)在17歲畫下白馬瞪羚。當時,他剛剛放棄巴黎的學業,在專畫動物的聾啞畫家魯尼·布蘭斯多的畫室學習畫畫。近乎于一張白紙的瞪羚正是他此時狀態的寫照。
因為父親就是一個熱衷跑馬打獵的貴族,勞特累克從小就熟悉馬,喜歡馬。當他在蒙馬特展開聲色犬馬的畫家生活後,馬在他畫中的形象也發生變化,變成費爾南多馬戲團女演員身下模糊的一團白。畫中的馬似乎正在努力奔跑,但已經力不從心,只能任由馬戲班主對它揮舞皮鞭。馬上的女孩與馬的命運類似,她可能就是勞特累克、雷諾阿和德加共同的模特蘇珊·瓦拉東,以前的費爾南多馬戲團女演員,因為一次事故墜落受傷,被迫離開馬戲團當上了繪畫模特。
最童話的馬:《母馬與小馬駒》
羅伯特·貝文(Robert Bevan)畫馬深受雷諾阿的影響,又有梵谷式的筆觸。在他之前,這種體積感和大面積的顏色只被用於風景和人物畫。在《母馬與小馬駒》中,貝文使用了與現實不符的美麗暗色調,馬的身體結構很準確,但是以一種最簡約的方式呈現,草地與樹林也畫得十分精確,包括陽光照射留下的影子。
貝文的馬母子可以看到阿旺橋畫派(Pont d'Aven)的影響,質樸自然,又十分純真,仿佛童話故事中的場景。他運用了高更的色彩平涂和輪廓線,強調裝飾性,是那種兒童也會喜歡的嫺熟之作。貝文去世100年後,他的畫法才得到認可,作品由子女捐入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
最鮮艷的馬:《藍馬》
弗朗茲·馬克( Franz Marc)的《藍馬》不合常理,但它們最顯著的優點也是顏色完全不對,弧線優美的動物形體和風景配上最挑釁性的色彩,看起來卻那麼和諧。
整個畫面只有藍、黃、綠、紅四種顏色,馬克把三匹馬都畫成純藍的,把山丘畫成藍、黃、綠、紅四色。在他眼中,藍色代表陽剛之氣,黃色代表溫柔性感,綠色代表藍色與黃色的和諧,而紅色則代表沉重暴力。
和康定斯基等其他青騎士社的成員不一樣,馬克一點也不抽象,他最好的作品都是以動物為題材的。他説:“屬於動物生命的純潔感覺激起了存在於我的那些善良的東西。”
最憂國憂民的馬:《奔馬圖》
徐悲鴻的馬是典型的瘦馬,憂國憂民,奔走呼號。兒子徐慶平評價他的馬時説:“那些‘馬’不僅僅是普通的畫作,是他對那個時代的理解,是他的期盼。”他最為知名的《奔馬圖》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長沙會戰期間,當時我方一度失利,長沙為日寇所佔,正在馬來西亞檳榔嶼辦藝展募捐的徐悲鴻聽聞國難當頭,心急如焚,他連夜畫出《奔馬圖》以抒發自己的憂急之情。
徐悲鴻的馬成為近代中國獨一無二的馬不僅是因為技巧,還因為他的馬與“奮起抗爭的中國人”有關。這層意義主導了日後中國人畫馬賞馬的趣味,總是強調一馬當先、馬到成功。(孫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