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契弗創造了小說藝術的“珠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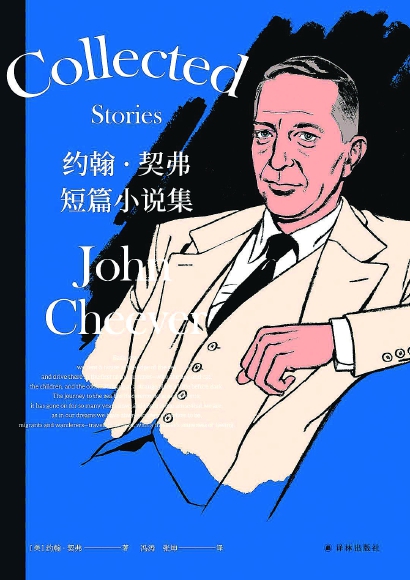
約翰·契弗短篇小說集。
契訶夫似乎被約定俗成地視為衡量作家短篇小說寫作能力的行業標尺,不同時期、不同背景的作家一旦被冠以“×××的契訶夫”之稱,就是對其專業水準的蓋戳認證,可他們中的大多數論風格、論題材,其實和契訶夫搭不上邊。倒是約翰·契弗被形容為“(北美)城郊的契訶夫”,還算有跡可循——他們視線聚焦的淺薄生活與漂浮的情緒,他們不動聲色又登峰造極的“假裝日常”的技巧,以及他們在書寫中流露的溫柔,能隔著漫長的時光和遙遠的地理空間產生共振。可是,如果把契弗安置在契訶夫的坐標係里,這委屈了他,因為他並不需要蹭對方的名望。
英國劇作家庫瑞什說得漂亮:契弗一直是完完全全的他自己,他以幽默的同情捕捉到生活中意味深長的時刻,他有能力用每一句恰如其分的句子,讓一切細節在最後時刻以酒神慶典的方式被升華。
從平凡的世界進入生活的神話
契弗在日記里表達過一種自我懷疑,他顧慮自己的作品“很有局限性”,題材過分狹窄,沒有時代感和意見領袖的氣質。《阿耳忒彌斯,誠實的打井工》或許可以看作這樣一個“跟不上時代潮流的”“逼仄”的故事。阿耳忒彌斯是個打井工,小夥子為了擺脫某個寂寞的中年主婦雇主,找旅行社報了個去莫斯科的團。他剛到莫斯科就被告知,作為“來自西方陣營的勞動者”,他將得到赫魯曉夫的接見,去酒店的一路上,他看到“無數肖像在百貨店和路燈柱上看著他”。等他渾渾噩噩地坐到莫斯科大劇院里,候了一整晚卻沒有等到赫魯曉夫現身,回旅館的路上,他發現所有的肖像都不見了。第二天,他意外地從一個英國僑民嘴里得知,就在他無所事事坐在劇院里的幾個小時里,赫魯曉夫被廢黜。這個傻乎乎的水管工渾然不知自己正在經歷什麼,他天真地陷入和一個俄國姑娘的露水情緣中,而對方是一位被斯大林清洗的元帥的女兒。于是,小夥子睡了不該睡的人,被遣送回國。他心心念念惦記著有過一夜情緣的姑娘,和對方頻繁通信,竟驚動了兩國的安全部門……風波終于不了了之,小夥子再也沒有收到來自莫斯科的回信,只是,“他經常想到她信箱上的一小塊白漆。天氣轉暖以後,他聽到了具有治愈效果的雨聲”。
契弗寫過很多個類似的故事,歷史的風浪呼嘯,但是大是大非大事件和小人物的小確幸小確喪之間,他關心的是後者。波瀾壯闊的宏大敘事是一種風貌,蕓蕓眾生的悲歡是另一種。他在戰後美國中下層的日常生活中觀察到,“人們生活在心照不宣的宣言中——沒有戰爭,沒有過去,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危險和不幸”。推動著社會進展下去的,不是大人物的生或死,而是萬千普通人既渺小又膨脹的欲望,他們對金錢和美滿生活的渴望,對完美婚姻和愛人的幻想。就像在《那罐金子》里,一對小夫妻從中西部遷居紐約,飛黃騰達的中產夢主宰了他們的人生,大蕭條、參軍、戰事和同伴的死亡都不能中斷那不止不休的渴望。然而命運如同陰險的莊家,反復玩弄著這些兢兢業業經營著“更美好生活”幻夢的人們,直到他們被持續破滅的夢想和無法實現的希望拖垮,“失意如同皮鞭,抽在他身上,痛得他幾乎暈厥”。“財寶這個詞讓他悚然一驚,一時間他倣佛看到喀邁拉,看到金羊毛,看到埋藏在彩虹朦朧光暈中的寶藏。”契弗無暇于觸摸時代的脈搏,卻給無名之輩卑微的發財夢寫出驚心動魄的史詩般的結尾,他從平凡的世界進入生活的神話,他所打量的是最微妙也最重要的事:普通人幽深契闊的精神世界。
他嘔心瀝血地追求著小說的藝術
在《聖誕節是窮人的傷心日》這篇,契弗寫了一個在富人公寓里當值的電梯工,他在聖誕節一早就開始和住戶們訴苦,絮叨著自己的孤獨和委屈,住戶們很同情這個窮困的單身漢,于是每戶人家都給他勻了點聖誕大餐和禮物,到了傍晚時分,他的小工作間里堆滿了美食和各種實用的小件。他因為收獲超額的善意,開心過了頭,給一位有錢老太太開電梯時速度過快,遭投訴後被當場辭退了。電梯工的一天呼嘯而過,如同一個荒唐又蹩腳的笑話,這個寒酸拮據的大叔沒有光輝偉岸的形象,他不壞,只是有些雞賊和猥瑣。契弗寫得格外生動的就是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猥瑣,這其實是庶民欲望里最具有色彩、最值得誠實面對的形態。這篇小說里有一段看似瑣碎,實則微言大義的“閒筆”,電梯工“估算每上下一趟大約八分之一英里,他靠開電梯為生有十年了,他已經經過成千上萬英里的距離,這段距離足可以使他駕著電梯駛過加勒比海的重重雲霧,降落在百慕大的珊瑚海灘。”契弗孜孜不倦寫出來的,正是從生活狹窄的電梯井,駛入杳杳雲霧的意識世界,直到俯瞰無邊無垠的時間。
他對筆下的角色是很溫柔的,雖時不時會揶揄那些虛無的秩序和乏味的品位,但從不以優越的智識感去霸淩平庸盲目的人們,也不會抨擊他們隨波逐流的欲望和夢想。他沒有野心勃勃地把文學當作社會幹預的利器,在他的認知中,“小說就是個實驗過程”。所以他最耿耿于懷的是《紐約客》的編輯讚美塞林格是個“了不起的工匠”,而他沒得到類似評語。
確實,比起契弗書寫的題材,他對小說藝術嘔心瀝血的追求經常被低估了。
在《豬掉進井里的那一天》里,契弗寫了一個紐約闊綽之家在鄉間度假地度過的許多個夏天,其間發生過階層錯亂的小兒女戀情,也重復著社會壁壘被鄉野風光暫時屏蔽的錯覺,這些都不重要,社會等級的議題不是重點。這個故事里的人們如同罹患強迫症一樣,循環地回憶起某個夏日午後層出不窮的狀況,在小徑交錯的意識流的花園里,時間獲得了自由流淌的能量,漂去漂來的歲月像探戈舞步一樣交錯著,衝破線性時間的約束交織出一支回旋的舞曲。很多年後,垂死的契弗被酒精和癌症折磨得面目全非,他在生命的盡頭感慨:一頁好的散文足夠讓作家立于不敗之地。那麼《豬掉進井里的那一天》可以看作是“孤篇壓時代”的不敗之作。其實,無論他同代的評論家怎樣非議他,契弗清醒地知道自己寫得有多好,在《豬掉進井里的那一天》初稿寫完時,他給《紐約客》編輯的信里頗為自得地寫道:“我創作了一部類似回旋曲的作品。”
他在寫作藝術層面大膽冒進,甚至因為過于革新而孤獨。1972年,《紐約客》退回了《卡伯特家的珠寶》,編輯認為這根本不算小說。然而半個世紀後的敏感讀者讀到這部偽裝成漫遊隨筆的小說,會驚訝于契弗的藝術實驗比這個時代的寫作者更超前,他在三言兩語的篇幅里觸及了短篇小說隱秘偉大的秘密:它收容著各種無法進入情節的情緒,隨時隨地地衝破時空阻礙,訴諸于浩瀚如星空的意識世界。今天的讀者應該慶幸契弗留下了《卡伯特家的珠寶》,留下這麼多無法被歸納的趣味盎然的短篇小說,它們是小說藝術中異常貴重且璀璨的“珠寶”。(記者 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