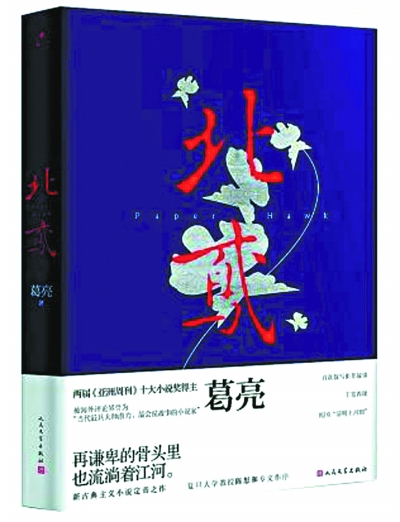
《北鳶》 葛亮 人民文學出版社
杜唯
可以說,小說《北鳶》的問世自帶光環。作者葛亮,是目前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文壇備受矚目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七年前他的第一部小說《朱雀》便艷驚四座。 若說《朱雀》是以南京為中心,敘述後工業時期南京依稀留存的古都氣象,那麼這本耗時七年寫作的《北鳶》講述的則是北地的故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譎雲詭的民國史中,襄城商賈世家盧氏公子盧文笙與沒落士紳家族馮家小女兒馮仁禎的命運,如風箏線般千絲萬縷地纏繞與牽扯。動蕩年月中,兩個家族的興衰與整個民族的跌宕流離也隨之浮出水面。
說《北鳶》備受矚目,自然還有另外一個緣故:但凡說起葛亮與該書,都逃不開其中暗藏的家族隱喻,也有人認為這是葛亮向《紅樓夢》致敬的家族小說。誠然,葛亮在文中埋下了些寫實的線頭:主人公盧文笙的原型是葛亮的外公,與盧文笙亦師亦友的毛克俞的原型是葛亮的祖父、著名藝術史家葛康瑜;而書中的石玉璞,暗指的是他的姨夫、上世紀20年代曾任直隸省長兼軍務督辦的褚玉璞,褚玉璞與張學良、張宗昌並有“奉魯直三英”之譽;而葛亮的太舅公陳獨秀也隱隱約約地出現在小說的文字之間。
然而,筆者卻不想像索引派解《紅樓夢》一樣去發掘背後“本事”,也不想把小說歸為葛亮家族記憶的傳承。不妨只把它當故事看。就連葛亮自己都說,他與曹雪芹所處的時代不同,方向也不同,他更沒有著意借鑒《紅樓夢》的意思。不過,若一定要和《紅樓夢》一類的古典家族故事小說類比,不如說是氣質的相倣,也如小說名字“北鳶”昭示的,那像風箏線一樣牽扯著的、如絲縷般不斷的古典文脈。
“這就是大時代,總有一方可容納華美而落拓的碎裂。”在自序中,葛亮的這句話講述了他的視角與情懷。民國史充斥著傳統的零落與向著現代的轉型,他既沒有像海派一樣關注都市的殖民地風情與現代化進程,也沒有蝸居在市井胡同中,以一雙民粹的眼,覷著世界的光怪陸離。家國離亂、民族危亡、愛恨情仇,書中故事自有萬變,葛亮卻以大浪淘沙後的沉淀意蘊,尋求文化因素中一絲不變的東西。它曾經華美,歸于落拓,卻深藏在中國人的骨髓里。
不妨說得誇張一些,《北鳶》中的價值觀是有一點“迂”的,“重儒輕商”的理念在全書開頭就明顯看得出。開篇處記敘了不少主人公盧文笙的母親孟昭如的心緒起伏,分明使讀者知道,盡管她對盧文笙的父親頗有情意,但嫁給身為商人的盧家睦,她還是有些落寞。好在,盧家睦有儒商風度,重信義,心術正,有學識,而最讓她歡喜的,是他身上的“幾分迂”。“我盧家睦,許多年就認一個‘情’字。在商言商,引以為憾,如今未逢亂世,情已如紙薄。”——“這’迂’是旁人沒有的。這世上的人,都太精靈了。”
除卻這上層社會的價值判斷,《北鳶》中涉及更多的是民間的精神脈絡。小說第七章中,盧文笙為抗日瞞著家里從軍,為盧家打理店鋪的鬱掌櫃照著盧文笙寄信的郵戳,一路打聽尋到部隊。鬱掌櫃嘴里口口聲聲叫著“少爺”,撲通一聲跪下苦勸他回家,甚至甘願為讓少爺回家捐出家產。這做派不免也是迂腐的,卻生出無限的情誼。亂世中這人情的溫暖,正是維係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或許葛亮認為,這時代變革都斬不斷的傳統脈絡才是我們的根。
都說葛亮善于挖掘民族文化底蘊,但讓人玩味的是,葛亮對文脈的追尋與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尋根小說路數全不相同。在當年的尋根熱潮中,作家們雖致力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卻往往預設了審視現代性的立場。他們似乎刻意將目光凝聚于蒼莽的民俗之中,呈現出具有前現代風貌的民俗社會,有時甚至可以說是帶著“原始”氣味的社會了。那時的文學作品中,突現不少蒙古草原、西北高原,乃至西南邊陲的意象,總有一絲“莽漢”的氣息貫于其中。誠然,這些尋根小說作家有獨特的價值視角,而葛亮卻與他們不同,他把眼光放置在被現代性浸染、卻依舊流淌著傳統文脈的世俗社會中。
能把這個並不脫離于世俗的社會描繪得如此古雅與豐富,當然還得益于葛亮的抒情筆法。作者的古典敘事手法相當純熟,只看最顯見的引語用法即可體會。全篇小說中,新文化運動後才納入白話文寫作規范的單雙引號式直接引語很少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某某道”“便說”“說道”的敘述,如此句讀,正是《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小說中的敘述口吻。《北鳶》通篇白話文,講的也是民國事,卻不完全依著白話小說的話語形式,此間張力凸顯了古韻,葛亮的敘事水準也可見一斑。
此外,《北鳶》的故事也如古典小說般形成了敘事的循環。小說開篇道來的是盧文笙的身世:他是個被孟昭如抱養來的孩子。而在小說的結尾,葛亮沒有特意表述盧文笙與馮仁禎的結合,而是將故事終結于他們共同撫養了已故親人姚永安的兒子——又是一個抱養來的孩子,身世如盧文笙一樣的漂泊,篇章終了,也在飄零的時代中展開新的故事。這情節的安排,一如《紅樓夢》中從“菱花空對雪澌澌”的氛圍開篇,最終也回歸了“白茫茫大地真幹凈”的情境。如此循環,正是古典小說善用的布局方式,首尾相接又生生不息,恍如沒有結尾的“白茫茫一片”,自有生機無限。
[責任編輯:楊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