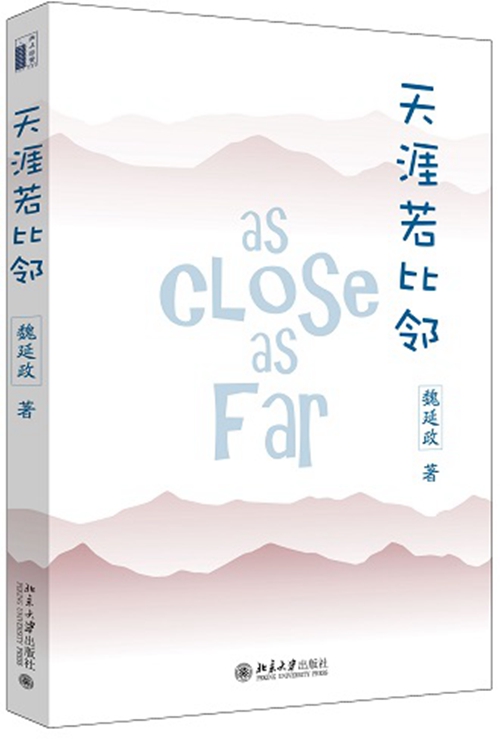
(本文摘自《天涯若比鄰》,魏延政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作者簡介:魏延政,北大校友,2011年不幸確診罹患世界罕見癌症,2012年右大腿截肢後離開工作崗位。在抗癌期間,堅持不懈地讀書撰文,在大型企業以及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名校,分享傳播東西方文化、歐美高端市場拓展、係統化思維、大型企業流程管理、產品管理以及人生幸福理念。2015年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面向全球各企業中高層主管開設的復旦哲學大會課堂上,多次主講《讀書吧,雖然這些知識終將隨著我們的生命而去》《係統化思維——人生幸福最大化》《當霍金說“哲學已死”時,他在說什麼?》《哲學的一萬種可能》,獲得眾多文化、哲學愛好者的好評。不幸的是,2016年年初癌症擴散。在病重垂危的時刻,為指導兒子未來的成長,撰文《人生若如幾回憶》,感動了眾多“魏延政智庫”的讀者。
人生若如幾回憶
朋友,你可曾想過,假如某一刻你的生命倏忽而去,你該給你最摯愛的人留下些什麼?幾年前化療的時候我想過這個問題,後來又活過來幾年,這個思考又被拋諸腦後。這段時間病魔肆虐,我猶如孫猴子被壓在五行山下,躺了半年動彈不得,這個問題便又盤繞在腦海中。人的一生究竟活了些什麼?大多數人都懶得去考慮這樣的問題,或者想不清楚,等到真能想明白點什麼的時候,往往是隱退江湖多年,或者是病到離死不遠的時候。
前些年,在我癌症截肢後最無助的時候,某500強企業向我踹了最狠的一腳——終止合同,人生慘淡莫過于此。我驟然變得如同一片鴻毛一般,無著無落地飄蕩在半空中,當時我設想了一下人生百年可能會有怎樣的百態,細想一下也不過如此:人生啊,活到一十,橫著豎著都一樣;活到二十,睡著醒著都一樣;活到三十,公司家庭都一樣;活到四十,博士文盲都一樣;活到五十,當官百姓都一樣;活到六十,有錢沒錢都一樣;活到七十,睜眼閉眼都一樣;活到八十,男人女人都一樣;活到九十,有腿沒腿都一樣;活到一百,死了活著都一樣!
人能活到像《聖經·創世紀》里那些人那樣動輒千歲嗎?若真能,人最終能記得自己這一生究竟是誰、做過些什麼嗎?第一個一百年做中學教師,當老師當厭倦了,第二個一百年做珠寶生意……如此下去,活著怕是一種負擔,未必每個人都想活那麼長。所以人生百年最好,不勝其煩,在豐滿到裝不下的時候落幕,恰到好處,一生所愛仍歷歷在目。
人一生能愛過幾次?第一次的愛,是依戀,孩童對父母的愛,是用一生來回味的;第二次的愛,是尋覓,我們總是抱以最真誠的願望,卻往往未成眷屬,是用後半生來忘卻的;第三次的愛,是相伴,人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每一階段如畫卷一點點展開,我們沉浸其中,來不及欣賞每一段的美好,只得須臾回想起彼此初見,歲月流年,她可能有某些不如意,但她永遠定格在那個最風華動人的一刻,只有她是用一生來相守的;第四次的愛,是回報,一個小生命的降臨,抱在懷里滿心歡喜,一時不見滿是挂念,是用一生的感悟來回報的。
我算是幸運的,四次愛都經歷過。一生所愛情真意切的幾個瞬間,時常浮現在我眼前。三歲的時候發燒,一個清涼的夜晚,媽媽把一片阿司匹林切成四瓣,給我喂了一瓣,然後到院子里給我把尿,我看見月亮很大、很圓、很亮;五歲的時候,爸爸帶我爬紅山,我跑得比他快,下山後看見羊肉串,爸爸給我買了二十串;七歲的時候,二姐放學後把我抱在腿上講她英語課本中漁夫的故事,大姐在做飯,那時常常停電,爐火把大姐的臉映得通紅;九歲的時候,和哥哥一起把所有樓門的螺帽偷回家,我心里非常不安,下午又偷偷把螺帽一個個全部裝回去,比上午偷螺帽時更緊張;十二歲的時候,晚上做不完數學競賽題,媽媽說“不著急,媽陪著你,做不完,你不睡覺,媽也不睡”,父親串門回來,也坐在一旁陪著我,有不會的難題,父親就來幫我。父母已老,我限于行動不便,願有一日能回到故土給二老正正經經磕個頭,感念養育之恩。我是不是老了?越久遠的事情記得越清楚。人一生究竟能有幾個瞬間讓你挂懷?
中間的幾十年,就像過場,橫著豎著、夢著醒著都一樣,忙忙碌碌含辛茹苦幾十年如七日:忙day(Monday)、求死day(Tuesday)、未死day(Wednesday)、索死day(Thursday)、福來day(Friday)、灑脫day(Saturday)、傷day(Sunday)。全球語言雖有不同,意義卻毫無二致,終究從忙到傷,又帶著傷回到忙。有時我從現年75歲的父親那里也能學到不少哲理,他說人到70歲自然明白退一步海闊天空,那便是孔子說的70歲從心所欲不逾矩吧,父親讀書不多,人生經歷和哲學都來自實踐。
終于有一日,生活有了不同。35歲的時候,我牽著她的手漫步蘇堤,一起唱著《戀曲1990》,那個時節,裙正飄搖唇正紅;翌年,她坐在大皮球上,我拖著她的胳膊,以便小生命向下運動降臨,醫生初時還問我,過會兒會出很多血、會不會暈血,後來便不再問了。我聽見第一聲啼哭、親手剪了臍帶;40歲的時候(去年),有一天他指著幼兒園課本里的天安門說想去看看天安門,第二天,去北京的高鐵上,他在我的懷里睡得很香。
然而自己不幸正值壯年卻病倒了,幸運的是遇到一位好妻子。那年情人節突然腿疼整晚以致無法行走,下午她陪我去醫院。我躺在活動擔架上,她推著我一個科室、一個樓層地走。她纖弱的胳膊常常推不直,左扭右拐。我躺著看著她的衣襟,似乎是她在抱著我走。我想到傑克·倫敦的一篇小說《女人的剛毅》:阿拉斯加天寒地凍,淘金的人們都在絕望地逃離,一對夫婦夜晚時發現一個陌生人在帳篷外的火堆旁取暖,女人出去看了一眼回來說那人快要餓死了。天亮後他們看到那人就死在帳篷外。他倆繼續趕路,幾天後女人也不行了,她告訴丈夫,她知道要走出阿拉斯加,糧食只夠一個人吃,于是省下了自己的那一份。男人痛不欲生,女人說,“你一定要活下去,不僅為了我,還為了我的親哥哥”——那天死在帳篷外的人就是她的親哥哥,他小時候曾從熊嘴里救出自己,為此被熊咬掉了幾根手指,他那晚在帳篷外烤火時她就通過幾根斷手指認出了他,但卻無奈地沒有相認……
我確診癌症一年的一個寒冷的冬夜,我伏在她身上,撫摸著她柔軟溫暖的身體,慶幸自己確實還活著。我望著她,她讀懂了我的眼神,我把臉埋進她的長發,眼睛濕潤了。我體會著她的體溫,我真的還活著。
[責任編輯:楊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