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喝醉”:李杜的詩酒與英譯
作者:孫紅衛(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美國人桑德豪斯(Derek Sandhaus)的《在中國喝醉:白酒與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Drunk in China: Baijiu and the World's Oldest Drinking Culture)(2019年)是一本類似于中國酒文化大觀的書,談論酒在中國的歷史、酒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等。在書中李白、杜甫等好飲的詩人一一登場,共同展現了詩酒的斑斕多姿,彰顯了醇厚的中華文化。在桑德豪斯看來,酒之于中國,猶如“文明之血液”。這是一個有著七千年飲酒歷史的國度。當一個人飲一杯中國酒時,“便融入了一個七千年之久的文化傳統”。

陳洪綬《李白宴桃李園圖》(1650) 資料圖片
一、杜詩與“濁醪”
《在中國喝醉:白酒與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的卷首引用了杜甫《落日》一詩的尾聯“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愁”作為題獻,英譯為:“噢,酒,誰給了你微妙的神力?/只需一小杯便可以淹溺千種的愁。”作為一部介紹中國酒文化的書,這是一個極為巧妙的選擇,一開始便將詩與酒、酒與人生聯係在一起,表述了酒對于中國人生活和文化的重要性。它的英譯並非出自桑德豪斯之手,而是引自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120多年前所譯的一個集子《古今詩選》(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s)(1898年)。在原來的譯本中,翟理斯將《落日》的題名換成了《酒》,但在這里,桑德豪斯又重新改為原名。翟理斯的譯筆淺白曉暢,不過 “濁醪”與“散千愁”兩處均未譯出:前者指未經過濾、粗制的酒,後者指史冊所載的一種被東方朔命名為“怪哉”的小蟲,遇酒即化,故有“散愁”之說。
“濁醪”一詞自帶粗糲之感,有隨性之意,不講究精致。老杜尤其喜歡拿這個詞來指稱酒,在詩中屢屢使用:“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粗飯任吾年。”“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等等。這一方面和他潦倒的生活狀態不無關係——他常常囊中羞澀,無沽酒之錢:“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大詩人胸懷曠達,能夠苦中作樂,隨遇而安;另一方面也有審美的考慮:“濁醪”的要義在于不修邊幅,在于一種質樸無華的感受。“葡萄美酒夜光杯”反而太過強調那種雕琢、修飾、工整的意味,不若“濁醪”來得天然純粹,這正是“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的道理:縱是濁酒,幾杯下肚,亦可讓人陶然忘憂,暫不必挂心仕途坎坷、命運多舛。“濁醪”這個小小的詞,宛若不經意間在文字中投下的石子,激起細微的波瀾,制造了意義表達的起伏蕩漾。若無它在場,詩歌則如一潭止水,太過平淡無奇。由此可見,從文化中提煉出的掌故,既可為詩文增色,亦可以含蓄地表達內容和思想。這麼一來,詩的一呼一吸,都牽連著文化的脈搏。可惜這一層多余的意蘊在譯文中完全消失了。
此外,濁醪、醪糟等詞也指向了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所理解的“wine”的酒文化,其中牽涉中國的傳統釀造工藝。
濟慈《夜鶯頌》里這樣寫道:“啊,但願飲一口美酒,/一口曾在地窖冷藏多年的佳釀!”詩中,“美酒”用的是“vintage”一詞的本意。無論是“wine”還是“vintage”,共有的詞根均是“vinum”(葡萄酒),與vineyard(葡萄園)等詞均指向了葡萄這一原材料。古羅馬人說:In vino veritas(酒中有真理或酒後吐真言),vino便是葡萄酒。與之相比,醪糟、濁醪等詞指向的是谷物類酒,從原材料到釀制工藝都大不相同。以“wine”譯“濁醪”,這種方法對于譯者而言自然簡單易行,不過也暴露了酒在跨文化的旅行中所遭遇的屏障。在很多情況下,譯文很難還原其原初語境進而曲盡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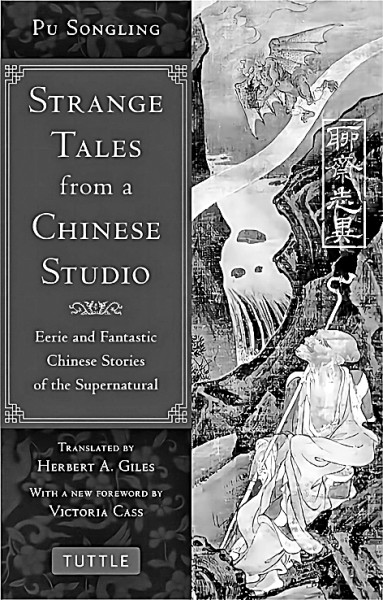
翟理斯譯《聊齋志異》 資料圖片
二、谷物酒與葡萄酒
關于“酒”字翻譯的難度,一百多年前,翟理斯在較早介紹中國酒文化時便深有感受。他認為:現代中國的酒和孔子時代的酒並無二異,都是“由米發酵、蒸餾的烈酒”,“雖然大量詩文顯示中國人在歷史上也飲用葡萄酒,但這種酒自15世紀後便消失了”——當然,他的判斷並不準確,酒的蒸餾技術一般認為開始于元代,中國的釀酒在原材料、工藝等方面也要遠比這句話所傳達的信息復雜得多。不過,翟理斯主要是為了強調中國的“wine”並非西方人普遍理解的“葡萄酒”,以及用“wine”來表達中國酒只是權宜之計,這麼說也無可厚非。雖然在談中國的酒文化時,他援引了古雅典的飲酒風俗來加以比較,認為兩種文化之間有著諸多共通之處,都熱衷于飲酒時劃拳、賦詩、聽音樂,都喜歡在飲到酣暢處換上大杯,“在中國的小說中,半醉的英雄人物總是毫不例外地叫嚷換上大的杯盞”,但是,看似有可比之處的兩種文化之間又存在著巨大的不同。
桑德豪斯的著作也提及了“酒”與“wine”對譯的問題,強調“‘酒’在中文中是一個表意極為寬泛的詞,用來指稱所有含酒精的飲品,包括白酒、黃酒、啤酒和葡萄酒,使得它的翻譯在多數情況下困難重重”。再者,白酒之中,又有不同的品類,如各種香型的區分也不可混為一談:“就像威士忌或杜松子酒的分類一樣,它們除了有著共同的起源,其他方面幾無可通約之處。”桑德豪斯對中國人的造酒術進行了考古,指出“曲”的發明至關重要,讓中國酒的歷史演化從此走向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其重要性不啻于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實際上,他沒有提及的是,在中國的文化中,“曲”會被用來指代酒。元代白樸《寄生草·飲》中寫道:“糟腌兩個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曲埋萬丈虹霓志。”從酒糟到濁酒(也即“醅”),再到“酒曲”,恰巧涉及了中國酒的釀造技術。
不過,唐代的酒既有谷物酒,也有葡萄酒,既有“濁醪”,也有玉液瓊漿。如翟理斯所言,至少在一段歷史時期,谷物酒與葡萄酒都是存在于中國的飲品,只是後者更加珍貴稀有。美國著名學者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在《撒馬爾罕的金桃》里談及唐朝的“外來物”時,就以酒為例,聚焦了中西文化交往之中的葡萄酒。其中《葡萄與葡萄酒》一節寫道,中國人早就“精通從谷物中提取發酵性飲料的方式了”,到了唐朝,“稻米已經成為酒精飲料的主要來源”。不過,隨著唐王朝的日益發達,外國佳釀也傳入中土。“唐朝統治初年,由于唐朝勢力迅速擴張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內變得家喻戶曉”,葡萄酒的釀造工藝也隨之傳入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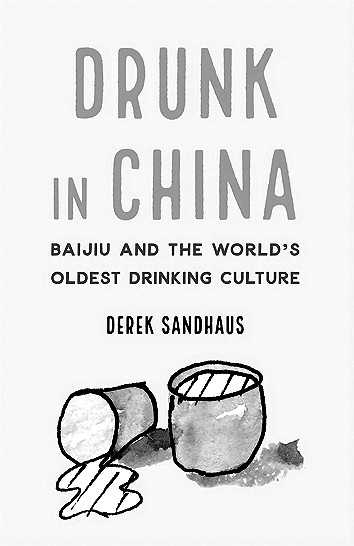
《在中國喝醉:白酒與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 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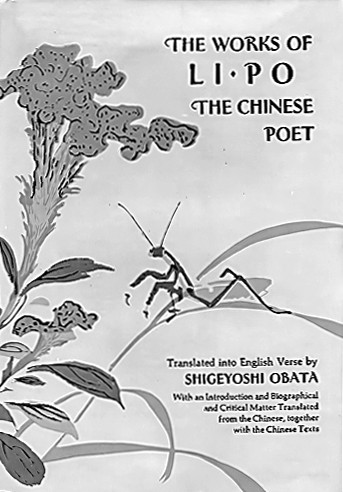
小畑薰良英譯《李白詩集》 資料圖片
三、“糟丘”的譯法
李白詩中,谷物酒和葡萄酒可以並舉。《襄陽歌》里有一句:“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築糟丘臺。”在這里,谷物釀的酒(曲、糟)與葡萄釀的酒共同存在。“糟丘”一詞如其名所示,涉及中國糧食酒的發酵、釀制方式,指的是釀酒後堆積如丘的酒糟,從而被用來指代大量的酒。不過,就譯詩而言,“糟丘”應是一處難以處理的文字。譯者要麼加以簡化,不附任何說明,如《聊齋志異·酒友》有“糟丘之良友”之說,翟理斯譯作“酒友”,以英文習語對譯中文習語,既地道又精準,相較于拖泥帶水的加注式翻譯反倒淺近又富有生趣,是極成功的譯例。“糟丘”這個詞多次出現在李白詩中——“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李白好酒,並且海量,而“糟丘”所指為“釀酒之多,沉湎之甚”,這個詞當然頗得他的歡心。如果“濁醪”是杜甫的心頭好,那麼“糟丘”或許是李白的最愛。聞一多先生談日本學者小畑薰良的英譯《李白詩集》,曾批評他沒有進行適當的甄別,疑似偽詩收了不少,卻沒有收錄《襄陽歌》等佳作,令人遺憾。小畑薰良譯本收錄了《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譯文也是刪繁就簡,取了捷徑,未譯出“糟丘”一詞。
在聞先生看來,小畑薰良的譯本不乏疏漏之處,比如“風流”譯作“wind and stream”,“燕山雪大花如席”的“席”譯作“pillow”,“青春”譯作“Green Spring”。
不過,小畑薰良的譯本,也有可擊節叫好之處。如《金陵酒肆留別》一詩的翻譯,“吳姬壓酒喚客嘗”譯作:“While the pretty girls of Wu bid us taste the new wine”(吳地美麗的少女請我們品嘗新酒)。譯文讀來生動活潑,尤其是“新酒”一詞既淺切形象,又天真爛漫。原詩中的“壓酒”是汲取新釀的酒,“米酒新熟,壓而取之。”小畑薰良將這個細節去掉,直接譯作“新酒”,應屬“就地取材”。一來西諺有源出《新約》的“舊瓶裝新酒”一說,引入此處信手拈來又合乎情理;再者,“新”一詞也可能不小心泄露了這部譯詩的一個參照對象:小畑薰良自序中提及大詩人龐德由日文轉譯的李白詩歌。20世紀初,為了一反英美詩壇陳陳相因的現狀,龐德將中國古詩作為改觀英語詩歌的源頭活水,提出了現代派文學的著名口號“make it new”(日日新),它便源自《大學》的“茍日新,日日新”。“新”字概括了現代派詩學主張的內核,影響深遠。當代漢學家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先生所編中國古詩集《中國古典詩歌新選》(The New Directions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採擷了李白、杜甫等歷代詩人的名作,封面上便寫著幾個大大的漢字“新日日新”,也是與20世紀初的“尚新”之意形成回響。
顯然,小畑薰良此句的翻譯對原詩的信息進行了取舍,可謂舊瓶裝新酒。這一改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聞先生也指出:“但是翻譯當然不是給原著的作者看的,也不是為懂原著的人看的,翻譯畢竟是翻譯,同原著當然是沒有可比性的。一件譯品要在懂原著的人面前討好,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酒文化的傳譯自然也不必非要拘泥于字面意義上的完全對等,有時需要採用適當的歸化手段,將酒譯成熟識的酒;有時則需要異化的傳譯,作為一個陌生物、舶來品安放到另一個語境中,引發不同的想象。

翟理斯 資料圖片

德加《苦艾酒》(1875-1876) 資料圖片
四、“舶來品”與共享的詩意
唐朝人熱衷于將新奇的事物入詩,變成一種特殊的意象。“葡萄酒在當時的確被認為是一種能夠喚起迷人的聯想的、精純稀有的飲料。”薛愛華指出,“在8世紀時,葡萄雖然已經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然而杜甫還是在一組新奇陌生、非漢地物品的比喻中使用了葡萄這個詞。他在詩中以‘葡萄熟’對‘苜蓿多’——兩種植物都是在公元前2世紀時由張騫引進的,而且都是相當古老的比興對象,在這首詩中,杜甫還以‘羌女’與‘胡兒’相對。”在李白的詩中,葡萄酒、金叵羅、鸚鵡杯,都屬于相對陌生、稀有的事物,因而天然帶有幾分神秘和浪漫。薛愛華說:“舶來品對人們有著強烈的吸引力。”來自一個陌生文化的名字總帶有一絲神秘感。即使我們對于這個名字的意思不明就里,也不認識以此為稱呼的人,也會覺得它帶著某種異域的、審美的色彩。柯勒律治的名詩《忽必烈汗》,第一句就是忽必烈汗在大都建了座長樂宮。無論是“忽必烈”還是“大都”,詩人都是要一下子就把西方的讀者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錢鐘書先生就說過,不識地名人名之美者不足以言詩——如果從地名、人名里體會不到美,就缺少一種談詩的感性了。
在一定程度上,名物的稀有性,也賦予其一種特殊的陌生感,或者是音樂感,然後讓我們覺得它所形容的人或者物是超凡脫俗的。從文化交往的另一端看李白,道理也是相通的。無論是他的好飲,還是他的詩名,皆是陌生的存在,所以對于英語讀者而言天然地具有詩意或者是浪漫感。當代愛爾蘭詩人馬洪(Derek Mahon)有一首題為《一個好奇鬼》的詩,其中寫到了曾任船長的岳父,並設想了在另一種生活里和他轉換了身份,這位船長可能是一位詩人,而自己則是一名水手:“……我曾申請加入商船海軍/卻未通過視力測驗/後來淪為一個瘋癲的抒情詩人。/你如李白一般失衡落水後,/他們在你的儲物櫃里發現了未發表的詩篇。”這里將中國唐代詩人李白和自己的岳父相提並論,將詩的藝術追蹤到遙遠的異域與久遠的年代,通過這種跨越表達了詩的親切、樸素與恆長。詩並不專屬于某個群體,而是一種跨越民族、超離時空的共有的藝術。
太白好酒,有“因醉入水中提月而死”的說法,雖是傳說,不過卻也符合他的氣質,對此西方人亦有耳聞。翟理斯《中國文學史》對此就有提及。桑德豪斯所編寫的中國酒的編年史專門列出了李白的出生年份,第二章篇首便援引了李白的《將進酒》,也提及了他醉酒後在揚子江中撈月溺亡的傳說。在另外一首詩中,馬洪寫到了“黃河月色”,讓人想到了李白詩中的黃河意象。中國的黃河與愛爾蘭本土的景觀毫無違和感地出現在同一首詩中,形成了一種新奇的回響。無論李白用“葡萄酒”“金叵羅”,還是馬洪用“李白”“黃河月色”,兩個相對陌生的名詞,將這兩首詩預設的讀者瞬間遷移到另一個時空之中,傳達了神秘的詩意。
酒可以引起頗具浪漫色彩的想象,成為一種文化、一個人群、一個時代的文化表徵物。酒也因為這樣的聯係具有了個性——朗姆酒讓人想到了海盜,杜松子酒讓人想到18世紀的英國民眾,想到荷加斯的畫,苦艾酒讓人想到19世紀的歐洲藝術家,想到凡·高、波德萊爾。酒自然也能成為某一人物最具標志性的符號,比如詹姆斯·邦德總要飲一杯:“馬提尼,搖晃,不要攪拌。”真實的人物也是如此,比如大詩人布羅斯基來到美國,留給當時英美詩壇的一個印象就是他嗜飲絕對牌伏特加,以至後來的傾慕者也要買來品一品滋味兒;又如,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侄女寫的《美國大作家的烹飪書》詳述了福克納“秘制”的熱托蒂酒——一種據說可以治療感冒的甜酒的制作方法,讓這種酒從此沾上了福克納的記憶。
在世界文化中,李白、杜甫素有酒名,酒也成了他們的一種標志性符號。從翟理斯,到小畑薰良,再到桑德豪斯,他們所收錄的李白、杜甫的詩歌中,飲酒詩佔十之六七,連題目中都處處點綴了酒的字眼,當然也播散了他們的好飲之名。在酒與詩的故事里,折射了人性各種復雜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古今、中外均可以共情、互通,我們在人生得意時,會開懷暢飲:“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在失意後,也會舉杯痛飲、慷慨悲歌:“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這些詩歌讓詩人不朽,也讓我們在推杯換盞或對影獨酌時“融入一個七千年之久的文化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