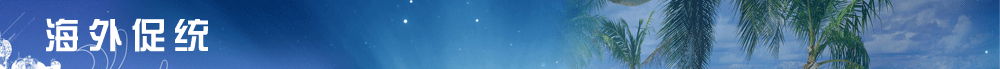|
陶短房:歷史不是做燒餅
在MSN上,陶短房回復總是很慢,給人以錯覺,以為他是個慢性子的南方人。他的《這個天國不太平》曾風靡一時,其中立論處處嚴謹,引證繁複,學究之氣撲面而來。
然而,電話中的陶短房完全不同,詞鋒激烈,反應迅速,夾雜著大量的反問句,儼然是大專辯論賽的口吻。
陶短房做過很多年外貿,在羅爾綱先生的鼓勵下,他靠自學成為歷史學者,並在太平天國研究方面頗有建樹。陶短房侃歷史,充滿趣味,因為他以更豐富的生活經驗為鋪墊,所以總能猜出你的潛臺詞,你在想什麼,然後提前把你下一個問題給回答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離不開海外華僑的巨大支援,在海外漂泊多年,讓陶短房對此有更深入的理解,那種背井離鄉的緊張感,國內讀者很難有所體會,而正是這份緊張感,開拓了中國人的現代之路。
加拿大華人不忘辛亥
北京晨報:對於辛亥百年,加拿大社會反響如何?
陶短房:對西方人來説,辛亥革命是個很模糊的概念,甚至一無所知,他們中許多人甚至對中國都不太了解,但對加拿大華人來説,辛亥百年是個繞不過去的日子,辛亥革命前,孫中山三次到加拿大籌款、宣傳革命,在推翻清王朝的歷程中,加拿大華僑發揮了巨大作用,許多子弟加入了革命黨,1911年5月,致公堂賣掉黨産,支援革命。對於辛亥革命,加拿大僑界非常重視,相關紀念活動一直很隆重。
北京晨報:為什麼加拿大僑界這麼重視辛亥革命?
陶短房:加拿大是華僑重鎮,洪門要地,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都曾在這裡活動過,著名的革命與改良論戰,維多利亞和溫哥華就是主戰場之一,許多華僑組織從當年傳承至今。1911年,海外同盟會與致公堂全面合作,孫中山本人也加入致公堂,這是洪門的一支,1903年孫先生便已加入了洪門,所以洪門認為辛亥革命是自己的事。
海外洪門為何崛起
北京晨報: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將洪門看成是黑社會。
陶短房:洪門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組織,分支極多,有的分支如三合會等,後來成了黑社會,但許多分支與黑社會無關,致公堂作為洪門的一支,不僅支援了辛亥革命,在抗戰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兩岸三地,華人社會對洪門都比較認同。
北京晨報:為什麼海外洪門影響這麼大?
陶短房:這與十八九世紀海外華僑生存狀況有關,他們語言不通,無法入籍,只能互相扶持,不團結就沒法生存,洪門恰好就是這樣的互助團體,所以生命力極強,當然,隨著華僑地位改善,今天年輕人對洪門等組織已不太感興趣,影響力日漸滑落。但在辛亥革命時期,洪門在海外的影響巨大。
為何不提孫中山
北京晨報:海外紀念辛亥革命,似乎不怎麼提孫中山?
陶短房:首先,辛亥革命不是孫中山直接策劃的,第二,孫中山在海外是公開活動,人們對他了解較多,所以評價更多元化,不像在國內,他前期被清政府認為是“亂黨”,只能秘密活動,而革命成功後,他被認為是“國父”,普通人也不太可能去全面了解他。海外對孫中山確實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晨報:為什麼會産生不同看法?
陶短房:這有歷史的具體原因,在革命過程中,孫中山得到洪門的大力幫助,但革命成功後,孫中山並沒掌握多少實際權力,所以無法回報。此外,當時中國政治環境險惡,孫中山不得不與會黨撇清關係,特別是1911-1915年期間,國內發生了殺會黨的亂局,國內洪門與海外洪門是一家,自然會引發一些爭議。
不能質疑辛亥革命
北京晨報:對於辛亥革命,國內學者目前也有一些爭議,海外怎麼看?
陶短房:雖然對孫中山的評價有爭議,但我在海外多年,從沒聽到過任何人對辛亥革命有過異議,大家看法完全一致,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不同聲音,我認為是逆反心理在作怪,對現實不滿,就否定一切。辛亥革命不是幾個人閒著沒事幹才搞成功的,在革命之前,中國人給了清廷充分的機會,1895年中國人給了(洋務運動),1898年也給了(百日維新),1900年還是給了(新政),可換來的卻是皇族內閣,可以説,保路運動中被清兵擊碎的光緒聖位牌,就是改良幻想的墓誌銘。
北京晨報:可批評者認為,辛亥革命沒能建立起一個好的秩序。
陶短房:這話要反過來問,清政府建立起什麼了?民主、憲政、自由……什麼都沒有,如果不革命,會怎樣?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年的帝制,僅此一點就足以名垂史冊。
革命不是錦上添花
北京晨報:如果選擇更平和的方式,損失會不會減少?
陶短房:革命不是錦上添花,孫中山自己説,在辛醜前,在海外談革命,根本沒人理,可《辛醜條約》簽訂後,4.5億人民,要賠4.5億兩白銀,海外的中國人全成了革命黨,因為大家都明白,清政府的統治絕不應再繼續下去了。
北京晨報:可辛亥後是持續的戰亂啊?
陶短房:應客觀地認識歷史,不是辛亥革命帶來戰亂,辛亥革命前一直是戰亂,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日戰爭、中法戰爭,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居然在中國領土上進行,這難道不是持續的戰亂嗎?辛亥革命是持續戰亂的中點,正是這些戰亂才引發了辛亥革命,這是個嚴肅的問題,不能含糊。
不要期待救世主
北京晨報:可人們總是會問,改良好還是革命好?
陶短房:這是個沒法回答的問題,就像面對一個病號,你説開刀好還是吃藥好?能吃藥的時候,誰會選擇開刀?張謇是標準的改良派吧?可他後來也主張革命。百日維新時,袁世凱站在慈禧一邊,因為這對他是最好的選擇,可1911年他卻去逼宮,因為除了革命,局面已經無法維持下去了。革命肯定有負面的影響,沒有人生下來就會革命,革命是毀家紓難,中國人家庭觀念這麼重,不是過不下去,怎麼可能去革命呢?
北京晨報:有趣的是,辛亥中許多人物的形象後來都被妖魔化,為什麼?
陶短房:我們有一種非常不健康的心態,總想當救世主,為了當下的需要,就將歷史寫成自己想要的樣子,這樣的蠢事我們幹了很多年,所以歷史人物的臉不斷在變,可歷史不是做燒餅,非黑即白,看這邊黑了,馬上翻過來,一會兒又覺得太白了,再翻回去。
辛亥革命是偶然嗎?
北京晨報:今天很多公共知識分子認為辛亥革命是一次偶然,您怎麼看?
陶短房:我不認為革命的成功是偶然的,所謂偶然,只不過是發生在辛亥而非壬子、癸醜而已。辛亥革命前,中部同盟會做了那麼多年的工作,40%的基層官兵是革命黨人,《猛回頭》、《警世鐘》等讀物在武漢人手一本,起義軍指揮部都被端掉了,依然能取得成功,這怎麼可能是偶然呢?
北京晨報:為什麼公共知識分子們會出現誤判呢?
陶短房:之所以産生這樣的誤會,因為國內很多公共知識分子習慣於坐而論道、隔靴搔癢,嚴重脫離群眾,他們把民眾放在一個過低的位置上去看,總有一種精英意識。而産生這樣的幻覺,是話語權與民眾脫離的必然結果,當少數人掌握了話語權時,他們肯定會覺得自己了不起。
北京晨報:今天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社會也出現了一些戾氣,您怎麼看?
陶短房:要分清是公共知識分子之間有戾氣,還是社會有戾氣,如果是前者,沒什麼可操心的。中國讀書人自古就喜歡爭來爭去,孔夫子在論壇上拍不過少正卯,回頭就把人家給殺了,宋代、明代讀書人吵輸了會滿門抄斬,可誰也沒閒著。這是我們的傳統了,沒什麼大不了的,媒體不必誇大這一階層的力量,本來也沒那麼大能量。
正確理解中國
北京晨報:可能您不太關注國內目前的狀況。
陶短房:不,海外華人對國內的情況非常關注,中國的穩定與強大與我們直接相關,加拿大華人當年為什麼支援辛亥革命?因為當時北美市政府公開排華,只有男人才能入籍,女人和兒童不能入籍,向華人收人頭稅,直到去年,才有一個市為此公開道歉。華人在海外受了那麼大委屈,中國不強大,我們就沒底氣,國內不太容易理解這一點。
北京晨報:不過發展過快,代價也很大。
陶短房:那要看人民自己怎麼看,拿拆遷來説,上世紀90年代,我在上海做外貿,在老城做市場調查,當地一些人以為我是“拆遷辦”的,圍上來説快點拆吧,老幼三代才住27平方米,後來拆遷了,他們敲鑼打鼓慶祝。保持傳統當然好,可誰願意過70%的孩子沒學上,90%的人沒照明電的日子?成了人類博物館,真是大家需要的嗎?世界上沒有絕對的黑,也沒有絕對的白,如果只從自己的意志出發看問題,就會形成偏差,時代發展了,我們應更多元地去看問題。
陳輝/文
陶短房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國專欄作家,曾長期在非洲定居,對非洲政治、經濟、文化情況比較關注,在太平天國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出版了《這個天國不太平》等著作。 |